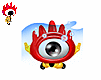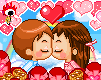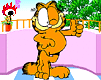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谁来决定住不住高校学生公寓-性、谎言、篱笆墙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4日15:25 新民周刊 | |||||||||
|
8月5日,广东省教育厅向广东各高校发文,要求各高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擅自在校外租房居住。这个文件,激起了意想不到的交锋。双方各据己见,几乎没有任何共识。 而广东省的这个文件实为教育部2004年6月3日《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的细化。
10年前没人会料到,大学生晚上睡在哪儿,会让教育部、大学校长和父母们如此挂心。那时候,无所不包的大学除了提供免费的教育产品,还负责安排父母们放心不下的住宿和饮食,以及国家对公民的日常管理:粮油关系、档案和户籍管理,直至最终为学生分配工作。 而今天,为了让住在校外的学生搬回宿舍,从教育部到高校一再要求、说服、动员,甚至表示不惜动用退学等非常手段。而人们对此的争论,也居然像争论教育收费、教改和大学城建设一样热烈。 性·谎言·篱笆墙 调查显示,除了情侣,租住在校外的还包括大量考研学生,不习惯集体生活甚至为租房而租房的人。但网络在讨论政策合理性时几乎集中在对学生情侣租房同居现象的批判。 1990年代中期前完成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对大学宿舍常有喜剧性的怀旧情绪。10年前,一首流行音乐《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因为满足了这种怀旧情绪,使音乐人获得了良好声誉。实际上,10年之前的住宿条件未必令人满意,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首先是不可选择,其次是价格低廉甚至免费,绝大多数大学生必然要在班级和宿舍里度过大学时光。这种怀旧情绪让其中不少人对今天大学生校外租房持道德质疑态度:开始是嘲笑今日大学生吃苦耐劳精神的缺乏,继而讽刺其性道德。 不少网民列举自己对大学宿舍的记忆后,认定今天学生情侣同居是校外租房最大的动力。有人声称租房可能出于学习所需或生活习惯的原因,也被指责是为大学生“性事”辩解的谎言。然而,这样的指责落到大学里,恐怕不足以激起任何反应。在大学里,校外租房普遍存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决不会让周围人侧目而视。和网络上常见的道德质疑不同,学生显得冷漠,高校体制内的清醒的教育工作者则看到了,随着整个社会观念、经济和生活习惯上的分化,要将学生纳入一个个全无区别的筒子楼宿舍,会越来越难。 熊丙奇的《大学有问题》一书数落中国高等教育弊端,在网上轰动一时。供职于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熊丙奇说,价值观念变迁、行为风险减小和经济发挥了区分人群作用,这三者从深层推动了校外租房现象。 校园内外的价值鸿沟其实是时代性的,大学扩招时正逢独生子女潮出生的一代人上大学的年龄。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20年的社会经济文化成果,城市中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生活习惯、观念和对个人空间的要求,和10年甚至更久以前的大学生已有相当距离。 “10年前不会有人因为室友脚臭、打呼、作息习惯不同就搬到外面去住,但今天完全可能成为现实。”有人说。 2002年,教育部下文要求,高校学生宿舍建筑要“采用筒子楼的形式进行建设,厕所、洗澡等设施一律不进学生房间,电话、电视机也不要进房间”。曾有学校根据学生宿舍的人数、楼层、朝向等划分收费等级,被教育部明令禁止,理由是不能对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搞区别对待。 虽然经教育部确认的宿舍标准样式,在实际建设中有所突破。但筒子楼、公共厕所、水房、定时供电,乃至集体起居,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忍受。 学校正在一步步失去控制学生选择权的力量。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学生为住宿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但如果在校期间发生性行为,一旦“曝光”代价会十分惨重。看不见的道德和舆论压力,严厉的制度惩罚依靠个人档案和毕业分配等等制度设置,轻而易举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这种制度惩罚的威力和中国大学传统的“学校——院系——班级”的垂直管理模式相适应。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中,“班级”和“宿舍”是两个基本的组织单位。前者有利于组织课堂教育和集体活动,后者便于进行日常生活和个人行为的管理。两者像篱笆一样,将学生分割成人数不等的单位,随之规定了他们选择的界限。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才会对学生“住在哪里”异常敏感。大学里,“夜不归宿”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很严重的违纪行为。有的大学卫生检查时,床底下的鞋子头朝里还是头朝外,或是被子叠成方块还是长条,都作为考核的内容,影响到学生的综合测评分数。而后者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名次、是否能获得奖学金乃至今后的分配。而学生的婚前性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之一。 然而,社会道德的标准已经逐渐变化,就业制度的彻底变革和人事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松动,使学生对高校的人身依附色彩日渐变淡,制度性的惩罚逐渐失去着力的地方。 一个曾在大学里流传甚久的笑话说,男生宿舍的熄灯时间会比女生宿舍晚10分钟,因为男生要送女朋友回宿舍。然而,现在一部分学生情侣选择了从图书馆直接回到租住的房间。 篱笆墙上已经被捅破了一个洞。 “圈养”与“放养”两难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写说,因为人口膨胀,巴黎不可遏制地突破了曾有的围墙。无规则向外蔓延的巴黎,失去了优美和秩序。 扩招带来的建筑扩张日益突破“象牙塔”的围墙,高校的管理者欣喜之余,也开始忧心,学分制和后勤社会化会使学生脱离班级和宿舍的“篱笆”,会让学校失去“安全和秩序”。 校长们知道,校园“篱笆”松散,不是从今日始。自从高等教育不再是免费的午餐,原来的“篱笆”就开始了松动,平静的校园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有序”起来。 专家表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免费还是付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高等教育全面收费以后——尤其是大学扩招以后,大学原有的社会管理功能,和收费确立起来的市场主体身份相矛盾。矛盾导致的缝隙,就是“篱笆”松动的空间。 曾几何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午餐。办学经费包括学生住宿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学生不仅不需支付学杂费和住宿费,学校还拨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人民助学金”,补贴学生的生活费用。从1985年开始,高等学校收费水平逐步提高,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公费、自费普遍并轨,高校开始全面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经过1999年以来的扩招,仅到2001年,政府高教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从62.9%下降至52.6%,而高校学杂费收入达298.7亿元,成为支撑中国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根据教育部网站提供的数据,当年中国大学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达到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增长率高达47.4%。学生人数激增,学生宿舍告急。不少高校出于无奈,在校外租赁民房供学生居住,甚至以发放补助的形式鼓励学生走读。今天大学要求学生搬回校内宿舍时,常常可以听见一种讽刺:宿舍不够住就鼓励学生住在校外,宿舍够住则不肯放过一笔住宿费。这个讽刺并非毫无由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高校扩招,校外租房现象同样会出现,但未必会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上议论纷纷的话题,需要各级教育部门下文管理,甚至引发学校和学生的对立情绪。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后勤社会化。学生公寓和食堂的新增建设面积成了衡量后勤社会化改革成就最重要的指标。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后勤社会化意味着,提供宿舍的不是国家福利,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学生在支付住宿费后,和后勤企业确立了市场契约关系,成为平等的买卖双方。 但学生们认为,既然我出钱,我愿住哪里就住哪里。既然学生和提供宿舍的后勤服务集团之间是商品买卖关系,学生就有权不购买其产品。 篱笆上的洞就是这样被捅开的。本来,学校作为免费或廉价宿舍的提供者,天然又是教育者和管理者,在被定义为“第二课堂”的宿舍里,拥有“圈养”的便利和高效率。但现在角色尴尬:学生向社会化的后勤服务集团购买住宿和物业产品,学校则硬插进商品买卖的关系中去。 大学生“住在哪里”,不仅仅是经济人选择住宿产品的问题。教育管理部门不愿放开“班级+宿舍”带来的“圈养”管理便利。在中国的大学呼吁和国际接轨,采用学分制的时候,这种学习制度和管理制度发生了冲突。因为跨院校、跨系、跨专业交叉选课,会瓦解“班级”。杨东平和熊丙奇都称,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主要的阻碍不是来自教育理念,而是担心学分制会削弱“班级”的组织功能,不利于对学生的管理。出于同一逻辑,教育部要求避免不分高校、年级和专业的混住宿舍区,也不允许学生根据不同收费等级选择宿舍,原因亦在此。 惯于“圈养”的一方因为不能组织“放养”状态下的管理,就以行政命令将学生“圈”进宿舍,不仅有“强买强卖”的嫌疑,而且被专家质疑违反了新颁布的《行政许可法》。“放养”还是“圈养”之争,实际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现状。 谁对住宿安全负责 民间舆论最担心是校外租房学生的道德水准,教育部门和高校最急迫的是,要把分散状态的学生重新有效组织到“班级”和“宿舍”中来。这种要求普遍得到学生家长的拥护。在许多父母看来,“圈养”至少能够保证孩子的安全。 杨东平说,狭义的后勤社会化是指后勤系统脱离高校,但他仍倾向认为,后勤社会化应该让大学生成为独立的个人,学校不再管头管脚。熊丙奇直言不讳地说,大学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从行政主体逐渐向市场主体和教育主体靠拢,更重要的是,确立学生的选择权利。 当然,选择权和责任是对等的。学生更愿意享受平等市场主体带来的自由感,但独生子女的家长们普遍认为学校应该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行为负责。自愿“放养”的学生一旦有事,家长就会追究“圈养”者的责任。教育部此次通知一再提到租房发生的意外事故,给高校敲警钟。但《通知》也特别注明,对坚持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在“承诺加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经本人与家长双方签字报学校备案”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在校外租房居住。这个官方的篱笆开口,表明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由一个“单位”对应负责的状况,日渐不复存在。可以住到校外——只要你愿意承担责任和可能的风险。 专家表示,突破“圈养”的模式其实不会如某些人担心的那样,导致天下大乱,也不会必然引发校园周边的治安和其他混乱。杨东平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高校的发展不应走“大学城”这条路,而是形成完整的大学社区,社区内培育校园文化生态,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住宿、饮食等社会化服务。“大学社区”在中国还是概念,但普遍存在于高等教育发达的西方国家。熊丙奇认为,通过学生为主的社团能够实现自我管理的目的。 熊丙奇说,需要规章,也需要对权利的尊重。就像咖啡馆里不能打赤膊,但选择喝什么咖啡,或是喝不喝咖啡,是顾客而不是服务员的权利。撰稿/汪 伟(记者)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