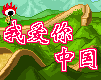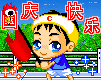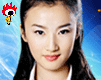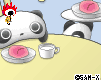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读书》事件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1日18:11 中国《新闻周刊》 |
|
他们为什么?他们谁跟谁? 尊重事实欢迎批评 你是关于“长江读书奖”被炒了近半个月以来第一个采访我的记者,感谢你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 对目前各类批评的看法 我想,从目前各类批评看,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类,绝大多数的批评是善意的,希望将这个奖做得更规范更公正。“长江读书奖”作为一个民间较大的学术奖,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批评,十分正常。我们虽然做得十分谨慎,但确实也没有经验。为此,我们在声明中将基本情况作了陈述,希望大家了解实际操作过程,更希望在此事实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章程和程序。 第二类,借“奖”批评《读书》和汪晖,希图将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以这种方式作出表示。实际上,此次评奖完全是独立操作,与《读书》并非一回事,更与汪晖无关。这样的做法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也不符合事实。其实对《读书》的意见,完全可以直接提出。《读书》也会欢迎朋友们的批评和帮助。 第三类,极少数人,毫无事实根据的谩骂和攻击,如“丑闻”、“腐败”说的发明者和传播者。这些人的言论已给“长江读书奖”造成严重的名誉伤害,构成事实上的诽谤。对此,我们表示应有的抗议和保留追究的权利。 现在的回避机制是科学的 现在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如为什么《读书》杂志主编得奖?为什么评委得奖?似乎这里有什么问题,立法者受了益等等。其实,汪晖作为《读书》主编,人在国外,这次完全没参与评奖这件事,钱理群也根本不是文章奖评委。评奖严守回避机制。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推委、顾委、评委百多位,都是一流学者。要评一流学术著作,必须请他们参与、主持。那么,评出来的得奖著作,也一定会有他们中的人。我们谁也不是算命先生,谁也不知道他们中谁会得奖。所以只能等初选的入围书出来,有谁的书谁就回避。我认为这个回避机制还是科学的、可操作的。如果这百多位一流学者都不能得奖,都要回避,那么我们可以再另请一批学者来做此事,但只要仍是一流学者,就仍会有得奖机会。除非请三四流学者来评一流著作,或请一流学者评三四流著作?我辈无能,想不通这该如何操作,很愿请教高明。 整个评奖过程合法、公正、透明 评奖过程在我们的声明、日志中已全部陈述。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所以特别注意严格按章程和程序做事。有一件事很可说明这种态度:从这次获奖作品看,学科的确不够均衡。在审读过程中,就有学术委员提出:主办单位、学术委员是否有权调整入围书目?但讨论结果,还是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必须按既定章程和程序、尊重全体推荐委员选出的入围书目,以此为基础来评审。讨论决定,建议下届评奖前就研究好纠偏机制,以克服这类问题的发生。 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 说实在的,我在“三联”,自问非常努力非常诚意地为学术界服务了几十年。也一向敬佩为学严谨的学者们,一直想为他们再多做一点什么。这次三联书店与李嘉诚基金会合作举办“长江读书奖”,也是希望为学术界再做一件好事。可对少数人的作为,我确实有些遗憾。但我不会气馁,因为我相信事实,更相信大多数学者是公正的。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会认真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和广大学术界的朋友们一起,把“长江读书奖”工作做得更好。 《读书》杂志风格有变是正常的 这与评奖是两回事。《读书》杂志每一任主编都有自己的风格,这是很正常的。时代不同,社会在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思考也会有所不同,加上主编风格有异。改变是正常的,一成不变倒是不正常了。但《读书》作为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宗旨,我们始终坚持。《读书》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园地,提倡的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我们也始终坚持。在这些方面,学者们有什么意见,我们都十分乐意接受。 《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的名牌杂志。近一段时间,一场围绕《读书》的“批判风暴”在报纸和网站上沸沸扬扬。作为一度被称为“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阵地”,“检验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尺度”的知识分子杂志,这场争论显得意味深长。批评矛头对准了《读书》近几年的风格变化,以及“长江读书奖”的评选结果。来势之凶猛,使业外人士如坠云雾。为此,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读书》各方当事人,请他们谈谈对“读书事件”的看法。 我从《读书》开始学会调皮 沈昌文(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总编) 对现在有关《读书》的争论,我说不上什么话,因为我一点儿也不了解现今的种种情况。 我不是亦远,也没在网上写过什么文章。我再老糊涂也不会忘记自己干过什么。 你问我在《读书》的经历?好吧,这我可以跟你谈谈。《读书》是1979年4月创办的。40年代,《读书》在上海,那时叫《读书与出版》。50年代改为《读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界开始大讨论。陈翰伯、陈原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人想恢复40年代《读书》的传统,办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陈原主编,史枚副主编。我是1980年来到《读书》的。1986年任主编。直到1995年底。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即所谓“寅缘时会”。这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办好《读书》的主要原因。所谓“好时候”,即指得力于那一帮老前辈撑腰。那些都是献身出版事业几十年的老人。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从那时起开始学会调皮。我过去是做秘书出身的,很听话,很乖。在老前辈带领下,我认识到,当编辑要学好,但不要学乖。前不久看到杨振宁博士的一个讲话,他说,中国人只会教孩子学乖,这是不够的。这似乎也适合编辑工作。 《读书》背后的力量 海外有人说,《读书》是官方特许让知识分子说话的地方。那我并没意识到。但在当时求开放的大氛围中,也的确有领导为《读书》说话。如1983年,《读书》几乎要停刊了,因为发表了一些让人不高兴的文章。你们现在可以在《胡乔木论新闻出版》文集里,读到其中一段写《读书》的文字。他说,大家对《读书》有一些意见。可一个刊物办起来不容易。既然已经办了,就让它办下去吧。你们认为有意见,再办一个刊物就行了。我当时听到这话很激动,那不是给我们解脱了吗?当时的领导人,有时还能为下面撑一下腰,很难得。 “不三不四”的《读书》, 《读书》的风格是不拘一格,因此又叫“不三不四”。跟作者的关系呢,你们这些小姐们听了要生气,我把这种关系叫“谈情说爱”,就是说要有感情联系。我们不大有固定的组稿计划。每个月搞一两次派对,那时叫“服务日”。租一个咖啡馆。大家来闲谈,从聊天中了解思想走向,从聊天中定下一些主题。编辑都出来跟大家见面。收集意见回去,开会讨论,向那些老前辈汇报,征求意见。我们最初的资源就来自这种“沙龙聚会”。当时那是北京城里很重要的活动。思想刚解放,大家都有好多想法。 有几句话是老前辈教的,也是我们一直奉行不懈的。如,发表文章就看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做到这些就应该给他发表的权利。有时我自己再加上一条:要选其中表达形式好的。当内容质量不相上下时,我们当然取形式好的可读性强的文章。我曾在一篇后记中写到“《读书》是供读者们卧读的。而不是正襟危坐在书桌前阅读的”。 我当主编是比较独裁的(马克思说过,他编刊物便很独裁)。所以我也要允许别人独裁。我喜欢看香港的打斗片,片中头儿对马崽说:“我要你三分钟之内消失”。我既然已经移交了工作,我也就从《读书》消失了。我还有更感兴趣的事情要做。 我就这么离开了《读书》 关于我的退休:90年,我曾问过上面的领导,董秀玉还从香港回来吗?他们说,不回来了。我于是做了很多安排。过了两年,上面给我一个通知,她还要回来。必须回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改变?他们回答我,这是党的纪律,不必问了。60岁那年,即1992年底,我被准许退居二线。三年间我专心编《读书》。后来上面说不许人们“退居二线”了。1996年1月1号,人事科长打电话给我:老沈,昨天下午你已经退休了。我才知道已正式下文。从此结束了与《读书》十几年的关系。 怎么能以“不变”应“万变”呢? 黄平(《读书》执行主编) 说实在的,我对《读书》也不是很满意,就像我对自己做的其他事不满意、对当今的很多东西也不是很满意一样,无论中国的还是世界的。但是我们只能尽自己所能去做点事情。办杂志当然要多听各种批评意见。一个杂志办得如何,是作者、读者和编辑在更大的语境下互动的产物。现在之所以还有这么多人关心《读书》和批评《读书》,说明它还有一点影响。 展现从黑到白的所有灰色地带 每一任主编都会有一些自己的风格。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读书》,也不能要求《读书》没有变化。至于说什么《读书》成“一家之言”,成“新左派的机关报”,各有各的说法。你只要看看96年以来的目录就知道它是不是这样。什么人在上面发文章,谈些什么样的观点和问题。看看声音是更多了,还是更单一了。 我觉得80年代和90年代一个重要区别在于,80年代是一个相对有共识的时代。主要就是如何冲破教条,怎样解放思想。知识界有一种共识。现在情况不同了,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思想上也就越来越有分歧。而《读书》无非是想展示出这样一种时代特色。别说整个《读书》,就说哪一期吧,能指出它是“一家之言”吗?《读书》也发了很多拥抱全球化的文章,讴歌现代性的文章。即使是批评或反思现代性的文章,也有很不同的批评角度。有人说《读书》是哪一派的机关报,拿得出任何事实依据吗?再说呢,把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复杂性用简单的左派右派这种两分法来划分,这不是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吗?有很多人的很多思想其实是处在中间状态的。《读书》的很多作者和读者都在黑与白的中间地带,怎么能简单地划分到左右两边呢?我一直觉得在黑和白、左和右之间的这一片灰色地带是最有魅力的,因此多元性、开放性的立场和位置是最重要的。《读书》要展现正是从黑到白的所有中间色,那无限的过程。 应该封杀某种声音吗? 《读书》一直坚持“读书无禁区”的宗旨,坚持多样性、开放性。那么各种声音(而不只是左中右的声音)要不要反映?《读书》上发表的自由主义的文章还少吗?说什么自由主义的文章在《读书》上已经发不出来了。这类闲话说得最多的人,能站出来说,哪一篇稿子我们因为其是自由主义而没有发,甚至拖延过?有人一看发了崔之元的文章就说《读书》成左派阵地,成一家之言了。怎么就没看到我们还发了大量反对他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文章呢?小崔的观点你可以反驳,但是用“新左派”去概括,是不是在贴标签?贴上这个标签,思想问题就解决了吗?在中国这种语境下,面对包含无限中间地带的声音,如何贯彻多样性,允许不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某种声音我们不让它发出来? 最近《读书》上发了两篇所谓表扬《白银资本》的文章,就象闯了什么祸犯了哪个天机似的。谁规定不能发?谁规定“弄文学”的人就不能谈这个话题?《读书》恰好不是专业性刊物,只要是思想问题,谁都可以谈。工人农民也可以谈。批评者自己也不是搞世界史研究的,按这逻辑,也该闭嘴?有人质问我为什么不去约研究欧洲史、世界史的学者去写。信不信由你,那是自然来稿,根本不是约稿。我有个缺点,即历来不习惯约稿,当编辑不应该这样。我主要是怕到时候约来又发不了,多尴尬。这是我的毛病。我自己也跟弗兰克吵。怎么能说《读书》发表了某篇文章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呢?一个70多岁的老人,坐冷板凳坐了20多年,出了这本书批评欧洲中心论,去年得了个美国史学界的奖。你说那书毫无价值?有人说问了很多人,竟然都没听说过。那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不是要思想自由要百家争鸣吗?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多年没发东西了,现在发了一点有自己特色的东西,哪怕这些东西你不喜欢,我们要不要给他说话的机会?作为编辑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必须有这种胸襟和气度。你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因为观点而排斥别人。否则那不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专制吗? 怎能以“不变”应“万变”呢? 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问题,不同主编也会有不同的特色。为什么要一样呢?世界都一个样子还有什么意思呢?眼看就21世纪了,时代变得这么快,《读书》不变,行吗?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编辑,也包括作者,的确不如《读书》的前辈,他们是既懂出版又懂写作的大家。我们也不希望《读书》在我们手上变得不好看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为了好看而牺牲问题的重要性。对我和汪晖来说, 从一个熟门熟道的领域来到一个陌生领域,开始当然是困难的,包括用什么语言来说,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一方面我们坚持“读书无禁区”,坚持多样性,一方面拓宽我们的视野和领域,还要尽可能拓宽读者和作者的圈子,和更多的领域更多的现象接触,而不要使它成为文人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小圈子。从建筑学、考古学到地理学,甚至还未形成自己学科的东西,它们中的精彩发现和思想,我们都不能触及吗? 有人热衷于拿《读书》发行量来说事,如说《读书》发行量到了汪晖、黄平手上就锐减,甚至说已降了4万了(也有说降至4万了)。这可以去查嘛。其实,汪晖接手后,读书发行量达到历史最高数。说实话,好刊物不一定就有高发行量。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时代,你要讨论思想问题、文化现象,要有多大的发行量才算高呢?这样的刊物越来越少了。 《读书》需要新鲜血液 说实在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说法都是小事,再尖锐再不宽容也都没关系(但为说话人自己好,最好不要用谩骂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说法多么离谱,不在于有人再也不订《读书》了有人不给《读书》写稿了,这些都难免。最大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日益多样化的时代,各种问题日益复杂日益尖锐,各种矛盾和新旧问题交织冲突在一起的情况下,《读书》如何能继续坚持“读书无禁区”,坚持多样性、开放性,适应新形势,展现新问题。并能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中去。我希望能多听批评意见,多到读者作者中去交流。有误解能澄清,有分歧能交流(包括争论)。更大的希望是那些年轻一代,希望他们能带进新思想新活力新批判,带进新鲜血液,来充实原有的东西。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否则那真的是很危险,真的是少数人的圈子了。再标榜如何“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样做违背了游戏规则” 余华(青年作家,《读书》作者) 前后任主编约稿明显不同。老沈跟我也是朋友。他要我写某种热点话题的东西。汪晖要我写一些哲学话题,要我从一个作家角度,谈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看法。出发点很不同。 我很喜欢现在的《读书》 我比较关心跟我有关的东西。96年后,我开始关心《读书》。我很喜欢现在的《读书》。毫无疑问,《读书》显然成了现在中国知识界最权威的刊物。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应该有一本能及时表达中国知识界最新思考方式、最新研究成果的刊物。以现在这种形象出现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80年代,敢于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与主旋律不同的声音,就是思想。作为一本知识分子杂志,过去《读书》的许多作者,经历过“文革”,积累了很多个人恩怨,通过文章不点名发泄出来,这不是思想。但这在80年代就是思想。今天我们已经超越那个时代。时代有它新的需要了。现在的《读书》与今天这个时代是合拍的。 《读书》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中国知识界的人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过去《读书》更多关心的是过去的问题,而现在《读书》更多关心的是未来的问题。 世界上任何一本著名的知识分子杂志,都有很明确的倾向性。这很正常。 非议不是学术层面问题 我希望这几句话你给我发表。根据这4年来我跟《读书》的交往,这段时间对《读书》的非议不属于学术方面的问题,而是人事方面的。本来我是局外人,根本没空跟他们搅和到一块。但我不能不说一些公道话。 对我这样一个作家来说,文章是不是在《读书》上发根本无所谓。我的书的发行量比《读书》大。我作品的三分之二是在《收获》上发的,但从没人说过我的坏话。我在《读书》上也就发过十来篇文章吧,就有人骂娘了。不满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坏。我觉得这的确不太正常。 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内心之死”。1万1千字。汪晖说太长了。但又不肯把文章还我。后来他说服我,说“要是我们是普通作者关系,文章发也就发了。但正因为我们不是一般朋友,所以要是你的文章1万1千字发了,马上就会有人要求给他发1万5千字”。我最后只能把它变成两篇文章,搞得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所以我觉得给《读书》写东西很麻烦,你知道吗?有这种非学术非文章因素起作用。另外,从97年开始,每年都听到《读书》发行量下降的说法。我曾特意打电话问黄平。他气愤地说“又在造谣”。 一群围剿《读书》的“媒体学者” 就像董秀玉说的,这的确是对《读书》的一种“围剿”。我现在是真正认识到了,在中国学者里,有一群是专心做学问的。有一群是专门跟媒体打交道的,我称他们为“媒体学者”,而那是一群假学者。那些人的文章,有些我曾公开不客气地说,通篇都是废话。你看人家黄平,也是搞社会学研究的,人家多少时间扎在三峡那些偏僻地方。再看汪晖,作为一个学者,能够在美国的《社会文本》,英国的《新共和》,韩国的《创作与批评》等国外最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化和思想史文章的就他一个。人家是真正做学问的。而你看看最近在报上网上攻击《读书》的那些所谓学者,我不客气地说,都是一群“媒体学者”。你就用这个词发表。 什么“违背国际惯例”,胡说八道! 到目前为止,对“长江读书奖”评选结果的质疑,都没有进入学术层面。这不是正常现象。 汪晖获奖不正常?那还有谁获奖正常?!说什么违背国际惯例,无知!你看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里边的好几个委员都获过奖了。我在意大利获得的“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0个著名作家评委,有4个都获过那个奖。你说“诺贝尔文学奖”,那些评委都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没有专职作家,评委自然不会获奖了。再说,“长江读书奖”又不是《读书》控制的。而且汪晖也没有当评委嘛。 汪晖去年10月份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这事一年前就定下来了。而“长江读书奖”是去年年底开始启动的。什么出国避嫌!我去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里的人就对我说,我们请不到汪晖。人家给的是巨款啊。 我本来懒得去管学术界那些闲事。跟我毫无关系。我今天发表这些意见,并没有感情的因素。咳,他妈的,这《读书》还真是事儿多。前后任主编跟我关系都不错,我比较了解。这次对《读书》这样做法,我觉得违背了游戏规则。 问题不是人是制度 汪丁丁(经济学家,《读书》作者) 这几年《读书》的主要问题是,学术性有取代思想性的趋势、或者思想性被学术性削弱了。一些空洞无物,没有思想的文章,披着严肃学术语言的外衣也可以在《读书》上发表了,这更降低了《读书》杂志学术思想的含量。 据我所知,《读书》内部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现象,因为其他杂志的竞争也比较激烈。 我以后会继续支持《读书》。不过现在的《读书》其实并不是太糟糕。 我看《读书》已经10年了,与三届主编都是朋友。我知道他们内部的问题在哪里。我只想说,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安排,再好的杂志也会衰败。我认为《读书》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 “茶杯里的风暴” 盛宁(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以前的《读书》面目比较平和。沈昌文先生基本上是一个报人,相对来说比较中性化一些,没有自己很强的学术倾向,所以过去的《读书》比较兼收并蓄,兼容并包。汪晖和黄平,两人都是学者。不是说学人不能办报。而是说两人的学术立场学术倾向性决定了他们在选择稿子时明显和过去的《读书》有不同。写的是他们认为的社会热点问题。他们也更倾向于读西方热点话题的书。我个人觉得在书的选择上面太窄。 以前的《读书》书卷气重一些。有时也有争论,但很少有箭拔弩张的时候,更多是交流。比较谈自己的一家之见。现在的文章言外之意很多。即使争论也是“茶杯里的风暴”。卷不起多大浪,没多少人感兴趣。 其实黄平和汪晖人品学问都不错。但做刊物跟做学问不同。因为读者期望《读书》是一个园地,大家都能来说说话,能有一些交流。一旦刊物有“同仁”倾向,别人读起来就兴趣索然。其实每个人本身读的书就很有限,如果你再缩小圈子,这刊物的视野就更窄了。 地表深处的潜流 赵丽雅(原《读书》编辑,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放下电话,我就再也不能入睡。作为记者,你的真诚令我感动。但很抱歉我不想接受采访。6年前,我曾以局外人身份写过两则小文。如今再看看,好象仍能用它们来表达我的意见和感情。我绝对不想针对今天的《读书》去“忆旧”。若要摘引那些小文,请务必注明时间背景。(以下是记者摘录) 有人称《读书》是知识界一面旗帜,不惟过誉,且比喻不当。它从来不是猎猎迎风的旗帜,而是地表深处的潜流:不张扬,惟渗透。这是它的坚忍,也是它的狡狯。更是生存竞争中锻炼出来的品格。 《读书》很早就把自己定位于文化边际,就是“文化阁楼”。并非不问政治,但政治进入《读书》的时候,已被纳入了文化讨论的范畴。也并非没有激情,但激情出现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是冷静思考之后的沉淀。“淡定地面对主义”,使它虽身处旋涡中心,却能不失身份,不偏离位置,稳妥、扎实地做它所愿意做的事情。以海派的灵秀与敏锐,去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并很快找到恰切的表达方式;又以京派的沉稳与厚实,使思考不致流于肤浅与空泛。它决不“领导新潮流”,但在它所营造的文化阁楼里,总是空气新鲜,虽然恒常有一种古典式的庄重。 它似乎不太有学术气质。可以说它提供了“思维的乐趣”;或者说,是思维的别一途径,是观察世相、评说世相的别一角度。《读书》人常说的“思想操练”、“语言操练”,也可看作是这同一意思的不同表达。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