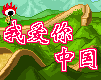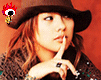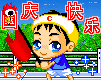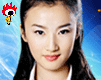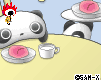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透彻的洞察者,吴文光在他的镜头后面更像一位冷静的医疗工作者,观察着纷繁的生活自身所呈
现的一切。
他最新拍摄的纪录片《江湖》参加了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柏林电影节,当参赛的那部主
流电影被内地传媒普遍起哄式地
炒作之时,《江湖》在该电影节的“青年论坛”上寂寞地放映着。这个栏目不评奖,只是观摩,吴文光说:“西方人从他们的
角度看我的作品,他们觉得这种生活不可思议,和在西方的媒体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在于我的作品是充满细节和
材料的,他们过得好还是不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这种生活的过程。”
《江湖》是去年年底才完成的,拍摄这部影片的原因是很偶然的,吴文光在几年前就无意中拍过一个大篷演出的片断
,他后来找到这个大篷歌舞团的经理,开始了对这个流动部落的拍摄工作。拍着拍着,他感觉把自己的生活也拍到里边去了,
这是一种当代生活,像丧家犬一样,一个可以落脚的客栈还没有着落的时候,使劲的还在瞎转。这部片子没有大起大落,绝大
多数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一个关于友情和背叛的故事。吴文光没法判断自己身边的生活是好还是坏,但是糟糕却是肯定的。
他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了,特别合得来,可以睡在一起,可以吃他们的,还可以为他们去派也所,为他们解决问题,甚
至吵架,有时他为他们做红烧肉吃。吴文光说:“做人不是做出来的,是非常自然的,有一种感觉是我在那儿时间一长,觉得
北京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变得和我没关系了,那是一种美好的日子,很温暖的感觉,外面风呼呼地吹着,就在门口撒泡尿,
很舒服。”
迄今为止,除《江湖》外,吴文光还拍摄了《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四海
为家》等四部纪录片,均在海外参加了若干电影节,却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播放过。吴文光无奈地说:“我当然愿意有更多的
人看,但事实上你无能为力,这倒不是因为拍的内容,好像所有电视台都不喜欢这样的东西,觉得太长,两个多小时甚至三个
小时。好在做这些我是从纯粹的兴趣出发,这是我能够不断做下去的重要原因。”
基本上,吴文光是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用低成本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梦想,这可能和他以前在云南和于坚一起写过
诗有关,因为诗歌写作也是一种用低成本完成自己梦想的方式。吴文光回忆说,80年代的一个上进心的标志,就是喜欢体育
和文学,那时自己没有拉小提琴的条件,爱看点书,就拿起笔来涂两下,后来他发现自己没有多少写诗的才华。吴文光说:“
你想你跟于坚生活在一个时代,而且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这等于是给自己背上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力特别大。当然不是非要当
第一才要写诗,关健在于写作里面有没有发现自己感觉到的东西。”
其实,他现在还在继续写东西,比如说在《芙蓉》杂志上连载的《江湖报告》,他说是用报告的方式写作的一种东西
,也不能算是报告文学,而是像流水帐那样,全是材料,更像一个社会调查。他认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
诗意”给弄丢了,他说:“诗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不能说所谓的诗意就是一个没有行动的所谓的空想,并且呆在一个
非常自恋的小空间里。有大才华的诗人能够创造一个非常不朽的作品,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来说,特别对于那
些没有才华的所谓诗人来说,靠它来苟延残喘,而且病态地生活着,是一件非常无耻的行为。”他强调说:“拿80年代来说
,中国有很多人在写诗,但写诗绝不是意味着你有多高的文学素养或者说文化高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人已经堕落到用一种自恋
的温情来自我抚摸的程度。”
吴文光80年代初就读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做了一年中学教师,就开始想往外面跑。80年代初期尚是浪漫
主义盛行的时代,他先去了西藏,后来又到了北京,他想到更边远的地方看看,他选择了新疆,就真的跑到新疆去了。他在天
山脚下做了一名老师,那儿有一个很大的牧场,他随身带去的是一把吉它、一本杰克伦敦的《马背上的水手》、一本海明威的
传记,还有一个海鸥205的照相机,以及一个很便宜的放大机,用来冲洗黑白胶片的,还有一条香港亲戚给的牛仔裤。他在
那儿呆了一年零八个月,没有离开过,他想在那儿写作,他以为这种异地的远游,再加上一点冒险的生涯会给他的写作带来很
多的灵感。但真的下笔写了一些东西却觉得惨不忍睹,后来干脆就不写了,忙于骑马、打猎,跟当地人喝酒打牌。后来由于母
亲病重住院,他又回到了昆明。
在当地干了两年电视台记者的工作之后,吴文光又想离开,那已经是80年代末期,他可能觉得北京的空间会更大些
,便来到了这个庞大而浮躁的地方。那时的北京象开了锅一样,到处是一片灰心丧气。恰恰是那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状态
反弹,他开始用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了他周围一些朋友的生存状态。慢慢地除了拍纪录片还写东西,出了两本和纪录片有关的书
:《流浪北京》和《1966:革命现场》。
吴文光认为纪录片是不可以替代的,他说自己对故事片既不爱看,也不爱拍,因为它需要非常强的虚构的能力,他觉
得自己没有这种能力。他觉得拍纪录片越来越像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式,是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的一种东西,不像拍故事片,需要
一大群人,导演像个公关先生,要和所有的人接触,那种昏天黑地的工作方式让他感到害怕,绝大多数时间消耗在和艺术无关
的行为中。他觉得在中国有很多东西是打折扣的,比如导演,就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工作时有很多人和机器簇拥着他,装束
也很奇怪,比如说胡子。吴文光感到轻松的是纪录片一般不会有如此庞大的阵容,可以很简单,尤其是现在有数码设备,后期
几乎在家里就可以完成,前期的工作有一个助手就足够了。
吴文光并不在乎有些人觉得他很业余,他认为业余不业余不在于你拿的机器牌子有多好,而在于你到底要做什么,拍
完《江湖》之后,他现在更进一步拍一些随心所欲的东西,他随时都在拍,随时都在做,纪录片对他而言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
式。目前他还参加一些戏剧和现代舞的演出,最新的作品是参加《生育报告》和《屏风》的演出,其中一个是由林兆华导演的
。吴文光以前曾经在林兆华导演的《等待戈多 三姐妹》中担任过一个老是呆在楼上的角色,而现在他通常在戏剧中扮
演的就是他本人,比如在《生育报告》中他用镜头对着别人拍摄并且提问,他觉得扮演自己会更适合一些。
说起独立纪录片的现状,吴文光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70年代出生的一些年轻人拍的东西尽管不多,只有一个两
个,但是非常厉害,他认为他们一出发就做他自己想做的,一上路就没有弯路,这非常不容易。他觉得尽管拍得可能有些幼稚
,也有些破绽,但非常有力量,可以看到一个忙碌的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事物,人们忙得就像苍蝇一样被忽视了,被抛弃了。
在午夜的黄亭子50酒吧,吴文光用手卷着烟卷,头顶的灯不太亮,有些微的摇晃,照耀着他的影像,他说话的音调
不高,南方的口音在夜色下缓缓出鞘,他说:“不管什么时代,总会有些东西是远离中心的,边缘的,……”
文/江熙 摄影/法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