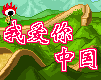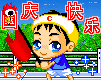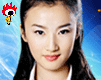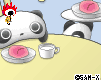我不是“文革余孽”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1日15:32 中国《新闻周刊》 |
|
余秋雨首次开口说文革旧事 近来,对著名学者余秋雨的各种批评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新千年伊始,青年学者余杰的新作《想飞 的翅膀》出版,对余秋雨的批评再度升级。余杰在新作中 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 子加流氓”,批评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余杰自称别人的批评没有批到点子上,没有真正的力度,“我觉得我 自己这篇文章比他们一本书的分量都要重。”本刊特约撰稿杨瑞春日前对两位当事人进行了独家专访。另外,余秋雨先生独家授权本刊发表他就余杰的批评致余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记:千禧之旅期间,出来了很多批评你的文章。最近的批评,大多是关于你的文革经历的。最近余杰写了一篇文章叫 《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质问你为什么对文革的历史避而不谈? 余:是吗?具体的文章我还没看到。关于文革,他们说的那些材料是伪造的。他们始终抓住一个叫“石一歌”的事情 ,说我是其中一个。我倒想问一下,“石一歌”的哪一篇文章出自余秋雨的手笔,请拿出证据。石一歌小组的那些人也都还在 上海,可以去问一问他们。 这里面有些基本的疑问很多人不去想: 首先,文革过后石一歌小组是经过清查的,清查的时候有余秋雨出场过吗?。 第二,文革清查在中国历经了整整三年,可以说每个字都曾经查过。清查结束后,我又没有什么背景,居然作了正厅 级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难道合乎政治常识吗? 第三,我做这个院长,是全学院三次民意测验第一名的结果。我不是从外地调到上海的,文革中一直在学校。如果我 做了什么,全校那么多双眼睛能看不到吗?当时我是中国最年轻的校长,为什么做了那么长时间的校长没人举报我? 记:那篇文章说,有人告诉作者,你是石一歌里面最年轻的写手。 余:就凭这一点,可以证明那个人完全不知道石一歌是什么。因为我在复旦大学参加编写鲁迅教材期间就看到第一次 署名石一歌的是一本写给小学生看的著作,《鲁迅的故事》,作者是一批工农兵学员。如果硬把我塞在里边,年龄不仅不是最 年轻,而且是最老的。仅此一段,证明此人的话不能相信。 现在石一歌的等级被闹得越来越高,这很可笑。你现在把“石一歌”和“梁效”放在一个等级,很多人都搞不清,但 在那个时候连在一起就很可笑了。石一歌那时候连外围的外围都谈不上。至于他们在一些学报上找到的文章,当时的署名、写 作、文章来源的状态跟今天想的是完全不同的。 记:那署名余秋雨名字的《胡适传》是你写的吧? 余:我真希望他们能打电话问问我,什么是《胡适传》?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署了我的名字?为什么只发了一个开 头不发了? 现在看来,我们解放以后对胡适先生的评价是非常不公正的,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学术界好像还有大量对他持否 定态度的意见。我们当时所谓编教材、写胡适生平,居然连他的任何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完全不存在研究和写生平的起码条件 。现在想来是荒唐可笑的。但是我至今认为,对胡适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多元并存,他的有一些经历即 使在我后来读了他的书、对他产生高度尊敬之后也还是抱非议态度的。他后来实在太政治化了,影响了自己的学术文化成果。 记:你当时效力于《学习与批判》杂志吗? 余:这个杂志当时的身份好像是复旦大学学报,因为当时毛主席反复号召要恢复学报,但后来这个杂志的倾向肯定是 四人帮的喉舌,里边也有一些刚解放的教授发表文章,那只是一些点缀。这个杂志有自己的编辑部,人员很明确,我不知道效 力的概念是什么。 记:有人说《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而写的。 余:这在时间上好象说不通吧。“批邓”的时候我已经在养病。我原先以为,林彪爆炸以后,造反派头头被逮捕,各 校复课,连我这样被造反派一直批判的人也有资格编教材,好像文革差不多已经结束,“批邓”一开始,这个感觉又没有了, 所以我很快以养病为名离开上海,到了家乡。在家乡,其实已经没有我住的地方,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不短的流浪生活,一直 到四人帮垮台才回到上海。 记:这段时间大家对您议论纷纷,看来确实跟事实是有出入了? 余:这不是出入,几乎可以说是颠倒。我不能说哪些人是在想故意害我,但确实回想起了文革中哪些寻找内奸、叛徒 、特务的思维方式,那么多专案组好像也找到了一些传言的线索和零星证据,一时间出现了那么多的坏人,后来平反时才发现 ,那种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诬陷上纲、浪漫联想、不把问题推到极端决不罢休的方法实在太可怕了。我在文革期间至少代父 亲写了五十万字的忏悔材料,怎么也符合不了造反派所定下的忏悔思路,所以很有感受。 我祖母当时七十多岁,我叔叔是他的小儿子,在批斗中自杀了,只剩下了我爸爸这个大儿子。她就每天在批斗会会场 大门门缝里去偷看批斗我爸爸的大会,我妈妈陪着。当时挂在我爸爸脖子上的牌子上面分明写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得力干将 ”,不知情的人一看以为他是多么重要的中央干部,其实他连一个副科长都挨不上。这种抓住一点,“全线畅通”、直逼顶端 的大跳跃式的逻辑方式什么时候能被真正的理性逻辑所替代? 记:关于文革的经历你好像很少做正面的反思。 余:我写了很多呀,像《长者》不就是其中的一篇吗? 有关个人的直接反思,如果我诬陷了人,批斗了人,迫害了某个老师,打击了某个干部或者参加了造反、抄家,或对 哪一些个人的大批判,我一定要忏悔;如果我明知邓小平的整顿对中国带来了希望还去积极批邓,说违心话,我也一定要反思 。但这几个方面我恰恰是完全没有参与,而且坚决反对、态度明确、从未动摇。因此,我把反思这件事看得很大很高,而不是 追究具体的个人责任。那些做了坏事的人的个人责任当然要追究,但不能强迫他们反思,因为思维领域的事很难强迫,强迫坏 人反思我认为是抬高了坏人。 如果用强迫的方式要别人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思想结论,而强迫者又没有搞清楚行为的真相,那么缠来缠去,争执不休 ,反而把反思这件大事降低了、庸俗化了。总有一些人至死不肯反思自己的罪行,但只要理性群体深入反思了,中国就有希望 。 如果就具体经历讲,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真可以说是悲惨之极,远远超出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想象。我看到一 篇文章提到,我在《千年庭院》一文中说起自己班级里面造反派同学和保守派同学如何分裂的过程,就断言我是在为造反派辩 护,为红卫兵辩护,因此又推论我是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其实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没有一个不知道,文革初期十九岁的我,是 全院第一个领头写大字报反对造反派的人,结果造反派掌权以后,承受了长时间的批判和侮辱。我没有向他们有过一丝一毫的 屈服,他们曾经威胁要与我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抄我的家,如果这样的事真地发生了,我可怜的祖母和母亲可能很难活 得下去,但我也没有因此向他们求饶。只是文革结束后,我做了院长,觉得很多责任不能完全让他们来承担才原谅了他们。 父亲关押后,全家八口人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只好变卖有限的衣物过日子,惟有叔叔能帮助我们,他又被斗死。我 是全家的大儿子,可以说文革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考虑家庭生计。初中才毕业的大弟弟不得不出海捕鱼来养活全家,但他每 次从海上回来,总是先找我问爸爸自杀了没有,那时他才十六岁。因为我们全家知道,爸爸的心理承受力远远低于叔叔,叔叔 自杀了,爸爸活下来是个奇迹,总以为他活不了几个月,我和弟弟还发现一件事,我爸爸居然有一次冒险从关押的隔离室里逃 出来去偷偷拍了遗照。这一下我们就更紧张了。其实爸爸没自杀的唯一原因是考虑到如果他一旦死亡,连每月二十六元的生活 费都没有了。全家怎么过? 即使我在复旦大学编教材期间,所有的心思也是放在家里。因为我爸爸在关押中六次病危,我记得有很多次我从复旦 大学坐车去看望爸爸时一路上都在哭,用手捂着嘴,车上的人全都看着我,其实我当时真是束手无策,不知怎么来救活爸爸, 照顾祖母、母亲、几个弟弟。当时我只要向任何一个最小的权势者表示软弱,求他们去给爸爸单位的人联系稍稍补发一些工资 ,我们家就会结束这种惨状,但我始终没有这么做。所以,现在那些文章和传言说我是受到康生、张春桥重用的人,真不知从 何说起,真不知如何向祖母、叔叔的在天之灵做解释。 我的这种经历在当时的中国千家万户都经历了,不足为奇,但确实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所不知道的。现在的年轻人要 重新批判文革当然很让人高兴,但无论如何,不要凭一时意气随便论断、“浪漫推理”,结果很容易造成根本性的颠倒。 有时候,想起来文革的痛苦,我都有要号啕大哭的感觉,他们现在说这些话的人是无法想象当时我受了多少苦,又经 受了多大的考验。有些年轻人认为我不大谈文革,是因为不敢谈,而我倒是因为受苦实在太多,怕在反思中掺入太多个人的情 绪,所以我有计划稍稍等几年,等个人痛苦再沉淀一阵,好好写一本回忆录。 记:那为什么这些年别人从相反方向问起这些事的时候,你一直避而不谈? 余:正因为是相反方向就没法谈了。例如你问我父亲在文革中打过多少人,我怎么谈?我能谈的,只是他挨了多少打 。又比如,有人问我,你在造反派中担任什么职务,我也无法回答,我能回忆的是被造反派批斗了多少回。这种相反状态很可 能会让提问者彻底失望。也让读者疑惑不解,而许多事情,我们又无法拉着证明人到报刊上去论辩,所以只能沉默不言。就象 有个人在路上硬说你长了尾巴,我不能当面脱裤子给他看。即使证明了确实没有尾巴,但当众脱裤子的动作比有尾巴还要难看 。 但是这种不作申辩的情景也有例外,譬如五年前香港有位叫罗孚的资深老报人误听一个上海人的传言,在《明报》上 发表文章,说我在别人的剧本上署了自己的名字,也说到我是石一歌等等。我立即请律师发表声明,他看我态度强硬,必有真 情,对自己开始产生怀疑,居然向上海的很多朋友一一查证,查证的结果使他明白了真相,他在《明报》连续三天向我道歉。 我看到这个道歉热泪盈眶,立即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他,感谢为我洗诬,他又写文章说该感谢的不是他,又继续向我道歉。这件 事使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人,什么是真正的大报纸。他们不可能完全不讲错,但却知道错了该怎么办。 记:你的文章里说红卫兵的行为只是孩子的胡闹,余杰认为你这样是为他们的罪行开脱。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余:请注意这样的句子出现在我的文章中,说的是我班级的同学!我的很多同学确实很可怜,他们在文革初期只知道 要保卫毛主席,哪里知道什么上层斗争!后来多少年他们都因为这些问题受尽苦难。你想想看,当时这些人的年龄只有十多岁 ,但他现在还背着那个时候的沉重包袱。 就我自己而言,我确实觉得我的这些同学没有责任,现在也这么说。哪怕他们当年是造反派,曾经伤害过我。从另一 个角度上讲,即使说他们应为此负责,他们所受的苦难已经够多了,下到农村、几十年的压抑,难道他们的罪行还没有抵消吗 ?我不希望这种苦难继续延续下去。 这是我父亲对我的教育,他受了真正十年的罪,我们几个孩子在文革结束后问他们单位造反派的名字,他说:“他们 都太年轻,响应号召过了头,主要责任不在他们,已经受过处分,你们不要再问了。我也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后来,我收到 一封读者来信,说他既是我的读者又是我家庭的罪人,希望再一次向我父亲道歉。我转达给父亲,原来父亲根本没有忘记他们 的名字。我看着苍老的父亲,十分感动,心想,他是不想让仇仇相报的悲剧在低层次上延续给下一代。 记:但如果这些年来说了这么多不确实的话,为什么你没有表现出愤怒? 余:再闹下去我就要愤怒了。但这愤怒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为什么这样一件未经确实的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中国人际关系似乎有这样一种力量,只要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名气,他们就会找到任何一个缝隙把他灭了。我们的文化结构怎 么会是这样的? 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位大师要求负责的批判者要有一个对基本事实的了解,而且是整体了解,而不是未经诠释的“传言 真实”和“文本真实”。余秋雨还活着、余秋雨当年的许多同事还活着,余秋雨的单位今天也还在,需要做一些起码的准备工 作。这些是不难做到的。 实际上我忽然想到我们有时候对古人的评价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幸好我还活着,记忆力还好,依然有写作、说话的 能力,并且事情过去还不算太久。请所有的人拿出证据来。文/杨瑞春 满会乔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