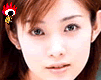最后一棵树(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08日18:07 安吉生态文化节组委会 | ||||||||
|
刘福嫌表哥越扯越远,老是财大气粗的口吻,这这那那自以为是,便说喝酒喝酒莫谈荆州。可许说得动了情,抱住酒瓶又自干两盅。不看僧面看佛面,这学校我一定盖好,不会
姓许的说得很慷慨。郝山扑哧笑了,敢情是我们向你要啥了,还是你当真欠我们什么了?盖学校就是盖学校,喝烧酒就是喝烧酒,甭扯得我们两个人心慌。 可愈这样,许愈是不成,说二位也许不知,那老柳树不一般,是一棵水泉柳呵。在东北不稀罕,在咱这儿就难得了,划成板子纹路水着呢。打家俱也好,装修家也好,都是上等的料。 原来如此,郝山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怪不得他非要那树不成。水泉柳早听说过,平时掏上大价钱都难买到,却不想老柳树就是一棵水泉柳。可说啥也晚了,他不知姓许的何时就瞄上了。心里不禁感叹,土包子就是土包子,跟姓许的咋也差一码。 刘福也出乎意外,老柳树就是老柳树,没想到竟这样珍贵。他清楚,老柳树在郝山心中的分量,便夹在中间有些尴尬。他不知,表哥精明还是糊涂,天大的便宜你得就是得了,干吗还要当面夸口?大概被二两猫尿烧昏了头。 姓许的却依旧在说,儿子就要结婚了,房子想装修装修,这老柳树正好用上了。刘福想把话截住,又怕伤了表哥的面子,想打圆场又不知如何打。郝山看着姓许的,拿火柴棍剔着牙缝,突然嘿嘿笑道,天下的好事都让你占了。他说,你不是不亏我们吗,过几天学校搬迁时,我们准备搞得像样点,老弟能不能助个兴? 郝山以老弟相称,许听了非常舒服,满口应承助助助,不就是一顿饭吗?郝山便掏出那字据,说甭嫌老哥做事小气,最好也批到上边。唉,我真拿老哥没辙,许没想到会来这一手。他叹道批就批,兄弟啥时候骗过你?写罢,把笔当地搁下。 姓许的上了圈套,这个圈套不会浅的,刘福干急也没办法。他深知郝山的脾气,正经起来比谁都正经,歪起来也比谁都歪,会叫你把兴助个够。他实在搞不清,表哥没喝酒时精明透顶,喝上酒咋变得像个蠢猪? 郝山朝刘福挤挤眼,举酒说今天真高兴,我和福子谢你了,往后如有啥不当,望老弟多多海涵。至于那树嘛,你想啥时候砍,就啥时候砍…… 几天后,姓许的便带人来砍树,同时在学校又开始施工。砍树的头天晚上,郝山怎么也睡不着,就来到老柳树下,独自呆了半夜。 山里的夜很寂,寂得像透明的冰,扳一块都会脆响,像娃们吃锅巴。在夜空下,四周的大山黑魆魆的,村子仿佛毛茸茸的鸟巢。老柳树与夜几乎溶为一体,郝山坐在树下的碾盘上,烟头红红的一明一灭。这时,他感觉陪伴着老柳树,如同小时陪伴着祖父一样,“祖父”在讲述许多往事,线砣似的绵绵不尽。 从他记事起,外界有啥风风雨雨,村里有啥风风雨雨,老柳树都同样经受了。五八年放卫星,六八年闹批斗,七八年搞承包,哪次都没得脱,树上的标语贴了一层又一层。饿肚的时候,常有人半夜三更到树下,偷偷摸摸地揭过标语,用刀剥那留下的糨糊。最残烈的是,他听人讲日本人进来时,三个长辈跟八路军打游击,被捉住后绑在树上活活砍死了。据说血气冲天,老柳树六月叶黄,人头在树上悬挂了几天,几天都飞鸟绝迹。 除此以外,老柳树下还是红白事宴,村人必不可少的热闹之处。无论娶亲回来,还是送出殡来,一定要在树下吹打半天。红头涨脸的鼓手,喇叭朝天地吹奏着,叽哩哇啦把村子都沸了。老柳树下也是村里议事的地方,开会时黑压压的坐下一片人。他就是在这树下当选支书的,从此只要有大事商量,就把村民召集到树下。修学校也不例外,那天他站在碾盘上,大声说今天开会没别的,就是大伙儿早看到了,咱那学校破得还叫学校吗? 他扬着手讲,在家里都把娃当金蛋蛋,一到学校却成了泥蛋蛋,风吹雨打的连山药蛋都不如。这首先是我的责任,谁有火气想撒就撒吧,但光撒气不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得修学校。可村里的光景,大伙儿也清楚,哪有钱盖学校?我便琢磨着,还得在树上做文章,把村周围剩下的树卖掉。再想点别的办法,向乡里要一点儿,向教育局讨一点儿,把学校盖起来。就这么个事,大家看咋的? 跟以往开会一样,村民们开始不吭声,可只要有一个说开了,立刻像蚂蜂炸了窝。这个也吵吵,那个也嚷嚷,紧要的不紧要的都来了。大伙儿郑重其事,但清楚不过是走走过场,最终修不修学校还得他决定。几位村民便说,反正学校不能不修,要修学校树不能不砍,可包括不包括老柳树? 意思是,砍老柳树就不同意,不砍老柳树就同意。他说不砍不砍,砍了连个开会的地方没了,连个唱戏的地方也没了,咋能砍老柳树?说起唱戏,他小时非常心醉,每逢唱戏就红火得不得了。戏台搭在树下,晚上不等锣鼓响,就爬上树挤占地方,常看着看着就睡了,一觉醒来已人去戏散,月挂树梢。 现在却要砍了,他跟村民向来说一不二,可这次为盖学校食言了。那满山的树被卖掉,心里都未怎么难受过,卖老柳树却非常不好受,就像要出聘闺女似的,而且聘出去永远不再回来。他拍一把老柳树,仰望着说我亏你了,我这辈子也欠你了…… 第二天早上,姓许的便张罗着砍树,村民知道后出来阻拦,可一听是支书让砍的,就又都退后去了。但骂声不断,开会说得好好的,咋就当屁吹了?卖、卖、卖,不停地卖、卖、卖,卖得山成了光屁股,再卖就卖娘们的×了。到后骂声止了,知道骂也无济于事,一个个看起热闹来,就像看谁家娶亲一样。 郝山蹲在梁上,他天未亮就下地,锄罢地要回去时,见姓许的带人砍树,便脚跟儿一软停下。面前是一棵桦树桩,黑苍苍的像伤疤,树桩的根并未死,转周生出一丛新枝,正好挡住他的身影。村民们看不到他,他却看得很清楚,骂声也听得很清楚。工人们戴着安全帽,那桔黄色的安全帽,像秋天熟透的南瓜。 因老柳树过于庞大,姓许的让工人先下枝头,工人们便爬上树锯的锯砍的砍,粗大的枝杈在斧锯声中“塌”下来。“塌”得非常壮烈,伴随残烈的折断声,如黄土崖陷落似的,在地上击起一片烟尘。嫩绿的柳叶纷飞,像成群的蜻蜓起舞。村民们不再是看,一窝蜂似的涌上去抢,枝杆上的细条嫩叶儿,转眼间被一扫而光,抱回家去喂羊。 郝山看红了眼,就像粮仓被抢。操你妈们的,他直想跳起来怒吼一声,那又不是发国民党的洋财。可话到喉咙,变成了哀叹,发吧、发吧,反正就这一次了。他把眼闭上,那折断声刺在心上,像打破的酒瓶锋利,要刺出血来。 就这样,老柳树如盖的绿荫,在斧口下渐渐消失了,仅剩下光秃秃的树身,像剁掉五指的手臂戳在那里。周围一片狼藉,枝杈横陈竖卧,被肢解了一样。郝山像法场陪罪,一下感到自己衰老了许多。脑里乱纷纷的,又仿佛一片空白,总摆脱不掉老柳树的影子。 姓许的怕损了材料,不用锯伐要挖起来。他指挥工人,先挖出一个大坑,然后把相连的根子砍断。几个工人光着背,巨大的板斧抡起时,一道灼亮的寒光闪过,像冬日的阳光投在冰面上。落下去时,一声沉闷的钝响发出,细碎的木片飞溅。几只板斧交替起落,便如旋转的水车车叶,当当的砍斫声随之不断。 郝山呆不下去了,起身离开梁上。他茫然无措,目光遍抚粗糙的山野,看到残存的树桩时,恍惚觉得自己是刽子手,双手沾满了树的鲜血。他觉得村民骂得好骂得对,这些年不停地卖卖卖,满山遍野的树都给卖了,最后连老柳树也难幸免。以后再卖啥呀,还再有啥可卖,难道真要卖女人的那个了? 这种近乎作乱的负罪感,他多少年来几乎不曾有过,甚至几天不见砍树心就痒痒,看着一棵棵树倒下简直是享受。那热火朝天的场面,砍的砍抬的抬运的运,仿佛坐虎皮拥火盆的山寨王,在欣赏喽罗们一片忙碌…… 村里静悄悄,村民们不是下地,就是看砍树去了,像唱戏时的光景。郝山漫无目的,既不想回家去,又不知到哪好了。当支书十多年了,从来都走在人前,把街面跺得很响,今天却躲躲闪闪怕见人。他经过刘福门前,见院门敞开着,就打一个定顿,抗着锄头拐了进去。 院里静静的,鸡在南墙下扒食,羊卧在栏里反刍。郝山忽然作贼似的,左顾右盼着屋里院外,变得有些心神不宁。他把锄头立到窗台下,轻轻地咳嗽一声,问屋里有人么?停等一下,见无人应声,就拉开门进去。刘福女人背对着门,正伏在架盆上洗头,他说咋问死都不吭气? 刘福女人仍不说话,郝山以为还没听到,就盯住那背瞧起来。粉红衫子脱在炕上,刘福女人只穿件背心,因弯腰裤子绷了下去,背心却向上翘起来,露出一截红裤衩。郝山便晕了一下,目光沾在裤衩上,像手似的要剥下去。他想起了那一巴掌,想起了那一声嗔怪,想起了那两嘟噜奶子,眼前如太阳似的炫晃。 郝山拦腰抱住女人,女人只是颤了一下,没有任何的反抗。头发倾泄在盆中,女人冷冷地停下手问,今天不球性气了?郝山喘着粗气,便往紧里一搂,说不球性气了。女人于是转过身来,把头发撩到背后,两手搭在郝山肩上,说院门也没关着,不怕他回来损了你? 女人的眼里荡着水,水得像刚洗过的头发,水得扑鼻的芳香味。郝山把手滑到臀部,让小腹紧贴住自己的小腹,说院门关不关无球所谓,不被撞见说明爷有艳福,被撞见损了也心甘情愿。你不是老说爷球性气么?那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女人不等说完,便两手槌打他的胸脯,――死东西,死东西,死东西…… 骂着勾住郝山的脖子,郝山顺势往起一抱,踢鞋巴一步跨上炕,拉一个枕头轻轻放下。女人仰躺着,任凭他把衣服剥去,说知道表哥要来砍树,一早他就着着忙忙走了,你咋不去?一提砍树的事,郝山就有些心灰,停下手望着女人,火似的目光矮了下去,变得浑然不知所措。 女人正感迷惑时,郝山两眼又突然放亮,放亮得火星四溅。他仇恨似的,伏到女人身上说,我也要是去砍树,谁还会来砍你?女人被塞进的舌头堵住了嘴。含糊不清地说,我早上就有个感觉,感觉你今天要来砍,不砍就不是姓郝的…… 屋檐上的一块瓦片,不知猫踏了还是风惊了,啪地掉下来打得碎。屋里顿时风平浪静,郝山出来抗起锄头,一面往外走一面扣扣子,在门口碰上刘福回来。两个人都愣在那里,刘福蠕蠕嘴想说什么,可盯着郝山扣扣子的手,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郝山顺着对方的目光,瞧一眼未扣好的扣子,问树砍完了? 嗯。刘福拿鼻子回答,脸一黑埋下头问,你也砍完了?嗯,郝山也拿鼻子回答。可“嗯”罢了,连自己也吃惊,忙改口说嗯球啥呢,我是路过进来解了个手。说着出了院门,刘福听郝山的脚步远去,就三步并作两步进屋,见女人伏在盆子上洗头,屋里一股洗发膏的香波味。他清清嗓子问,砍树时四处找不见他,却跑家里来干啥? 谁?女人没有抬头。刘福瞅着裸露出的后背,说谁谁谁还能有谁,那个起草发情的秃驴。女人依旧在洗头,哪我还知道,除了找你还能干啥?哼,找他妈的×,刘福打量着屋里,说大概是闻见骚味了。 女人吃的一笑,抬起脸撩开头发,说你是怕闻见,还是想叫闻见?女人眼里缠着血丝,眼脯下泛着桃色。刘福被问得哑口无言,出去把门重重甩上,把喂鸡的瓷碗踢得乱响…… 两个月后,学校全部完工,围墙建起来了,一百多级台阶也修好了。校门两侧刷了红彤彤的标语:“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搬迁时很隆重,从乡里借来十几面彩旗,还请来一个威风锣鼓队。 典礼由郝山主持,参加的有县教育局和乡政府的领导,带来的奖状什么的摆下一溜。郝山头剃得光亮,从上到下打扮一新,像谁家办喜事请去当总领。典礼开始后,先是奏国歌升国旗,接着是县乡领导讲话,还有教师和学生代表发言。最后是郝山讲话,他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又回到了儿时看电影的光景,激动得双眼都潮润了。 他起初还有点怯,抓耳挠腮吭吭喀喀,麦克风被震得嗡嗡响,但讲着讲着就嘴溜了。刚才领导们说,盖学校是落实“三个代表”的最好体现,“三个代表”我学是学来可没想那么远。老师和同学也说,我想师生所想急师生所急,不怕大家笑话这倒是真的,可不光是我一个人。刘村长也想来急来,所有的村干部都想来急来,要是他们不想不急的话,这学校是盖不起来的。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光凭我一个人成吗? 当然更少不了领导们的支持。郝山拍拍旁边姓许的又说,也多亏了许老板的帮忙,像今天咱们红火谁呢?哈哈,就是红火许老板呢。许立刻起身抱拳道,不敢当、不敢当,我给盖学校是挣钱的,说帮忙谈不上。能有幸来参加,权当凑个乐子。 郝山讲完话,威风锣鼓队便开始表演,十几面大鼓一字儿摆开,铿锵的鼓声喧闹了山村。村民们大开眼见,正陶醉在鼓声中时,一群山雀突然从天而降,霰弹似的攻击起人来。一时间会场大乱,人们开始光顾逃,继而人鸟混战起来,所幸人没有踩伤挤坏。事后,校园内一片狼籍,死下的山雀随处可见,有的被踏得血肉模糊,羽毛和尘土四下里飘飞。 许多人变得衣服不整,一副丧魂落魄之状。许被屙了一团鸟屎,一边拿纸揩一边哀叹,真他妈怪了,好端端咋就惹了这些鸟们?郝山光头上被啄起个包,自嘲地说这有啥好怪的,鸟们也是来凑热闹呗。刘福的脸让抓破了,他一声没吭,悄悄离开学校,到小卖铺买了香烛,去后山脚下的山神庙了。 教育局和乡里的人都躲进了教室,因躲得及时没有被鸟伤着。一个个望着屋外的场面懵了,不知何故触怒了那些山雀,突如其来的跟人过不去?便叫师生赶紧收拾,让锣鼓队重新敲起来,以防鸟们再来袭击,还派了人四周警戒。可表演的再演不起劲来,观看的也再看不起劲来,总是诚惶诚恐地顾忌着天空。 表演草草结束后,郝山便招呼去吃饭。像办事宴一样,刘福女人带几个人,着忙了整整一上午,着忙出十来桌饭来,屋里摆不下就摆到院里。许一进院就傻眼了,说得好好的只管一顿饭,咋摆了这么多桌?再加上请锣鼓队,还有其它的开销,这得花多少钱?他上郝山的当了,可上得有点哑巴吃黄莲,因为自己当初说的只是一顿饭,并没有规定多少桌。 他扯扯郝山的衣襟说,你真是山汉成精,今天要存心宰兄弟了?郝山鬼眨着眼一笑,说堂堂大老板甭耍小气了,哪里省一点不值这几桌饭?心想宰不宰不由你,白纸黑字写着呢。一面招呼客人入席,一面又俯到许耳朵上道,老弟用不着发愁,我不是还欠你工钱么? 许顿时醒悟,敢情是要拿工钱来顶,不顶就甭想拿到工钱。心里不禁恼怒,这简直是要挟,简直是过河拆桥。嘴上却笑盈盈说,老兄宰就宰吧,就怕好吃难消化。郝山听后便拉入座,哈哈笑道那不怕,比起老柳树来,要好消化的多了。何况我这人,活半辈子了,就喜欢吃硬的。 午饭吃得很热闹,一个个酒喝得上劲,话也侃得非常上劲。可侃来侃去,最后总要侃到鸟事上,听说过老年间狼闹事,而鸟闹事还是头一次。除了奇怪之外,都感到有些不祥,但谁也没把话挑明了。郝山心里也圪圪瘩瘩的,几两酒下肚本已撂到脑后,一听吵吵又不痛快起来。他今天情绪很好,自觉脸上特别风光,却不想被鸟们搅了。早不闹晚不闹,偏偏那时候闹?像一片阴影,他不知预示着什么,又将要发生什么。 刘福没喝几盅就倒了,剩下全凭郝山来应酬,但再也应酬不起兴致。他从不相信神呀佛呀,这时却突然感到了一种罪过,而且好像一条蛇蛰伏已久。那阴影如云破开,一束桔黄色的光笼罩心头,他好像顿悟似的明白了一切。嘴里呐呐道,该撒手了,该撒手了…… 郝山把碗中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从今天起不再当支书了。人们沉浸在酒中,起初并不以为然,都以为他喝多了,或得意过头了,说醉话说痞话,想叫人恭维赞叹,支书当得不错。因为这样的话,他已不止说过一次,可到后还是照样当着。一个乡干部就取笑,你快甭做秀了,如果嫌奖状给得少,我回去再给要几张? 郝山听后血红了眼,真想拿酒碗把那干部飞了,可看大家酒正喝在兴头上,转而吃吃地笑了。他笑得很狰狞,说姓郝的就那么贱,就那么稀罕一张擦屁股纸?我告诉你,老子当支书是乐意,盖学校也是乐意。现在老子不乐意了,这还有好奇怪的? 众人见如此说,才停下酒当真起来,但不明白究竟为啥。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早有准备?要么就是有了好差事,或者班子不和干不下去了。那乡干部脸上搁不住,便自己找个台阶下。这么说,老哥是真甩手不干了? 郝山没有回答,拿起酒瓶栽下半碗酒,然后转桌挨个儿去碰。到了姓许的跟前,说跟别人喝都是碰,跟老弟喝却是敬了,谢谢你给盖学校,也谢谢你这顿饭。老弟不用担心,我不干了福子还干,欠你的工钱一定打清。 可许仍有些懵,舌头发僵地说,老哥就、就是不干了?你也以为我骗你,我骗你们干吗?郝山便转身大声问,老少爷们说一说,当支书当十几年了,我姓郝的骗过谁?他摇摇头说,没有、没有,我谁都没骗过,可、可是…… 郝山显出了醉态,脚也把不稳了。那样子有点悲壮,他再没有往下说,“可、可是”什么,像个尾巴留给了众人。热烈的气氛凝滞了,席面上变得静悄悄,都盯着郝山猪肝似的脸,想寻找出一个答案来。 宴席就这样结束了,多少有些不欢而散。像发生的鸟事一样,郝山突然辞去支书之职,一时成了村里议论的话题。在一片议论声中,郝山却扛着镢头上山了,从早到晚不停地挖坑,渐渐鱼鳞似的遍布了山野……(黄风) 相关专题:浙江安吉生态文化节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浙江安吉生态文化节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