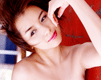西瓜皮祝枝山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2日17:29 时代人物周报 | ||||||||
|
-车前子 祝枝山在当代,除了书画界,知道的人不会太多。我宁愿把话说得保守一些。我以前写散文,出现的人名,常常不加注释,以为地球人都知道。看来情况并不是如此。前不久某青年书法家找了一班人马在人民大会堂开他的书法集发布暨研讨会,有个做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津贴的书法理论家发言:“字写得不错,但书写内容太不讲究,一定要书写名篇,《
我觉得这有点喜闻乐见,清名不到学者耳,陶庵先生笑盈盈。注:陶庵先生即张岱。 接着说祝枝山。祝枝山,明朝书画家,兼善诗文。或者说他是诗文家兼善书画。他的草书有明朝第一之称。苏州人。弘治五年举人,做过小官,有文集传世。在民间故事里,祝枝山几乎是唐伯虎的马仔,其实他是唐伯虎的前辈,《明史》上说他“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名声比唐伯虎显赫。唐伯虎有绯闻,颜色浓得起来。祝枝山没有绯闻,颜色也就浓不起来。虽然唐伯虎的绯闻是民间艺人痛痛快快涂抹出的子虚乌有的桃色,虽然有专家为唐伯虎鸣冤叫屈六月雪,但唐伯虎作为风流的符号早已深入人心了。说他幸或者不幸,替古人担忧,无非是今人开脱,身后是非谁管得,活过就活过了。你能告诉我吗?活过是一种幸还是一种不幸? 在正史里,祝枝山倒是风流人物,挥金如土,仕女如云,而唐伯虎基本只有正常且拮据的家庭生活,到了民间故事里,到了野史里,却整个翻了一个个儿,唐伯虎就像天蟾舞台上的风流小生,祝枝山就像天桥撂地上说相声的邋遢老头。正史与野史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也就是说这都是想象——正史是合乎上层建筑的想象,野史是合乎世俗基础的想象,正史为了调和统治阶级的矛盾,野史为了疏通平民百姓的情绪,历史说到底或许是今人把几个好玩的古人放在想象空间里的把玩,历史之中恰恰没有时间。祝枝山的风流被换到唐伯虎身上,唐伯虎的潦倒被换到祝枝山身上,只要出效果,在空间里能占住面积,就都合情合理。 民间故事里,祝枝山的书法作品无人问津,唐伯虎的绘画作品供不应求,祝枝山求唐伯虎救济,唐伯虎对买画的人说:“从今往后,你们要买我一张画,我就要搭卖祝枝山两张字。”买唐画的人不干,唐伯虎说:“我的画是西瓜,你们买西瓜总得连皮买回家吧,有剥了皮买的吗?明白了吧,祝枝山的字就是西瓜皮。”买画人说:“大师说得也有道理,只是为什么要一下子搭卖两张呢?”唐伯虎摸了一下祝枝山的脸,说:“西瓜皮厚呀。” 那一年清明,祝枝山跟着唐伯虎春游,凭吊烈士,看见一个小寡妇带着一条狼狗上坟,小寡妇正哭着。唐伯虎对祝枝山说,你能把她逗乐了,我送你一坛酒。祝枝山说这个好办,他走上前去,冲着小寡妇毕恭毕敬地喊了声:“妈妈,你在这里啊。”小寡妇本来就恨不得拿把扇子上坟,看祝枝山痴不痴癫不癫的,忍不住噗哧一笑。祝枝山对唐伯虎说,快去置酒。唐伯虎说,你再能把她逗怒了,我送你三坛酒。祝枝山说三坛酒太少,最起码五坛酒,我才去。唐伯虎说五坛酒就五坛酒,但你逗不怒她,要罚十坛酒。祝枝山说这个好办,他走上前去,咚的一跪,冲着小寡妇身边的狼狗,连磕三个响头,毕恭毕敬地喊了声:“爸爸,你也在这里啊。”小寡妇勃然大怒,喊道:“狗狗,上!” 受人好处,也就要看人脸色,往大处想,和受气差不多。祝枝山又是西瓜皮,又是喊娘叫爹,平日受够了唐伯虎的气,但唐伯虎是唐老板,马仔祝枝山只得忍气吞声以泪洗面,但一遇到软柿子,他又拼命地捏。夏天的时候,文徵明家种的梅子都被人偷走,文徵明当然不高兴,一次与唐伯虎、祝枝山喝酒,文徵明说:“我家梅子都被偷了。”祝枝山接过话头,说:“春天你说你家笋被偷了,去年冬天你说你家萝卜被偷了,你家女人怎么这么容易被人偷啊?”吴方言里,梅子和妹子、笋和婶、萝卜和老婆一个音。所以至今苏州卖萝卜的小贩从不敢吆喝,“卖老婆啊!”,这一吆喝,会跑来一巷子光棍。 癫狂不羁的李松 -杨卫 李松是一个很本质的画家,我甚至觉得除了画画,别的他可能什么都干不了。我这话当然不是说李松没有别的能力,而是他对画面的专注与痴迷程度,使人觉得他生来好像只能干这一行,也必然会干好这一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生的,一个人的爱好与人生选择是不是早已命中注定?但我知道撒旦只管撒旦的事,上帝也只管上帝的事,既然选择了自己的事,就一定要做好。李松也是这样看的,他并没有把画画想象得多么崇高,也没有把画画想象得多么低贱,而只是把它看成了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职业,每天必须要面对。 李松的这种朴素思想常常能带给我一种踏实的感觉,看看美术圈子里那些张牙舞爪的“能人”,再看看脚踏实地的他,我更愿意把赌注压在他身上,把希望的目光投放给他。人说深坑才能积厚水,其实,做人也是一样,只有深刻才能厚实,才能饱满起来。 我跟李松认识,也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会儿,我们都住在圆明园,彼此是邻居。那时的李松就以他特有的勤奋而闻名村里,他不像园子里的某些画家,喜欢东跑西颠地四处找机会,那时的他几乎从不出村,除了偶尔在酒桌上与朋友海饮一番,多数时间则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房间里画画。那时的他就已经画了满墙满屋的画,而且是写实的,这在常人看来不可想象,像我们画一张并不怎么写实的画都要磨蹭一两个星期,而他却能画出这么多写实的作品,真不知道是怎么挤出来的? 我一度猜测李松一天的二十四小时,至少有一半时间在画画。果然,有几次晚上我去找他,他都在挑灯夜战,弄得我每每都不好意思,为打断他的创作而责怪自己。可李松又特别好客,一旦有朋友来,总要端菜摆酒、山呼海饮一通。 李松与酒,曾经是一个分不开的连贯词,圆明园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喝酒,而且逢酒必多。后来有人喝酒开始躲着他,认为他喝酒的状态过于生猛,于是乎,李松更是会到处找人喝酒,而一旦再喝也就更容易狂醉。 关于李松那一段时期癫狂不羁的喝酒状态,其实我很理解。酒是一剂清心的良药,不仅可以化解心中的郁积,而且可以消除疲劳。对于李松这样每天闷在房间里工作的人,如果再没有酒,那就太黑暗了。 现在的李松住在通州,跟我还是相距不远。经常,我们还会在一个酒桌上相聚,但现在的他却再也不端酒杯了。李松的这种变化,不仅令我,也令所有朋友们吃惊,看着跟原先判若两人的他,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承受的? 对于李松的画,我曾经写过文章。在我看来,生活中的李松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的作品也是朝往一个方向的延伸,关系到他的心灵、记忆,以及所有跟他精神和肉体相碰撞过的事物。有人说李松有点空中楼阁,而我恰恰认为,他的楼阁中装满的正是我们曾经和即将失落的一些情怀。艺术家分为两类,一类喜欢关心社会事物,而另一类则更关注内心世界。我觉得这两种类型的艺术家都不可缺少,因为世界需要颜色,时代也需要丰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我想,这不仅只是对艺术家,也是对所有人。 李松最喜欢念的一首诗,我记得其中一句:“目光的棍棒碰着四壁。”在念这一句的时候,李松的情绪会很激动。看得出来,他很压抑,极其渴望得到一种心灵的放纵。然而,现实不是臆测,更需要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承担。不论是对于李松,还是对于我,也许都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沿着自己现在脚下的路一直走下去,只有走到更黑,才有可能看到清晨的那个黎明。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时代人物周报专题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