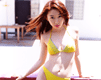城市像泡菜坛子越泡越香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3日12:44 南方周末 | ||||||||
|
6月9日至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动设立在老城区的几个分会场,原住民、房地 产商人、规划师、建筑师、电影导演、记者、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围绕现代化与旧城改造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报驻京记者 石岩
6月9日,北京什刹海边上的两层仿古建筑“望海楼”在建成11年之后,首次打开了大门。第一批踏进大门的人发 现地面上的尘土有一寸厚, 墙地天花六个面都是粗糙的混凝土,像烂尾楼一样裸露着空洞和呆滞,这和雕梁画栋、油彩鲜艳 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北京和北京——现代化与旧城保护间的挑战”展览活动的一个会场。 借展览的光,四周的居民第一次得以走进望海楼的大门。直到去年,防护板一直把他们和望海楼隔绝开来。“一到夏 天,热得不行!”住在马路对面的刘阿姨眉毛都竖起来。“以前我们这就是水边了,夏天风吹过来凉快极了。这楼一挡,风也 吹不过来了。” 刘阿姨说,望海楼的一部分侵占了临海的便道,另一部分,是在“填海”之后盖起来的。楼前一棵成人可以环抱的杨 树,被说成由康熙的孙子手植。 “太恶心了!要篡改历史!那棵树是我们瞅着长起来的。”一早一晚歇凉的时候,刘阿姨开的“爱海之友小卖部”门 口,望海楼总是闲聊的街坊们埋怨的对象。 树从房脊里长出来 望海楼是“北京和北京”活动艺术及建筑展览会场。会场的背景是望海楼粗糙的混凝土墙面,策展人吴华在一些角落 支起脚手架,拉上黑色的鱼鳞网,摆放“危险,请勿靠近”的标识来强化“工地”的效果。一些铁皮制成的胡同铭牌钉在四面 的墙上,或者成堆散落在地上。甘露胡同、邱家胡同、半截胡同、玉芙胡同、永泰胡同、马厂胡同、黑虎胡同……它们已经消 失或者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 温子先把数十辆残破的自行车用钢丝密密麻麻地编在一起,有的车丢了座子,有的轱辘是扭曲的,有的断了辐条,所 有的车都被喷上白粉,它们曾经是四散在城市角落的主力交通工具,现在,它们的遗体被收集起来连缀成一堵白色的墙。 邵帆把古旧的太师椅和现代的板式家具嫁接在一起。“传统”和“现代”,“现代”对于“传统”的破坏以直观的方 式地被呈现出来。 按照吴华的设计,展览的入口设在望海楼东侧门。“观众从这个门走进来,经过曲曲折折的水榭,享受后海开阔的水 面和微风,夕阳泻在身上,简直美得不行。可是一走进那个黑洞……对比会更强烈。” 吴华说的黑洞,就是望海楼内。她心里有一张可以缩放比例尺的地图。“望海楼是一个工地,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大工 地。” 在吴华心中,理想的布展是“实地游览式”,观众在走过水榭和“黑洞”之后,到周围的胡同转一转,之后向东,经 过与后海比邻的烟袋斜街和二环边上的国子监,再经过平安大街东头的南新仓,到二环和三环之间玻璃房子正在拔地而起的幸 福三村,“一条线走下来就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理想的布展方式没有实现。但与展览同时进行的、有关“保护老北京”的 若干讨论都选在“实地游览”的节点上举行。这些节点代表“老北京”的几种命运。 SARS之前,烟袋斜街一脸素净,街边的民居、道观保留着多年不变的古朴。北京市政府25片历史街区的保护名 单公布之后,斜街上的私房主纷纷效仿已经“起来”的什刹海,将各种油彩涂在小街的脸上。“政府说了,这片永远不拆!” 在街头卖麻辣烫的老北京头也不抬照顾锅里的菜。她的身后,几个外地民工正在往院子里运砖头,对老房的修葺正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房管局对修缮仅作高度上的限制,风格要求是笼统的“仿古”。于是,各种版本的对于“古代”的想象在街边滋生、 复制。今天的烟袋斜街是丽江和凤凰的翻版。 国子监街更幸运一些。1992年,在获得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介入到国子监地区的改造中,对区 内建筑、街道、树木进行详细调查之后,拿出了整套改造方案。“这是中国第一张按照实际测绘情况做出的规划图。”当时参 与项目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说。为了保持国子监的文教特色,规划方案要求沿街不得开辟商铺,对房屋外部的修葺装 饰要在古建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尽管与游客云集的雍和宫比邻,今天的国子监街依然保持着她的宁静。 更多的老城区没有烟袋斜街、国子监的名气或者人气。吴华曾经站在钟楼上看下面的胡同,“道路和院落的结构已经 被严重破坏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树好像是从房脊里长出来。老城是有病的。” 受保护的老城区从25片扩大到30多片,尽管被拆了三分之二,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老城在。“拆和保解决之后, 老城可不可以动?谁来动?”吴华问。 谁配住在老城? 以前能动老城的基本限于开发商。为了让更多的力量介入,“北京和北京”把原住民、规划师、建筑师、电影导演、 记者、大学生跟开发商组织在一起。在望海楼、在南新仓、在国子监街和烟袋斜街的茶楼、酒吧,他们讨论“北京城市发展和 社会认同”、“北京的开发和发展对老北京保护的挑战”、“旅游给老北京保护带来的影响”、“老北京VS.当代建筑”。 “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认同”讨论会开始之前,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作了国内首次公开放映。电影放 映之后的交流环节,影片的摄像刘杰说《17岁的单车》记录了他对美的认识过程:“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 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 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 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可是到处都在拆。我选中了一个地方,两个月后实拍的时候,跑去一看已经拆掉 了。2000年底,这部片子拍出来不久,在放映上遇到一些麻烦。有关人员问我,北京有那么多美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专拍 灰暗呢?我问他们认为北京什么地方美好,他们说,比如国贸啊。” 在“北京的开发和发展对老北京保护的挑战”讨论中,自称参与过多个旧城区改造项目的地产顾问公司老板李忠成为 众矢之的。 李忠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老城改造的重要原则——保证相当数量的原住民还能回来——在北京是不可能实现的 。“老城的居民可以分为居住户、户口户、产权户三类,真正的原住民在其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 个人的户口。所以老城的拆迁成本通常是非常之高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建高楼,这对老城的格局是一 种破坏,另一个选择就是把老城区的居民置换出去,对原住民进行更新。随着地皮价格上涨,未来老城将主要发展无污染的高 创意的行业,老城居民可能没有从事这些行业所需要的技能,在城里,他们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上,以前他们去菜市场 买菜,以后可能不得不去超市买菜,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恰当的生活方式。” 家住后海的聂先生为“地皮升值之后,老城对原住民是不恰当的生活方式”瞠目:“别提文化消费,就家里过日子那 点事儿,我们这的物价是市区里最便宜的。”特定人群的聚居使得什刹海形成独特的生态环境,尽管四面有高楼和宽马路,在 这个环境里面,老北京们并没有觉得窘迫。“他们开发商应该去开发那些没人的地方,已经有人活得好好的地方就不用把人赶 走了,让他们‘开发’了。”聂先生这样回敬李忠的“好意”。 “他的意思我听得很明白:穷人不配住在老城区,你们滚出去,让富人来住!那要这么说,我觉得他也不配住在老城 ,他也不够富,得李嘉诚或者比尔·盖茨才行!”丁艾说。丁艾是老城区的原住民,她的名片上印着“北京旧城保护民间志愿 者”。 老城的出路是发展旅游? 接下来关于“旅游给老北京保护带来的影响”的讨论中,丁艾和其他原住民成了主角。 他们大多是“北京旧城保护民间志愿者”。而这些志愿者中的大部分又是经租房(经租房一词来源于1956年1月 18日的一份中央文件,这份文件提出了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 )的原产权持有人。2001年开始,在零星的上访咨询过程中,这些人慢慢聚集在一起。 从6月9日到15日,“北京和北京”的各场讨论,他们场场必到,且有心照不宣的分工:有发言人,有人附议、有 人专司记录。 在老外、记者、北大城市规划教授的包围下,做过十几年胡同游导游的老王坐在桌子上,掏出本子和笔,一条一条介 绍他对于保护老北京的心得。 老王的第一条是“呼吁政府有效保护北京市内的古树”:“现在什刹海的很多树,叶子是发亮的,那是虫子屎。好些 枣树都得了疯枣病,过两年就得死。俗话说‘要看院子老不老,就看有没有树’,要想保护地道的老北京,这些个都得治。” 老王的第二条是“胡同的深层开发”,样本是他几个朋友自主开发的家庭旅馆,“外国人来了,可以踢毽子、弹琵琶 、吃饺子、听京剧”,“效益相当不错”。 老王的建议得到了原住民热热闹闹的响应。他发言的时候,丁艾小声告诉记者,去年,民间志愿者们就向有关部门递 过“一份东西”,阐述把老城房屋产权落实之后,可以在胡同里开家庭旅馆,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也能缓解2008奥运会 的住宿压力……老王的话音一落,丁艾已经站在场子中央:“我在大大小小几个旅社,导游、计调、外联,都做过。很多游客 跟我说,北京旅游多少年都是老五样:天坛、故宫、长城、十三陵、颐和园。自打有了胡同游,游客们总算有了个新去处。据 我所知,现在50%的北京游线路里都有胡同游这个项目,但胡同游主要集中在后海这一片。什刹海现在最少有十二三家胡同 游公司,好多都是黑车,大部分导游都是外地民工,对胡同根本不了解就开始胡抡。就是这样,到了黄金周,黑车、‘不黑车 ’加一块都不够用。” “他们不是要经济效益吗?不是不知道老城保护下来干什么用吗?我们告诉他干什么用!”家庭旅馆、私房菜馆,一 言以蔽之,发展旅游是原住民们共同的结论。 “这是最好的。股票你还可能套里头呢,这个,房子是自己的,想经营就经营,不想经营自己住着。到哪天也赔不了 !”赞成老王和丁艾的戎阿姨向记者耳语。1990年代大规模拆迁开始之后,戎家的6处房产被拆掉了4处。戎阿姨希望, 剩下两处的产权能重新回到自己手中,若有经济能力,她会把两处房子置换成一个“真正”的四合院。 城市乌托邦 做着“老北京”之梦的不仅仅是戎阿姨一个人。《城记》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北京老城保护的今天与明天” 一场讨论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勾勒了存在于文献之中的老北京: 元大都时代,相隔79米有一条胡同,胡同的宽度是按步行街的尺度设计的,所以住在里面的人能体会‘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的意境。胡同是步行的距离,是产生《西厢记》那样故事的距离。如果今天的北京以公交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胡同完全可以满足出行需求。 然而事实上,现代北京的尺度是“大马路、小汽车”的尺度。“双向六车道、八车道的大马路在这个城市比比皆是, 可照样堵得水泄不通。”王军说,“北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九五’期间达400亿元,占GDP的4.3%;‘十五 ’期间预计投入838亿元,占GDP的5.15%。这样的投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是,现实的北京交通并没有得 到根本缓解。走路不方便了,骑自行车不方便了,乘公交车不方便了,开小汽车也不方便了。” “道路面积率低”、“道路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通常是修建大马路的理由。为了弄清楚其合理性, 王军曾采访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杰夫。苏的答复是,“建大马路是不明智的。”理由是,“在一个高密度的路网,我要去一 个地方,如果前方堵车了,我就能方便地改变行车路线,选择其他的途径到达。因为在这样的路网中,一个地点总是与多条道 路相连。而你建一条大马路,也就只能通到一个地方,像北京那样的快速环线,要是堵车了,大家都出不来,只能挤在那里, 使拥堵范围迅速扩大,这是很脆弱的情况。所以,你还不如把一条大马路,分解成许多条小马路,使它们形成系统。” “美国也有过惨痛的教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城市里建了许多大马路,甚至出了一批超大街坊、靠大马路和小汽车 维持的城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城市是非人性的。”苏杰夫说。 城市不止为道路而存在。居住在城市里的人需要城市有亲切可感的多个侧面。王军对于城市的想象和《城记》的灵魂 人物梁思成颇类似。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位置的建议》中对老城城墙的功用做出这样的设想: “今日这一道城墙已是个历史文物艺术的点缀……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的地方 。(并且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地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城门。” 现在,城墙已经没有了,旧城还残存着一些小寺庙。王军认为,这些小寺庙可以成为社区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会 朋友、聊天、散步……在古之幽情的涵养中完成社交。然而实际上,现存的小寺庙已经很难完成这样的功能,它们有些被大杂 院或者某单位侵占,门洞或者被砖头砌死或者堆满杂物;有些像东直门内大街的药王庙,主体已经被拆没了,只剩下一座庙门 ,旁边是一块被铁栏杆围起来的断碑。 与这些有形的改变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些无形的改变。 “传统的北京不存在富人区,在很有钱的人家旁边就住着穷人。包括帝王生活中的很多服务都是和地方共用的,比如 皇帝出殡时候用的杠房。”6月14日,参加“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动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木盾教授说。 事实上,李教授所言的贫富杂居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 唐代的长安城就是按“宫城”、“皇城”、“郭城”严密规划的三重天。宫城是皇帝的寝宫,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 郭城是百姓的居所。郭城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衬托皇权的威仪,另一个是便于官对于民的管理。前者可以从一些数字上得到 印证,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坊墙可以作为后 者的例证: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 买东西,只能到东市、西市——这就是“买东西”片语的来历。 城市有了生气,是在宋代以后。“到了宋代,坊墙被拆除了,于是有了《清明上河图》,”王军说,“每个院落是城 市的细胞,如果维持其生命状态,这个城市就像一个泡菜坛子,越泡越香。”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南方周末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