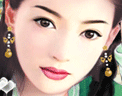兰州与西藏50年的故事:青藏铁路把它们距离拉近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31日18:40 都市天地报·城市周刊 | |||||||||
 云丹加措  徐铸 本组报道:文/本报记者 郭兰英 李永成 佘超龙 图/本报记者赵立华 任春艳 时间像一把重锤,把所有的记忆都夯实在了历史的深处,让我们难以挖掘。就像兰州与西藏的联系,历史远比我们知道得更多。
50多年前,在当时的中国,兰州是内地进入西藏的必经之路。西藏工委在兰州设立了内地第一个办事处。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全国所有去西藏人员的接洽工作,还有内地运往西藏物资的联系和运输。然而,50多年过去了,兰州这个“门户”的作用几近消失。如今,随着青藏铁路的修筑,兰州有望再次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成为西藏通往内地的桥梁。 在5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兰州和西藏两地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一幕幕动人的故事。他们或身在兰州想念拉萨,或身在拉萨想念兰州。然而,漫漫长路阻隔了他们的思念。 一、 在兰州想念拉萨 年少时,他们用双脚丈量着走进了藏地,几十年后他们回到了兰州生活,这一别又是几十年……岁月漂白了他们的鬓发,却抹不去他们对雪域高原生活的深深眷恋;虽然人在兰州,可他们依然想念西藏,想念拉萨…… 在西藏驻兰州办事处干休所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70岁的云旦加措和76岁的黄万俊。虽然已步入古稀之年,但这两位藏族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云旦加措头戴黑色礼帽,身穿深灰色的休闲装;黄万俊头戴深黄色礼帽,身着夹克衫。从外貌和穿着来看,云旦加措和黄万俊与平时生活中的老年人没什么区别,然而,这两位外表看似平凡的老者,在几十年前先后进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雪域高原。 征服“生命禁区” 人物:黄万俊 76岁 在藏工作42年 踏上西征路 1951年年初,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像是个新生的婴儿,但她的人民却已经在兴奋中沉浸了一年多了。解放台湾、挺进西藏的标语随处可见。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锋镝已经接近了“三八线”。全国上下掀起的红色大潮一浪高过一浪。 那年2月6日,地处祖国大西北的兰州还没有度过严冬。金城,这个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已经成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后方。在位于萃英门的西北革命大学里,21岁的黄万俊被班主任叫住了:“组织上动员学员们去西藏,你考虑一下吧。”听了班主任的话,黄万俊楞住了,他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去不去西藏这个问题。他没有立刻给班主任答复。回到宿舍后,黄万俊犹豫着:去西藏好像没什么意思啊。用黄万俊现在的话说,那个时候,他的革命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然而,在后来的几天中,班主任又对他做了几次工作,黄万俊终于在西北革命大学学生赴藏人员报名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被编入解放军第18军独立支队。 接下来的几天里,黄万俊接受了组织上的审查,学习了党和国家对西藏的政策。“当知道西藏人民还在封建农奴制的压迫下时,我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去西藏的路。”黄万俊说。 为了运输物资,黄万俊被派去河西买牲畜。在永昌,他们买了300峰骆驼,40多匹骡马。随后,他们和到其他地方买牲畜的人一起在青海湟源集中,做着进藏前的最后的准备。 7月,隆重的誓师大会召开后,独立支队向西藏进发。一路上,队伍穿过了地势高寒、荒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越过巴颜喀喇山,跨过黄河源,用“牛皮筏子当军舰”强渡过了通天河(沱沱河)。11月,黄万俊随同独立支队到达了拉萨。老远,黄万俊就看见了金顶辉煌高耸入云的布达拉宫。回忆起艰难的进藏历程,黄万俊感慨地说,徒步进藏,就像长征一样艰难。 我想念在拉萨的儿女 到西藏后,黄万俊被分配到了日喀则干部大队部。给当时的日喀则盖礼堂、建人民医院。此后,黄万俊又跟随医疗队和宣传队深入到日喀则下属的县里,向当地居民发放无息农贷,并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为推翻农奴制度做准备。“那段日子是很苦,可再苦也没有当地的老百姓苦。一想到要解放西藏,推翻农奴制度,再苦再累也就感觉不到了。”这段历史,让黄万俊终生难忘。 在那段日子里,吃饭成了他们的一个大问题。在一些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地方,做一顿饭,有时需要一夜的时间,通常都是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一起吃。 1957年,黄万俊调到了日喀则地区政策研究室,当年在各县区做的社会调查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政研室工作了半年,黄万俊被派往四川大学学习。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黄万俊又被组织上招回了西藏。这一次,他在西藏一待就是34年,直到1993年回到兰州。 采访中,我们问黄老先生,青藏铁路修通后,还想不想去拉萨看一看。老人沉思良久,抬起头低声地说:“我想念远在拉萨的儿女……” 一颗红心 献给西藏 人物:云丹加措,70岁,在藏工作32年 平息叛乱进了西藏 1959年3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0个春节刚过,北京还是春寒料峭。在中央民族学院预科班上学的甘肃天祝籍学生云旦加措和另外三个藏族学生正在刻苦学习。过一段时间,他们要接受学校的派遣,去苏联留学。这一年,云旦加措23岁。 3月19日,星期四。一大早,云旦加措和另外几个藏族学生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说西藏叛乱了,学校接到命令,停止他们的学习以及去苏联留学的计划,3月20日进藏。老师的口气很严肃,没给云旦加措任何思索的时间。“一听到这个命令,就知道非去西藏不可了。不过当时我们年轻学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已经70岁的云旦加措说起当初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 回到宿舍,云旦加措把被褥打了个背包,就算准备妥当了,就等着第二天踏上去西藏的路。 艰难的进藏征程 3月20日,云旦加措和其他同学从北京乘坐开往兰州的火车。随着火车的缓缓启动,他的心也飘向了遥远的西藏。经过几天的颠簸,他们到了兰州。并在西藏工委驻兰州办事处休整了3天。休整期间,办事处的同志为他们准备了路上吃的、用的东西。3天后,他们坐上了去往新疆方向的火车。一天后,火车停在了一个叫厦敦的小站上,云旦加措他们要在这里转乘全副武装的军车,去西藏。从这里,他们也开始了更加艰苦的行程。 刚开始,云旦加措他们是白天行进的,所以在甘肃的一段还都很顺利。有时也能看到村庄人家。但到了青海境内,他们就在夜间行进,路也越难走了。刺骨的寒风在荒原上肆虐着。大家只能蜷缩在军车里,互相依靠着,用各自的体温为同志“取暖”。路况越来越差,确切地说,已经没有成形的路了。不得以,只好下车来搭起棉帐篷休息。所有的人都只能铺一张薄席子,一张长四尺、宽两尺的毛毡,盖一个四斤棉花的被子。这抵挡不了寒风的侵袭,大家只好蜷缩在薄被子里,半梦半醒地睡上几个小时,等待第二天更艰难的行程。 就这样,车在戈壁上、草原上跑了7天,才到达拉萨。在这7天里,车一直是在简易的路上行驶。没有桥梁、没有涵洞。遇到小河,如果汽车过不去,就卷起裤子淌着水过去。“现在想起来感觉是很苦,可那时候真的没有这种感觉,什么苦呀、累呀,都好像不存在一样。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年轻,有精神支柱,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到人民需要的地方去。”云旦加措说。 在西藏工作,无怨无悔 到了西藏后,经过一段时间全封闭的学习,云旦加措被分配到了情况复杂的南木林县——那里有小股土匪的不断骚扰。云旦加措和工作队到达那里后,主要工作是“争归、争降”,平息叛乱。“争归”就是争取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早日归来;“争降”是争取叛匪尽早投降。 云旦加措在南木林工作了一年半后,撤回了日喀则。经过20天的短暂休整后,他又被分配去了萨嘎县。从日喀则到萨嘎,汽车沿着草原上留下的车辙行驶,差不多是边修路边走。这段现在坐汽车仅需要8个小时的路,云旦加措当年走了整整18天。 萨嘎是日喀则最西的三个县之一,靠近中尼边境,海拔4600米,没有人烟。萨嘎汉语叫“白土”,意思是寸草不生的地方。云旦加措他们到那里的时候,整个萨嘎县只有三个群众——两个瞎子,一个老头,其余的人都跑光了。在那里,他们白天的工作就是拣牛粪。“我们除了警卫外,其他人分成几个小组去拣牛粪,先要保证生存”,云旦加措说。到了晚上,好学的云旦加措就点着洋蜡,趴在洋蜡箱子上写文章。 在回忆起那段军旅生活的时候,云旦加措这样说:“那个时候,我就一床被子,打起背包,说走就走,毫无牵挂。而且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今年70岁的云旦加措在西藏工作了32年,在西藏娶妻生子。现在,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还在拉萨。他说,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儿女也会埋怨自己,为什么当初要去西藏。云旦加措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赶上了那个年代。我的很多同学、同事都牺牲在西藏,想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云旦加措陷入了沉思。 二、在兰州想念拉萨:西藏,永远的诱惑 人物:高智华 甘南人 藏族 1987年进入藏地, 在西藏工作了7年,1993年调回兰州,现任西藏驻兰州办事处副主任。 虽然,离开西藏已经10多年了,高智华还会经常跟女儿讲起自己在西藏的生活。女儿不相信:“爸爸,真有那么苦吗?”的确,零下3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棉大衣,烧着牛粪,和许多人挤在一个帐篷里……对于孩子来说,这种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对于我们这些至今还没有去过西藏的人来说,在头晕、胸闷,极度缺氧的情况下睡在铁皮房里的事情是那样的遥远。然而,所有这些“不可想象”的事情却都在高智华的藏地生活里发生了。这一切都缘于他深深的西藏情结。 “在我的身边有很多老同志,他们都在西藏工作了很多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虽然我也去西藏工作过,但比起这些老同志,我的事也就不值得一提了!”当本报记者提出想采访高智华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时,他谦虚地说道。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高智华作为80年代末进藏的典型人物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1、诱惑与决定 1987年1月,寒冷的冬天还没有结束,甘南比起兰州还要冷许多。自从大学毕业后,高智华似乎已经习惯了在甘南的这种固定生活方式,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基本没什么业余生活,这样单调的生活一过就是两年时间。 两年后的一天,高智华在单位听到一个消息:祖国正号召有技术、有文化的人去援藏,报名时间有限。去西藏的人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干够8年后,就可以回内地,相应的可以提级、涨工资,家属还可以转成城镇户口等。“当时,并没有多想,至于优惠政策也只是一个参考而已。或许是厌烦了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或许,自己本来就是藏族人,而西藏对于一个藏族人来说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总感觉去西藏就像回家一样,这种感觉很奇特!”年仅23岁的他果断地报了名,在意向协议上签了字。 现在回想起自己的决定,高智华还是很欣慰,他认为当年很幸运地作为援藏干部去了西藏,才会带给自己更多的人生阅历和难以忘记的西藏生活。 2、进藏路上,我后悔了 所有手续办理妥当后,就该出发了。高智华只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后,和进藏的其他人员一起坐汽车启程了。按照他的回忆,当时的进藏路线应该是:甘南-西宁-格尔木-安多-拉萨。途中只住了三个晚上,其他时间都在赶路。 “一路上,越往前走就越荒凉,路上基本没有什么人烟,路况也不好。本以为甘南的冬天就够冷了,没想到,越靠近西藏就越冷。当时,气温都在零下三四十度,尽管穿得已经很厚了,可人冻得还是受不了,在车上直打哆嗦。坐车久了就会很难受,想下车活动活动,可刚一下车就感觉到头疼、恶心,这是明显的高原反应。”回忆起当年进藏的情形,高智华记忆犹新,用他的话说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记得我们到了安多的时候,高原反应更明显了,安多的海拔是4600米,而在甘南只有2600米,此前虽在甘南生活了很多年,可海拔上升了2000米的时候还是受不了。晚上,路太黑,车没有办法再往前行走,我们就在安多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说是旅馆,就是那种铁皮小房子,没有生火,像冰窑一样,整个屋子黑乎乎的,被子也是黑的,几乎看不出一点白的地方。没有办法,条件就这样了,睡呗,还能怎么样?我们几个人眼睛一闭,钻进被窝,就这样挨到了天亮。一路上全是这样的情况。”说到这儿,高智华不好意思地笑了。或许,现在就连他自己都难以相信那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第二天天刚刚亮,高智华他们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又上路了。虽然休息了一晚上,可这时候头疼的快要炸了。“当时,有没有后悔?”当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时,高智华不好意思地说:“后悔了,感觉很后悔。干嘛要放弃安逸的生活跑到这里来受罪啊!当时甚至想掉头回来。可当咬牙坚持到拉萨的时候,感觉就好一点了。” 80年代末,从甘南到拉萨,汽车在青藏公路上行驶了整整五天。 3、艰苦而难忘的藏区生活 到拉萨后,高智华被分到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当时,自治区人民医院属于全国援藏的29个大项目之一,也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高智华在藏区的生活就此开始了。也是在这个时候,高智华才告诉了还在甘南的家里人自己的这一重大决定,当时他的父母都气得不行,坚决不同意他在西藏工作。后来,父母还是拗不过他,默认了儿子的“冲动”。 80年代末,西藏的经济状况还不是很乐观。“拉萨市只有两条路是柏油路,全长仅几公里。”初来乍到的高智华在拉萨市还是有高原反应,经常头疼头晕,容易感冒,很不适应。后来,他还得过一次肺水肿,因为自己是医生,所以发现得早,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就好了。 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里,高智华等一批援藏医务人员的到来,给这里带来了不少的生机。这个医院里医生很少,平时住院部只有3个医生,每个人平均3天值一个夜班。门诊也只有3个医生,每天看七八十个病人。从甘南到拉萨,高智华虽在工作性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因为地域的特殊性,藏区人民给他留下了终生忘记的印象。当记者问他在西藏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地说:当地的老百姓!“拉萨的老百姓心很诚,人都很纯朴,他们尤其对医生特别尊重。” 藏区当时的医疗设备很差,尤其像阿里、那曲这样高海拔的地区,更是这样。高智华他们好多次都被派往这些地方去讲课,做疾病普查。在那曲,他们看到当地的县医院几乎没什么医疗设备,只有一排铁皮房子,简单的几个药柜,里面放着几种常用药,有些甚至连一些急救药物都没有。当地牧民有病一般在县医院治,治不好到地区医院,实在不行就送到自治区人民医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谈话间,高智华回想起了发生在90年代末震惊全国的“那曲雪灾”。“雪灾发生后,几十万牛羊相继死亡,人员伤亡严重。我当时作为第一批救援医疗队奔赴那曲灾区。当时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个四川籍的女同志,身体状况特别不好,有的都休克了。在大雪封山后,医疗队基本没什么吃的,只能靠吃糌粑、干肉维持生命。那曲海拔在5000米,比拉萨还要高出许多,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我们穿着棉大衣,烧着牛粪。晚上几个男医生挤在一个帐篷里,但冻得人睡不着啊。”就这样的日子整整两个星期。 4、梦回拉萨 1993年的时候,在西藏呆了7年的高智华重新回到了内地,回到了兰州。 12年过去了,回到兰州的高智华依然没有忘记拉萨,西藏的一草一木都清晰地留在脑际,那里有纯朴、诚实的藏族朋友。“多少次我总是梦回拉萨,就像12年前一样生活,还有那场雪灾……”现已是西藏驻兰州办事处副主任的高智华依然怀念在拉萨的生活,想念着拉萨,他说西藏对于自己是永远的诱惑。 现在,他每年都有机会出差去西藏:“这与我第一次来西藏的感觉大不一样了,西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这一点真是让人高兴,公路已经修了四环,规划也很好。老百姓公共意识提高了,改变了以前脏乱差的印象,城市已经很干净了。” 而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也正是高智华所期盼的,他希望火车能早一点通车。“坐火车还是好一些,尽管现在可以选择坐飞机去拉萨,可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低海拔的地方再到高海拔的地方,一下子适应高原气候还是比较困难的。而坐汽车在路消耗时间太长,极有可能遭遇出了名的高原天。俗话说‘高原天,孩子脸’。在高原上行走,一天内也许可以经历春夏秋冬、也许可以经历6月飘雪的可能,这不是神话。相比而言,还是坐火车既安全又方便。” “现在,我经常会给15岁的女儿讲在西藏的事情。女儿不相信,会有那么苦吗?”对此,高智华有很多感慨,他觉得曾经在西藏的生活是很艰苦,但从人生的阅历上来讲,那里的生活就像烙印一样深深地烙在了心里,也因此让自己更加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三、在拉萨想念兰州:一个兰州人的拉萨生活 人物:杨庆军 西藏商报记者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或失之交臂,很多人都认为是缘分,而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之间的默契相融,我想也应该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就像身在他乡但念念不忘生我养我的故乡——兰州,就像生长着我的梦想并给我归宿的美丽拉萨…… 1、回到拉萨 当我第三次回到拉萨时,已是5年前的事了。 2000年8月末,我通过一篇《西藏随想》的散文,顺利通过了《西藏商报》的招聘考试,成为一名记者。记得面试时,考官问我为什么想当记者,我忽然想起了在十里店小学上学时,我的语文老师王兰贞,她经常在作文课上念我的作文给同学们听,有一次她对大家说,杨庆军以后可以做一个好记者。那时我并未在意,只当是老师在夸我。真正成为一名记者后,才知道王老师说得没错,这个行业还挺适合我,比较自由散漫,在早上可以睡个懒觉。 在这之前,我曾在号称“西藏江南”的林芝地区波密县做过三年教师,过着与世无争的逍遥生活。那时课很少,下班后在江边垂钓,在原始森林中采蘑菇,在酒吧里与藏族老师拼酒。后来,我忽然感觉自己这么年轻,就提前安度起“晚年”生活,实在太过份了。于是借学校取消高中部之际,回到了兰州,回到了日夜盼我回家的母亲身边。 但在西藏波密的三年生活,已让我的灵魄和雪域高原深深地融合为一体。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感觉无所适从。上海、广东的生活节奏我赶不上,也懒得去赶,兰州的空气污染80年代末异常严重,灰沉沉的云层和面色苍白的太阳,也令我整天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拉广告、做推销,豪无激情,也没成果,梦里面总是出现西藏的山山水水,蓝天白云。末了,在无所事事的两年东游西逛后,忍痛离开了老母亲,再次回到了梦中的西藏,开始了拉萨的记者生涯。 2、永别母亲 初做记者时,工资很低。我和一位四川的朋友合租住房。秋意渐浓,拉萨的早晚寒风刺骨,我们接连换了好几个地方,但廉价的房子都很破,夜晚的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我们紧紧裹着被子,被子上又压满了外衣。只要太阳一出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拉萨马上变得温暖明亮。朋友在十字路口边的街角修手表。我跑完一两条新闻后就坐在他的表柜旁晒太阳,看街上快速行驶的车辆,看面前闲庭信步的人群。每天如此。 四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当我正在编排版面时,六姐打来了电话,说母亲病危,让我第二天即刻赶回兰州。 年前机票难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连夜奔走,为我筹钱买机票,那天晚上,我梦见母亲穿着一件像唐装一样的新衣服,愁容满面地坐在我的床对面,看了我好久之后说道:姐姐们的日子都过好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从梦中醒来,一股寒意冷彻心骨。 第二天当我赶回兰州时已是午夜时分。在路上,我想母亲一定在等我。但一切都太晚了,通向家中的胡同两边,长长地排满了白色的花圈。 六姐说,母亲临终时在所有守候她的人群中寻找我。 我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记得当我决定再次回西藏时,年近70的母亲极力挽留,6个姐姐早已成家,父亲住在乡下,兰州的家中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人,是走是留?母亲的眼泪让我深陷矛盾。但最后,母亲还是默默地为我收拾行囊,因为她不忍心看儿子消沉下去。临行时,母亲背过身去,那天,兰州下了一场暴雨。 3、佳节倍思亲 和姐姐们安排完母亲的后事,我带着愧疚和懊悔再次回到拉萨。没能守候在母亲身旁,让我始终不能释怀。 生活还得继续。 四川朋友还在修表,但我白天去他那里晒太阳的次数少了。看书、采访、编排版面,总觉得如果再吊二郎当,就对不起在远处注视我的母亲。每次逢年过节,我和姐姐们都要互相通电话、听6个外甥在电话那头讲他们的学习和趣闻,顿感又回到了全家人团圆时的幸福时光。 在汽车七队的家属院里,过年过节就数我们家最热闹。特别是大年初二,6个姐姐6个姐夫6个外甥,从早上10点左右陆陆续续从十里店桥、西站、庙滩子赶来,不一会屋子里就挤满了人。姐姐们帮母亲在厨房做菜,姐夫们围着桌子开始划拳喝酒 ,6个外甥则缠着我讲故事听。我编一些乡下老鼠和城市老鼠的奇遇,用兰州话的对白把孩子们逗得前仰后合。中午饭做好了,大家围着桌子大吃一通,边吃边点评菜的味道,饭后姐姐们刷碗,外甥们上街买鞭炮,姐夫们大声划拳,目的是喝翻一个“现场直播”。 整个一天家里都是欢声笑语。临行时,被灌醉的姐夫则在姐姐的责骂下狼狈不堪地被抬走。院里的很多老人对母亲说,你们家才叫真正的过年。 这才是序幕。从初三开始,6个姐姐们还要逐家串门,我和母亲每天就应约去吃饭。随后还要去舅舅家,姨姨家,直到正月十五才告一段落。 在拉萨过年,我只能在回忆中孤单单地躺在床上看电视,或约几个朋友大醉一场。半夜醒来,把在兰州过年的情景温习一遍,随后在梦中吃起母亲做的哨子面。 4、朋友、面片与酒吧 在拉萨生活,最不能缺的是朋友。或许是思乡心切,我的好朋友中多数都是在兰州生活过的。 我们经常凑在一起,在街上寻找最接近兰州风味的牛肉面,风华楼、清香阁、泰成饭店,这几家的牛肉面还有点“兰州”的意思,但“牛肉面出了兰州就变味”的话一点没有错,吃不过瘾,只好约到一家揪起尕面片来。里面下点土豆,放点西红柿和菠菜,高压锅打开后,大家一扫而空,拍着撑起的肚皮直叫“满福得很!” 拉萨的餐饮业生意火爆。“菜根香”、“重庆香牌坊”等一大批全国连锁店绽放拉萨。入夜时分,各个火锅店都爆满。在餐饮汇集的德吉路,晚上的停车难让拉萨人头痛不已。 饭后,又是酒吧的登场时刻。什么“雪堆白”、“矮房子”、“生活在别处”、“冈拉美朵”,遍布城市每条街道的酒吧或灯红酒绿、或温馨怀旧、或简陋舒适,或本土本色,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找到他合适的去处。 最近,有一个叫“70年代”的酒吧着实吸引了我。周末一有空,我们这帮70年代出生的人就相约“70年代”,看酒吧放的《霍元甲》录相,听酒吧播送着《青苹果乐园》等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酒吧的装修别具一格,我们曾经用过的黄军帽、黄书包等挂在墙上,崔健、Beyond乐队的海报令人怀想过去。 5、 等待火车 兰州有句俗话,“人想路不想”。拉萨和兰州的距离往往打消我回家的念头。一想起每次在这条路上坐车受的罪,就让我叹气。 今年5月初,我和妻子回家度蜜月,到唐古拉山口处道路堵塞,饥寒交迫地等了4个小时道路才疏通。挨到格尔木,坐上火车身体才算舒展开来,一到兰州东站,兰州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深深地吸了几口。这时亲切的兰州话从四面飘来,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终于又回到了家乡。 姐姐和外甥们早已候在接站口。晚上,6个姐姐和孩子们闻讯赶来,一顿拉条子伴着兰州话,让我醉在不眠中。 兰州变了,南北滨河路花团锦簇。立交桥、银滩大桥让兰州驶入快车道,曾令我沮丧的空气污染也被南北两山的绿树净化了,蓝天白云让人心情舒畅。 姐姐说,等火车通了,就陪乡下生活的父亲一起去拉萨。 10月12日,青藏铁路全线贯通。我和妻子憧憬着,每到过年,我们从拉萨坐火车出发,一天一夜到达兰州,在兰州和姐姐们相聚数日后,再乘火车去她的老家长春,过完年后回拉萨,和所有想去拉萨的亲戚朋友们,同乘一节车厢,集体奔向雪山草原深处的目的地……… 相关专题:青藏铁路全线贯通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青藏铁路全线贯通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