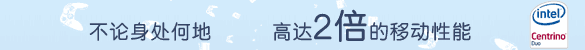|
|
|
|
|
一个教师的阅卷史:常因标准答案与出卷人争吵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9日12:52 南都周刊
 黄玉峰 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 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答案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 1990年7月8日,早上七点不到,黄玉峰就走出位于江湾的家门,这个质朴憨厚、阔嘴大鼻,貌似农民的中年人,提着一份蛋炒饭两条煎带鱼,怀着一种责任感,要横穿大上海,赶往位于上海西部的华东师范大学高考语文阅卷处。 那一天,黑色七月的影子罩着全国数百万考生。那一年,黄玉峰是上海市重点中学复旦附中的语文高级教师,6月底,他向学校申请去高考阅卷。那时的阅卷名额,由有关方面分配给各校。 在黄玉峰心中,阅卷官神圣无比。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阅卷官的级别都很高。唐时乡试,主考由学政担任,负责会试的须侍郎一级,至于殿试,由龙目御览,更令人生畏。当他还在读小学时,最敬畏的就是阅卷官,认为他们最有学问,且有生杀予夺之权,那时他调皮捣蛋,常常是红灯高挂。后来,他看到连环画《董一了》,说的是由于阅卷官的误会,使董一了连中三元,这不禁令他神往,祈祷有一天,阅卷官也糊涂一下,给他一个好分数。 不料30年后,他自己竟也做了阅卷官。这个提着午饭上“战场”的老师,没想到从此把他对阅卷的敬畏感打得荡然无存。 带饭的阅卷官 1990年的高考阅卷条件很苦。在黄玉峰的记忆里,阅卷处设在教学楼里,阅卷采取流水作业,四五十个老师,分大作文题组、小作文题组、文言文组和全国卷组等,试题由两人批阅复核,再由组长抽查。 黄玉峰分在大作文题组,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教室,散布着二三十个老师,每人面前厚厚一叠试卷。看到好卷子,有人奔走相告;看到差卷子,也有人骂娘。 正是七月,教室里连吊扇也没一个,窗上没帘子,阳光直逼进来,教师们的汗水直往下淌。阅卷量大,人手少,时间紧,批一篇作文大概一分钟,连擦汗的空都没有。几个领导从外面搬来了摇头风扇,一会儿吹吹你,一会儿吹吹我,一会儿吹吹饭菜。到了中午,路近的赶回家吃饭,路远的要么上街填肚子,要么带了饭,放点开水,吞了下去,稍事休息又接着干。几天后,阅卷官就辞去了几个。 一周的阅卷结束,黄玉峰领到的报酬是每天25元,扣去预支的盘缠,已所剩无几。晚上回到家,将劳动所得交给每天早起做饭的妻,脸上颇有难色。他又想到,在匆忙中,自己未必不制造了一二个“董一了”,怎么对得起寒窗十二载的学生?内心就无法平静了。 带饭阅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7月13日,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慰问时。那一天,副市长看到教师桌上的八宝粥,大为感慨:这怎么行! “高考阅卷,掌握着生杀大权,关乎千万考生的命运,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古时考卷要另请人用红笔誊抄,以免舞弊,可谓用心良苦。现在已非科举时代,对阅卷反而如此轻视。”黄玉峰说。带饭问题曾使他如哽在喉,后来在报上发表文章,借讲阅卷条件之差,调侃自己在冥冥之中也会草菅人命,委婉地批评有关方面对阅卷没有足够重视。 标准答案: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给黄玉峰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是带饭问题,而是每年都有的冲突,和阅卷老师的冲突,和出卷老师的冲突。 这个后来被传媒和教育界称为“语文教学叛徒”的特级教师,1990年时43岁,却依然有着青年人的纯真、率直,视人格独立与个体尊严为生命,以民主与科学为教育理念,眼里容不下沙子。在他心目中,作文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那种让学生完全按照标准答案去迎合出题意图的教育,不过是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前两年,黄玉峰自感人微言轻,并不那么锋芒毕露。第三年,其他阅卷老师发现,这个黄老师眼光很凶,从一堆卷子里,几眼瞄过去,就能发现哪些是一类卷,哪些是二类卷。很快,他成为作文组组长、语文阅卷中心组5名成员之一,秉性渐露。 1992年,上海高考的大作文是《遥望星空》:夏夜的星空,人们往往由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慨而产生种种思索,请以此为题写篇短文。 这一天,黄玉峰在休息时,翻到一份卷子。一看,内容不错,考生遥望星空时想起已逝的老师,决心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再一看分数,怎么是22分?黄玉峰拿起卷子就去找阅卷中心组组长王光祖。据说该文偏题,没点明“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要求。黄玉峰急了:这怎么能算偏题呢?作文点明老师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也表达了那层意思。最后该文被定为43分。 争论似乎此起彼伏。阅卷中心组有一个修正章。有时当众说不一,黄玉峰就索性敲一下修正章,直接把分数改过来。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有一次,黄玉峰在批阅大作文时,一抬头,发现卷子上头的小作文打了零分。据说该作文文不对题。10多年后,黄玉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衡量一篇作文有很多标准:主题、审题、结构、语言,即使偏题了,也不能打零分! 分歧并非偶然。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5人的答案都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 谁扼杀了他们的个性? 在朋友眼里,黄玉峰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禀赋和雅趣,他吟诗缀文,自成体式;挥毫泼墨,独具风骨;书斋静坐,思古忧今;悠游天下,逸兴横飞。他更以文人的姿态介入语文教学,作文于他是快乐而彰显个性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个个性色彩极为丰富的文人,似乎注定要在高考作文中看到太多遗憾。 1995年,上海市中考作文是《母爱》,一时母亲早逝的文章比比皆是;高考大作文是《责任》,于是,大唱高调的《责任》没完没了。黄玉峰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的阅卷情况: 面对着令人心烦气闷的八股腔,阅卷官们笔底踌躇忧心忡忡:板着面孔的说教,随意编造的故事,似曾相识的片断,从三闾大夫写到周总理,从孔繁森写到王宝森,百篇类似,千人一面,偶见一篇清纯的,便拍案大呼:难得,难得。 休息时,教师们大叹苦经。一位白发长者忽出惊人之语:我有一诗,可解诸位之忧。诗云:啥个叫责任,唱唱孔繁森,谈谈钱学森,骂骂王宝森,联系中学生,稳得基准分。语未毕,一片无奈笑声。笑声过后,忽然一片寂静,阅卷官们陷入沉思,什么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责任? 那一年,黄玉峰也在感慨:教书30年,越来越不知怎么教学了。流行的语文教学,多是老师讲学生听,把好端端的文章割得支离破碎,把平常的作品吹得天花乱坠。为敲开大学之门,学生都成了急功近利者,听讲先问考不考,不考的,听不进;讲读书,太遥远;讲做人,更反感。任你口吐莲花,却不过是顶着石臼做戏。 是什么扼杀了学生的个性?这似乎不仅是教育问题。在黄玉峰看来,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年代,人们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评价学生的语言能力,个性表达被视为洪水猛兽;此后,高考作文几经变化,从泛政治化到道德说教,到个性表达,再到多元时代,人们的个性表达空间在逐渐拓宽。只是在转型期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时常被放在突出的位置,部分制约了学生对生活的思考和体验式表达。 与1995年作文的千人一面相比,1996的作文《我的财富》,却忽如杂花生树。黄玉峰看好这个题目:“具有人文精神,可反映考生的思想水平、情操、理想乃至爱好,选材范围广,出题无偏题离题之虞,又限以‘我的’,可避免套话、老话、大话、空话。这对于语文教学中局限于课本知识的做法,无异于敲了一记警钟。” 这个强调个性的题目,却给阅卷带来了难度。考生之见解,千姿百态:金钱、书籍、草坪、阁楼,是财富;青春、健康、毅力、自信是财富,知识、经历、挫折、失败是财富,传统、音乐、微笑是财富。到底什么是财富?如何统一评分标准?阅卷进入第二天,进度仍无法加快。阅卷老师为此展开了争论。黄玉峰积极地为个性作文鼓吹: 有同学写道:没有财富就是我的财富,因为没有财富,就促使我努力进取,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功。对于这样的文章,能说他跑题吗? 有同学写道:邓小平是我的财富,我们经常说,邓小平是国家的财富,民族的财富,但如果他看过邓小平著作,把小平精神引入生活,你能说他离题吗?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朗朗乾坤,本无废物,各人有各人的财富,各人有各人的财富观,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真有体会,皆无不可。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