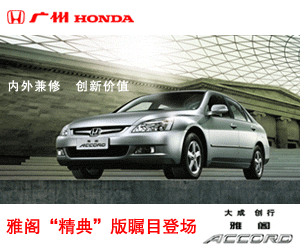|
|
|
|
|
十三不靠尹丽川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31日09:36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梅倩 她的电影情结一度被搁置,处女作《公园》拍了29天,尹丽川用它书写自己的父亲,父亲看过后说了一句“挺细腻 的” 号称自己“十三不靠”的诗人尹丽川,从外表看来和其他在南锣鼓巷泡吧的北京女孩并没有什么两样,她穿着一件卷 毛狗图案的白色T-shirt、牛仔热裤,精瘦、爱笑,看不出江湖上流传的“酷阿姨”风范。 她会在半个小时内连点3根烟,每根抽了不到1/3就按灭在烟缸里,也会在披头士《佩伯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的 歌声中说,“我其实挺中国的”。 将近一年的时间,她几乎没有写诗,却加入“云南影响”新电影项目,写了一个父亲替女儿相亲的剧本,执导了电影 处女作——《公园》。 眼下,她的第二部电影开机在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尹丽川身上,“导演”这个名头将与先锋诗人、“下半 身写作”代表人物、70后偶像、美女作家等称号并存。 被搁置的电影情结 尹丽川的电影情结始于大学时代。 在重庆、贵州、北京辗转多个学校之后,1992年尹丽川来到北京城南一座不知名的高中复读,结果成了那所学校 唯一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读书时,她开始接触当代西方文化。 有一天,一位朋友给她拿了一本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局外人》。“那是我看的第一本现代意义的小说。”尹丽 川说,“当时,感觉非常震惊。” 很快弗洛伊德的哲学、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的摇滚和诗歌、台湾的《电影馆》丛书和法国电影,也出现在尹丽 川的视野内。她说,一下就有了“西化青年”的感觉。 “青年时代挺悲观、叛逆的,可那时的精神武器只有罗大佑、齐秦什么的,忽然发现那些东西西方早就有了,有一种 找到组织的感觉。”尹丽川说。 1996年毕业后,尹丽川去了法国巴黎,在ESEC电影学校学了一年基础理论后,她选择了纪录片编导专业。 尹丽川用“安静”来形容在法国的三年时光,“看了一些电影,适当地聊了一些天,比我在中国过的平淡多了”。 1999年,回到北京的尹丽川写了几个纪录片大纲。“一看题材人家说肯定做不了,当时也没有DV时代的概念。 按我这个性格,让我去为这种事儿去奔波,好像也不太可能。”就这样,尹丽川的电影情结被暂且搁置,开始了写作。 2005年,尹丽川去了一趟西藏,她在左臂上纹了一个蝎子图案的刺青,同时觉得远离了“在这个圈子里写东西的 烦躁感觉”。年底的时候,“云南影响”的总制片人罗拉约尹丽川见面,问她有没有兴趣参加,拍一部故事片。尹丽川讲了3 个故事,在谈了大约1个小时后,罗拉说:“咱们签约吧。” 写剧本前,尹丽川想起以前曾看过关于在北京中山公园父母替儿女征婚的新闻报道。为此,她特意跑到中山公园,那 里的情景让她震惊:一二百个老人拿着牌子,上面写着子女的征婚条件。“一个现象必须要还原成一个故事,我就想起一个父 亲和一个女儿。”尹丽川说。这就是《公园》的故事雏形。 用电影书写“父亲” 《公园》在云南昆明拍摄仅用了29天,尹丽川说,再拍不完也就没钱了。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父亲高远山突 然到来,打乱了女儿高小君的正常生活。为给女儿挑个终身依靠,父亲到昆明的翠湖公园给女儿征婚,那里有一个自发形成的 父母为儿女征婚的聚集地。小君已有一个艺术青年男友,但为安慰父亲,被迫去公园约会。在相亲的过程中,父亲认识了一个 为儿子征婚的母亲,小君又萌生了为父亲找个老伴的念头,这对彼此深爱的父女却总是互相伤害。 “这里有我的影子,而且不是一点点。”尹丽川说,“父亲,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崇拜,到反 抗,到伤害,到对持,到和解,到学会爱??” 尹丽川出生于70年代,她说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悲观”而“叛逆”。“以前我父亲挺专制的,他太想我考上大学了 ,所以我就不能有别的生活。”尹丽川说,“我总觉得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失望,特别伤害我,让我活得特别痛苦。” 尹丽川曾经用两年时间,试图用文字书写自己的父亲,直到《公园》的出现,才完成了这个心愿。尹丽川说:“我父 亲希望我考大学,就像这个父亲希望女儿有个好归宿。希望都是用爱的方式表达的,你不好抗拒爱啊。”在尹丽川看来,父母 与儿女的隔膜是一种“没办法”的事情,其中也有时代造成的无奈。“父亲那辈人没完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那个时代 太捉摸不定,他就把这个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尹丽川说。 在影片的结尾,父亲高远山决定回自己的家。临行前,小君和男朋友陪父亲去公园划船。船到湖心,三个人静静地坐 着,父亲神色平静,深感自己已完成了为人父的责任。 虽然在这个电影中忍不住“抒发一些积攒多年的怨气和对父亲的不满,但更多的会是体谅与妥协,甚至仅仅因为父亲 们老了”。 一个朋友给《公园》的评价是“不够残酷”,而尹丽川的父亲在看过了《公园》后,只说了一句“挺细腻的”。 传统的人就是先锋 尹丽川身兼《公园》的编剧和导演,再加上她诗人和作家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新浪潮时期开始拍电影的著 名小说家玛格利特·杜拉斯、阿兰-罗伯·格里耶,以及戈达尔、特吕弗等导演和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提倡的“作者电影 ”。 尹丽川觉得“作者电影强调作者、原创、表达的愿望,这个肯定是对的”,但对狭义上的“作者电影”却并不认同。 她说:“有一种作者电影挺自我的,为了表达一种观念,而造成一种理解上的隔膜。久而久之,好像就是为了反对电影工业。 ” 《公园》的故事体现着传统的价值观,整个影片也体现出一种沉稳、平静的风格。尹丽川引用了著名诗人车前子的一 句话:“现在传统的人就是先锋。” 尹丽川觉得,既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结构的时代,先锋的形式反而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一些沉稳的、有价值观的 东西,网络时代需要的是“建构”,“电影起码应该言之有物”。 “电影对我来说不是承载哲学,甚至也不是政治和社会态度。”尹丽川说,“电影只是讲人的,应该有沟通性,让人 明白。”尹丽川说:“每个艺术都有一定的限制、一定的特殊性,电影为什么被归为流行文化里面,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 我对电影热爱,就是因为觉得它讲了一个故事,而且是讲人的。” 大片也需要商业的真诚 《公园》和“云南影响”项目其他9部电影走的都是小片路线,成本都在300万左右。罗拉希望,这10部影片能 团结成一股力量来争胜于一两部好莱坞大片。 尹丽川说:“我不存在对抗,跟父权不会,跟好莱坞更不会了。”她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就是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 ,觉得“挺好,挺可爱的”。 “大片还是存在娱乐价值与钱的流通的价值。”尹丽川说,但她觉得大片需要做到“真诚”。 “我觉得两年前的《金刚》就很真诚,因为这个导演从小就有这个梦想,就喜欢金刚。”尹丽川说,“说实在的,陈 凯歌喜欢大片吗?他不喜欢。陈凯歌当初不就是一个文艺青年吗?他也不喜欢游戏,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怎么可能喜欢游戏的概 念呢。所以就别弄《无极》(那样的电影),太不伦不类了吧。” 尹丽川说:“没有一个剧本能满足所有人,像《黄金甲》这样的大片满足不了中国文艺青年,也满足不了外国人,他 们还是要说一点点东西吧,不能什么都没了。”她觉得有了这“一点点东西”,就能做到“商业上的真诚”。 回想下半身 《公园》让尹丽川以新生代青年导演的身份频频见诸媒体,差点让人忘记了她的另外一个身份——先锋诗人。 1999年夏天,著名诗人黑大春喝醉了,说特别想朗诵。尹丽川说这有什么难的,就做了一个关于纪念阿根廷诗人 博尔赫斯的诗歌朗诵会。那次,尹丽川认识了车前子、莫非、树才、侯马等诗人,他们让尹丽川“对诗人的不良印象大为改观 ”,于是开始动笔写诗。 在成为诗人半年之后,尹丽川就和“下半身诗派”一起站在了诗歌界的风口浪尖上。2000年5月,沈浩波拉尹丽 川“入伙”即将创办的诗歌民刊《下半身》。尹丽川和聚集在这本刊物周围的70后诗人沈浩波、朵渔、南人、巫昂、李红旗 等,被称作“下半身诗派”。 在《下半身》的发刊词《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这些诗人提出了“下半身写作”的概念,坚持“一种坚决的 形而下状态”,“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和“一种肉体的在场感”,反对“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 、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 诗人伊沙说这篇宣言,“在90年代初期便有人私闯禁区的、中国新诗的身体写作由此形成理论和一种至关重要的写 作原则”。 新世纪之初也是网络时代的开端,诗江湖、灵石岛、诗生活等十余家诗歌网站突然冒起,成为诗人自由发表作品的阵 地。从2000年开始,尹丽川几乎每天都混迹于“诗江湖”,发表了《情人》、《退休工人老张》、《妈妈》等作品,但她 说自己在2002年之后就基本不去那里了。 现在回头看“下半身”,尹丽川说:“本来它就不是一个诗派,它是一个民刊。大家觉得各自的方向很相似,那时候 大家真的都很年轻,很有热情,但生活也好、写作也好,总归不是集体的。” 对于“下半身”,尹丽川曾有这样的评价:“下半身精神可嘉,但作品尚未到位,有不少偏差。”尹丽川说这种偏差 是“被一种理念所迷惑”,“提出了一个理念去反对另一个理念”。她说:“当时你写我也写,互相鼓励,是挺可爱的,慢慢 就会觉得不应该是这种大跃进的形式。” 同时,她也在反思网络的作用:“网络的即时性挺可怕的,诗不一定是要大家叫个好,或者批判一下,我觉得它应该 沉一沉。” 去年,女诗人赵丽华的诗歌引发网友、诗人、作家旷日持久的争论。在自己的博客上,尹丽川把这称为“一场娱乐事 件”。 “浮躁就是希望把一切都娱乐化,像杨德昌去世,还把他的前妻扯出来,这已经过了底线。”尹丽川说,“社会现在 没底线了,但我当然还有底线。我的底线就是,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 尹丽川说:“多数人都在忙着识时务,忙着恶搞,忙着解构,忙着出十五分钟的名,我的一部分也在其中。但是另一 部分的我,可以坦然对朋友们说:就写诗,就把酒谈理想。” 谈到理想,尹丽川大笑:“我就是有理想!就生活这些破事儿,没有理想就太没有意思了。” 南锣鼓巷的这个咖啡馆里贴着一张褪色的、诗人顾城的画像,一角已被撕开。当记者请尹丽川坐到海报前拍照时,她 拒绝:“我就别去糟蹋人家了。”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