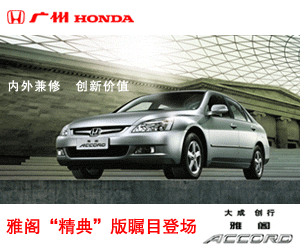|
|
|
|
河南矿难井下75小时求生纪实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6日02:30 中国青年报
李江红见到丈夫。国新供图 7月29日中午电话接通不久,朱念群就听到了媳妇的声音。“你啥时能出来啊?”媳妇带着哭腔嚷道。 “没事儿,下午就出来了。”朱念群对着话筒喊。他这话也是冲着身边68个弟兄说的。实际上,究竟能不能出去,他心里也没底儿。 自1983年到矿上工作,朱念群历经大大小小的事故,包括1987年的瓦斯爆炸,“埋了17个兄弟”,他都侥幸逃生。但是像这样被困在井下,干了24年矿工的朱念群也是第一次遇到。 那几天,接了家里电话的人哭,不接电话在旁边听的也忍不住哭。特别是第二天第三天,听别人打电话,就都想想自己的家人。 39岁的采煤队矿工张少民就一边抹泪,一边寻思,我的家人咋都不打电话咧。井里进水前,他正在算账:“大儿子刚去广州打工,要安家钱。今天怎么着也能搞个14、15窖,一窖煤7元钱……” 老朱就出来做思想工作,你哭,别人听见了也难受,你哇哇的哭也帮不上啥忙,起不到作用。 有时老朱接电话,对所有家属都说“都在,都很好”,也算表达了矿工的意思。 兰朝军给媳妇儿打电话说:“家里头那电视机下面还窝着2000元钱,你啊,把那钱拿上,买几件好衣服……”倒是有人给他开玩笑:“还弄啥2000元钱哦,要真是出不去了,矿上给你家发个20万元。你家媳妇儿拿钱就……就要去找个小男人喽!”好些人都笑。 机电队维修工张全周本不该被困井下的。他本是零时的班。可程自昌因为有事,要求跟他换班,结果却遇到了灾难。赵长林跟他开玩笑说:“你能得不轻,叫你跟人家换班,人家走了,你却替他困在这。” 30日中午,宁保师的老婆孔贵荣找到矿联防队员胡二国,让他帮助打电话询问井下情况。 “你就给她说我没事,不用寻。”宁保师电话都没接,让朱念群代为回复。 宁保师认为,电话是大家的生命线,不能老占线。而如果自己接了,老婆会罗嗦半天,哭个没完。 淹井事件发生的当天,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立即冒着暴雨赶赴现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被困人员。 7月29日20时10分,徐光春与被困矿工通电话,关切地询问他们在井下的情况,“氧气够不够?”“呼吸怎么样?”“有没有受伤的?” 他动情地说:“矿工师傅,请你们安心、放心,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抢救出来,你们不要慌乱,要保持体力,节约用灯,我们已开始组织抽水,也在给你们通风供气,你们一定要互相帮助,树立信心,渡过难关!” 7月29日,攻坚战是把河道中漏水的井口堵住。从下午1时一直到次日凌晨3时,在铁炉沟河奋战的武警官兵和消防官兵有300多人,武警官兵来自洛阳和三门峡两地,消防官兵来自三门峡所辖湖滨区、陕县、义马市、灵宝市等各消防大队。 大雨下了多长时间,战士们就奋战了多长时间。 7月30日18时30分:大家都饿得挺不住了 通风管送来氧气和牛奶 7月29日20时,安全员郭石屯饿得有点受不了了。 28日晚上,他与朋友聚会,喝酒有点多,早上没来得及吃饭。现在饥肠辘辘。 朱念群等人不答应。“收食物时都说过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吃。我们不知道要困多长时间呢!” 30日早上,张群官也受不了了,闹着牙疼要吃东西。“我先把自己该分的那份吃了,你们再吃的时候我不吃。好不好?” “你牙疼的原因是上火,你上火的原因是心情太急躁,你现在要心情放松。”宁保师劝道,“你牙疼是上火,牵涉不到生命。” 到30日早上,大家已经饿了一天一夜,也有人要求吃东西。 但自救小组认为,除非大家都实在挺不住了再说。 30日18时30分许,朱念群等人决定给大家分食物。 因为,有许多工人反映自己已经饿得撑不住了。朱念群他们一看也到时候了。 根据井上的电话通知,可能会想办法往下送牛奶。 “大家原地不要动,有人送到你跟前。”各队负责人开始给自己的队员分发食物,每人要么半个烧饼,要么半个馒头,要么一个小包子,要么一个鸡蛋。 从29日早上6时30分左右吃早饭,到30日18时30分许,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一夜,宁保师已经36个小时没吃东西。 宁保师终于分到了半个烧饼。一小块一小块地吃着,细嚼慢咽。 他带的那两个被水泡软了的烧饼,特许被其他两个矿工一人分到一个。 在此之前,宁保师已经喝了两缸子水。 在快到安全区域时,他们把泵站的水管打开,接了一保温桶清水。旁边有一个搪瓷缸子。清水可以随便饮用。 但有些人却一次水也没喝,因为没有心情。 7月30日,获悉井下被困矿工未感觉到潮湿、反而感觉干燥,指挥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通过查阅井下图纸资料,指挥部判断井下被困人员一定处于被淹巷道上方的一处高台面上,此处不仅正好是一处通风口,而且该处正好有井下降尘管道通过,并且还装有控制水流开关的高压泵。 而这时,井下人员由于新鲜空气被巷道阻断、二氧化碳含量增高,开始出现胸闷等症状。指挥部果断决定:先试着压入医用氧气保证大家呼吸用氧。 特制的三角管阀被以一定角度焊接到通风管道上,医用氧气罐成功与送风管道接通。 半个小时后,井下打来的电话让人欣喜:“感觉舒服多了。”此后,医疗专家根据井下人员报上的身体感受,不断调整送氧量,让井下的空气与正常空气达到最接近值。医用氧气罐被连接到管道上,这条线路从此被称之为“生命线”。 又一个大胆设想被提了出来:通过送气管道向井下输送新鲜牛奶。这一中国煤矿抢险史上从没有过的举动一度让很多人非常担心:送奶就要停气停氧,会不会给井下矿工兄弟造成伤害?但经过几个小时缜密的规划和计算,指挥部认为10分钟时间不会出现大问题。 400公斤鲜牛奶组织到位后,现场人员开始向管道中先压入净水清洗内壁油污,随后鲜奶被缓缓压入了管道之中。现场人员的心再一次地提了起来。 “报告指挥部,俺都喝到鲜牛奶了,也都喝饱了,大家的矿帽里也都接满了。”7月30日晚,朱念群打上来的电话,让指挥部里一阵欢呼。 不少矿工都是头一次喝牛奶。从来也没喝过牛奶的张少民喝了一口说,“不好喝,腥味、豆味直冲鼻子”,他喝了半茶缸就不喝了。人家劝他,牛奶你没喝过,再试试,多喝喝就好了。 在中国煤炭工业的历史上,为井下受困人员成功利用通风管道输送氧气、鲜牛奶等,尚属首次。 72小时后:空气越来越差,大家都累软了 12人趟水寻找洞口 整整过了3天3夜,矿工们的情绪开始出现波动。 72个小时以后,里面的空气越来越差,好像这边气刚呼出来,又给吸了进去。大伙儿都累得软和了。 张少民寻思,“与其跟大伙儿待在这等死,还不如跳到水里,还舒服点。” 不过,副队长朱念群有严令,都待在平台上保存体力,谁也不准下水。 正寻思呢,张少民突然意识到坐在旁边采煤队的薛旭谦小解了半天还不上来,再等等,还没来。“半天不上来,这小子溜了?难道下面有路?” 于是,张少民也假装解手往坡下走。到那一看,薛旭谦在水边立着,正拿脚踢水。张少民悄悄过去跟薛旭谦“咬耳朵”:“哎呀,我怎么感觉水那边吹过来的风凉呼呼的,已经打通了?” 后面大个子董建方也凑了过来。张少民问他:“你个儿高,是不是能觉着上面有风哇?” 几个人一合计,“等着也是一死,要是趟趟水没准能摸着个洞口。就是淹死了,也少受点儿罪。”几个人嘀咕着,就开始游着往前面走。 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开拓队的,平时干得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活儿,边走还边说,“哎,这边有风、有风”。 这时采煤队的几个人也都跟了过来。“你们头前走哇。”水面上的空气好些,人也精神了,游得都挺快。 张少民脱下裤子,跟在后头,平时在家里也玩水,水性还不错。他把裤子担在肩膀上,一手抓着上面的钢管,抓一把,向前凫一下,一米、半米,摸索前进。一开始水面到巷顶还有一米多的高度,后来水越来越深,脚也打不到底,走到后来,水几乎淹到了巷道顶。张少民只好把头拼命地探出水面呼吸点空气,此时水面到巷顶也只有十几厘米,他们紧紧地抓住钢管,脖子仰起来,鼻子露在水面上,耳朵都贴在钢管上。 听见外面说话,吆喝声,虽然听不清,但还能清楚地听见“擦擦”的声音,还有水泵“吭吭”抽水时的轰鸣。 再往前摸,才发现淤泥已经堵死了路,还是出不去。 大伙儿只好回头。 这时,朱念群等人都脱了衣服要下去查看情况,见他们回来,都撵上来。朱念群上来拉着胳膊,第一个就“日骂”(方言)张少民,“你咋这样大胆啊!你不要命啊?我们要是出去了,没带着你,见到你媳妇儿,咋给人家交代?” 点了一下人数,这拨趟水的人一共12个。好好骂一顿,羞得12个人不敢上去。再加上采煤班班长,大伙儿都不敢回去,就悄悄溜到坡上,把身上湿透的衣服扒下来拧巴拧巴,一起蹲在40米坡道的中间。 待会儿就听见上头喊“上来吧,下头空气不好。”上去了,倒也没有人再说啥。 张少民琢磨着想将功补过,他摸到朱念群身边说:“我们刚才已经听见外头人擦擦的响声和说话声,能不能想个法子找个钢管啥的捣个窟窿。这样大伙就能出去了。” 朱念群听完开始打电话,向上面检讨:“我们这人没有组织好,有人跑到口跟前,连援救队的说话声都听得见,是不是能用钳子、钢管啥的捣个窟窿?” 外面很快给了答复:“好,我们马上想办法,不过里面的人安静些,不要太着急啊。” 8月1日晨:13米长的通道打通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 8月1日晨,两天多的排水,巷道顶板已经透气了。义煤集团张新科矿长传来指挥部的命令:改变策略,从淤积物上边扒开豁口,不顾一切爬着也要往前探,加快救人速度。 义煤集团石壕煤矿掘进队队长任耀和抢险队长焦胜利一个打头阵,一个随后,趴在水里往里拱,一边用铁锹往两边扒,一边把铲到的淤渣往后递。脏污的水淹到了下巴,能出气的空间只有几公分高,换气都得侧着脸。遇到撑巷道顶板的铁梁,就得把头没到水里。 就这样,爬着、扒着、掏着,硬是打开了一条13米长的通道。任耀隐隐约约看到前边有光影闪动,像是矿灯,心里一阵惊喜,难道是被困的矿工兄弟?他大声地喊,里面有人吗?就看见,灯光来回摆动,越来越近。任耀使劲儿伸长胳膊,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连拉带拽到跟前,又推着他的腰和屁股,交给了身后的焦胜利,对他说,“救着了,救着了”。 这就是第一个爬出来的矿工兰建宁。 任耀马上使劲儿地敲着通气的铁管子,又大声地往里喊话,“兄弟们,不要怕,你们得救了。捏着鼻子潜水快爬过来啊!” 每隔几分钟,任耀就把一个矿工从里面拽出来,拽出来的最后一个是支建煤矿采煤队副队长曹百成。任耀反复问他后边还有人吗?曹百成非常虚弱,还是清楚地说:“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本报三门峡8月5日电 2007年8月2日下午,河南省三门峡市,正在接受康复治疗的陕县支建煤矿获救矿工,见到了各自的家人。 本报记者 潘志贤 蒋昕捷 实习生 白雪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