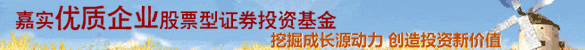|
|
|
|
|
少年杀母事件调查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9日18:11 南方人物周刊
 少年杀母事件  幽暗的城中村小巷,偶尔有老乡经过 图 大食 实习记者 林珊珊 本刊记者 尼克 蒋志高 一 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 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多年积累的仇恨得到释放,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1991年11月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07年6月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 其间,陈菊打开大门惨叫一声,但门很快又被关上。那就像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这幽暗的小巷的深处,有一个拐角,几栋四层高的楼房围成一口天井,张明明的家在这儿。抬起头,天空依旧是一条狭长的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米多宽的小巷两边房门紧闭,垂吊的女人内衣透着湿气,牛仔裤则似乎长年挂在一边,一动也不动。还有一个个小口子,连接更小的巷子,有时候,一个安静的小孩跟着一个女人拐进去,或者,一个谢顶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睁大眼睛瞪着过往行人。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光亮在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二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广州一家嘈杂的手机卖场,劣质的音响播出的音乐就像是暴发户在大声说话。 张柱良抽着红双喜,手微微地颤抖,烟雾轻轻袅袅悬浮着空中,他的目光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数十年后,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受这样的疑问,你收获了什么。张柱良的答案是:赚钱。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来到广州。想象中的广州很繁华,但不是那么回事。站前路那家大酒店当时还只是一个大土堆。下了火车,我看见到处是赛马的宣传,涌动的人头。我挤在人群中寻找大哥张光荣,来之前,他对我说,下了车说找河北老张,他们都认识我。可当时大哥在花都。当晚我睡在韶关大厦下面的广场,半夜一拳头打在我胸口,我惊醒过来,丢开旅行包逃走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车站晃来晃去,检查人员盯着你,你吐口痰,丢一片纸屑,就跑过来,罚款十元。我仅有的四十块钱很快被罚光了。我只能帮人提提行李,两三天就混过去了。 我跟随大哥卖黄牛票。那时火车站的生意真好,天天都像春运。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到了窗口,售票员就说没票了。我们就凑上去问,老乡,去哪的,帮你买票。我们很容易拿到票,他们售票的每天回家两个口袋满满全是钱。仅做了两三个月,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总问到便衣,而且,骗人这事我干不漂亮。当然,最无耻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敲诈的。他们夺过旅客捏在手里的票,“给我一百块,不然把它撕了。” 接下来将近十年,我几乎都在当保安,跟过服装场、酒吧、夜总会、地下赌场…… 1996年,你知道,到处都是歌舞厅。那时我在沿江路一家歌舞场当保安,圣诞节那晚,门票200块钱一张,等着跳舞的人排着长队挤在阳台上。那一年前后,我认识一群流氓。我们四五十人自称河北帮,帮人看场、收债和打架。老大一叫集合,我们就抡起水管、排骨刀,涌上去往人家背上胳膊上乱砍。有吃有住有玩,我们都很乐意。我们被抓进派出所无数次,又放出来。 当时,大哥承包了几家酒店的洗碗活,几十个工人都是去火车站找的那些没饭吃无家归的人,提供吃住,一个月350元,大哥每人赚上一百。老李是这些流浪儿中的一个,后来他结识了赌场总经理,就介绍我去当保安。老李后来失踪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长久的。 那是1997年,一个地下赌场每天赚上十几万。只要我站在那里,就会忍不住想赌。结果工资刚发,一眨眼就输光了。一想到该寄钱回家,我就特别紧张。到了年末,赌场闻风警方要大规模打击地下赌场。我们就自行解散了。 1998年,我在一家楼盘终于当上正规的保安,到了2001年,还混上了保安队长。可是,不久,开发商与物业分家。我又失业了。 我重新回到赌场,这下赌场都是先进玩法了,最主要的是玩老虎机,还有一些黑网吧。一次警察来检查,我们立刻赶走所有的少年,但还有一个少年玩得入迷怎么也不肯走,就被我们打了。再后来,他的妈妈闯进来了,操起凳子往电脑砸过去,我就骂她:“是你儿子自己要来的。我们又没强迫他。” 2003年,我开始和老婆在广州卖烧烤,到了2004年,老婆说儿子也大了,让他来帮忙吧。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瑶台,相依为命,靠卖烧烤为生。 三 这是瑶台,离广州火车站不远的城中村。一座不夜城,夜幕降临,它的黎明刚刚开始。浓烈辣椒味混着啪啪炒菜声弥漫在小巷里。夜晚九点钟,才起床不久的张柱良踩着他的黑色28吋自行车出发了。 车后架上躺着一个泡沫箱,里面堆着鸡翼、鸡腿、羊肉串、秋刀鱼……盒盖上倒扣着两张小凳子,茄子、菲菜陷在里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儿子张明明,骑一辆26式自行车。8点半,他准时从网吧归来,把一张沾满油污的长方形小桌子,烧烤炉紧紧绑在车架上。此时,陈菊刚刚上了香求完平安,关上灯,锁好门窗,也出门了。 张柱良经过一个小店,几个外省大娘在看电视扯家常,店主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微胖男人,几个小女孩呱呱地吵。往下走一点,有一个公用电话店。窄小的店面里,散散落落地在墙边摆着几部电话。 这一家人在三元里一带卖烧烤,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档,凌晨三四点收档,然后睡觉。中午醒来,切肉、洗菜、调料、串羊肉串。晚上再睡上两个小时,又出档了,日复一日,如今是第五个年头了。 这一天是2007年6月11日,只是时间洪流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日子,却足以拒绝这个家庭继续前行。 四 张柱良往左拐出小巷。这条街总是这么热闹。穿开档裤的小男孩在路中间嗑瓜子,鼻涕滴答、懵懂地看着你,中年男人围成一桌桌喝酒、搓麻将,小摊贩的玉米、番薯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手机店里各种音乐混杂着人声车声孩子的哭闹声鼓捣着人们的耳朵。 在路的尽头他向右拐,那是一条阴暗狭小的路,只能推着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到五点半,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站街女。 有时她们抓住他的手,“要不要?”他骂道,“每天都看见我经过,还抓!”他厌恶地甩开手。 可有时,他也心生同情。一天中午,他在街上乱逛,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穿着短裤,黑色男装背心,呆呆地站在前面。突然,她大喊大叫,闯进档口,拉住一个男人的衣角,哭喊着:“爸爸,别不理我!”那男人用力地踢开她,她又闯进另一家铺面,又被狠狠地踢在街上。他看着她,真想把她送到派出所。但很快,他打消了这种念头。这些人都认识他,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他只是想着,这个倔强的女孩子,一定是想不开,受不了,被生活逼疯了。 要是软弱一点的,就屈服了,不久后还会招来同乡姐妹。她们或许在火车站流浪,或许是离家出走的,被骗到一个地方,卖淫。在这个街头,他撞见过七八个神经错乱的小姑娘,有的乱跑乱叫,有的痴呆地望着天。此后,便永远地消失了。 眼下,这条路成了一个小经济地带,人们在这卖手机、食物、性用品、药品。 几分钟后,一家人挤出瑶台村,来到广园西路。一条宽阔的街道就在脚下延伸了,到处都是汽车,高架桥上的疾驰而过,地上的拥挤混乱。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