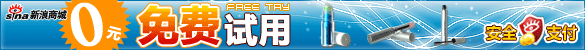|
|
|
|
|
交管局副局长与北京交通34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03日14:06 三联生活周刊
两个书屋近40平方米的空间里,69岁的段里仁包围在十几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中。走过全世界300多个城市的他,在每个地方用走路的方式去丈量当地交通,书屋里挤满了他拍的20多万幅照片。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段里仁提出把发展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交通作为中国交通工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提出把交通工程作为法规、教育、工程环境和能源结合的“五E”科学,这一学说被国外专家称为“段氏交通工程理论”。世界银行交通专家组特聘段里仁为“世界银行高级交通咨询专家”。 记者◎吴琪 交通奇缘 我与北京的交通发生联系,并且一投入就是30多年,说起来非常传奇。1973年北京饭店17层的东大楼修建完了,当时是全北京最高的建筑,用来接待外宾的。东大楼要装600套电视,但时值“文革”,我们自己供应不了天线,又没法进口。所以北京市找我这个在武汉大学研究“天线与电波传播”的老师,让我设计出600台电视只用一个天线的“共天线电视系统”。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正值六月天,我住在北京饭店里,完成“共天线电视系统”后就去长安街溜达。在南河沿交通岗亭,我看到一个民警忙得汗流满面。我非常好奇,问他在干什么,走进一看,他正在用手扳交通信号灯。扳第一下,东西方向绿,南北方向红;扳第二下,南北绿,东西红;扳第三下,某个方向可以左转弯~一共要扳七下,信号灯才用上一圈,然后接着扳下一轮。只要有车走,民警的手就不能停。那时候路上的汽车非常少,需要用上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也少。可我亲眼看到民警的全手工操作,还是很吃惊。 我问他为什么不用上自动控制技术呢?这刚好和我的专业相关。这位姓卞的民警非常有兴趣,马上就跟领导打电话,说“一位湖北老乡来到我岗亭里谈自动控制,说我可以不用手扳灯了”。领导一听也有兴趣,让我第二天早上去他办公室。第二天我来到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的办公室,这位领导说,周总理也在琢磨这件事情,希望交通信号自动化。但那时没有经费,事情就此耽搁下来,我回到武汉大学继续教书了。 这一年的“国庆”前夕,突然从北京来了两个警察,通过学校党委找到我。学校还挺紧张,以为我在北京出差期间犯了什么事。两位警察告诉我,我离开北京后,当时电子部部长王诤8月份提出希望北京交通指挥用上电子技术,万里同志也非常关心。开会落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怎样办,一位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说,两个月前有位武汉大学的老师来讲过这件事。于是万里发话:你们赶紧派人把他找来。 说起来非常有趣,我一次无心的闲谈,竟使自己后半生与北京交通紧密相连。从1973年开始,我和交通部的人一起,设计出了我国第一个红绿灯交通信号控制器。我查了整整一周资料,国内没一篇研究此类问题的文章,让人非常失望。几乎要放弃时候,好在我的外语不错,我从一本日文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电子控制的文章。文章后边的参考资料列表,让我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大海捞针似地查阅有了效果。我做成了路口控制器,独立设计了交通电视监控系统,在前三门做了全国第一个实验。 完成这几件事情后,公安部注意到我,刚好他们兼管交通的人生病了,借调我去管交通。那时候公安部下边没有专门的交通部门,我的工作属于治安科。我开始研究交通管理规划,同时钻研技术上怎样让交通现代化。那个年代马路上没有多少车,人群的流动性也不大,社会和领导们对交通不重视。第一台自动控制信号机在北太平庄实验时候挺成功,可是领导看了后,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段啊,你可不要犯技术至上啊。”计算机控制在前三门大街实现的时候,领导也说,“计算机又不能跳出来纠正违章,人是最重要的”。好在那时公安部治安局的解局长很支持,我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当时我国交通事故已经比较严重,我从1973年到1976年查阅了大量交通资料,国外交通管理现代化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建议领导派一个代表团去国外看看。我觉得应该像国外那样,把交通死伤的实际情况公布出来,让老百姓警惕。但是领导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伤亡数字是保密的,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庆幸的是,我“出身好”,家里是湖南益阳的贫农,在“反右”、“大批判”这些历次政治斗争中都没事,所以也比较敢说。 1978年我做完了第一份交通管理规划,提出派考察团去日本和欧洲几国看看,这几个国家都是发展节约型交通,充分使用道路,和中国的类型比较相似。于是我们15人的第一个中国交通城市管理代表团出国访问了。到了东京,在机场去酒店的路上,我们就看到派出所门口的牌子上写着“辖区去年交通事故死亡××人,今年已经死亡××人”,走到一些路口,也会有牌子提示。领导们大吃一惊,原来交通死伤是可以这样公布的。我们看到人家的马路上有车道、有护栏、有斑马线,领导们这才知道交通上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回国后,中国马路上才开始划车道线、斑马线。 日本和欧洲那时候汽车社会已经非常发达了。它们车多,却并不太堵,路上很少有警察,基本上是信号指挥,建立指挥中心、控制中心,这些给我们的触动非常大。1979年4月我们就从广州开始推广自动化信号机,北京容易堵车的崇文门路口、西单路口、东单路口也用上了自动化信号机。 北京的三次大拥堵 我虽然是学技术出身,但我非常明白,交通管理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活。交通社会与人类社会一样,车、人、路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才有交通,交通出了问题,就是一个综合管理的问题。我从1973年开始研究北京交通,1985年开始在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的职位干了13年,后来成为总工程师、北京市政协委员,这34年一直在研究北京的交通管理。 北京交通有过三次大拥堵,分别出现在1984年、1995年和2003年,每一次拥堵都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城市发展得太快,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很难预料到北京的交通需求增长如此迅猛。 1984年第一次大拥堵在中秋节前后,发生在早高峰,堵了半小时。我骑车到崇文门路口了解情况,那时候满大街的自行车动不了,机动车在自行车的包围中也开不动。人们没有过大拥堵的经验,非常急躁。当时道路条件差,人们居住在城里(现在的二环以内),而城外则是纺织、化工、钢铁等工业区,所以早上以出城的车辆为主,和现在正好相反。 这一次大拥堵给北京交通的触动很大,当时直接采取的措施有两条:一、路太少了,要修路;二、减少车辆,禁止4吨以上大货车进入二环行驶。第一条措施非常对,北京的路确实太少了,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除了长安街,其他路都不好走。中国是从人力车社会发展起来的,城市由胡同里弄组成,经历几百年时间发展成汽车社会,原有的城市格局肯定满足不了这种剧变。西方是从马车社会发展为汽车社会的,汽车初期行驶的道路、交叉路口与马车一样,所以它们只经历了城市格局的渐变过程,矛盾没有我们这样激烈。北京需要更多的路,这肯定是对的。当时的措施被称为“打通两厢 缓解中央”,我认为打通两厢是对的,但是即使打通了,中央的压力也是缓解不了的。 但是我对限制车辆行驶不太赞同。那时候北京90%的车都是货车,在交通枢纽没有形成以前,禁止大货车进城只会造成小货车泛滥。人们纷纷把4吨货车的运力分散到了3辆1.5吨的小货车里,结果路上的车更多,道路更拥挤。北京也曾经实行过机动车分单双号进二环。这种做法墨西哥等少数国家采用过,我不太赞成。交通需求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国家在特殊年代,曾经做过太多试图限制老百姓需求的事情,最后证明光限制需求是无用的。实行单双号也一样,原本一个单位只用买一辆车,可能是个单号的牌照,现在就会再买车去上一个双号牌照,对缓解交通压力一点作用都没有。 禁止大货车进二环的措施,在实行七八年之后取消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交通枢纽基本形成,外来大货车在三环外就可以装卸货物了,我们在交通上有条件禁止大货车白天进城了。 1995年第二次全城大拥堵来得非常突然,管理者想不通,怎么北京的路修多了,还是一样会堵呢?这时候的拥堵主要在交通路口,环路以内的交叉路口堵,全城大的交叉路口基本上都堵。西二环和东二环也非常堵。 这段时间我是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副局长,同时兼任北京市交通工程科研所所长。因为第二次拥堵主要发生在交叉路口,所以解决交叉路口的通行能力成为我花了十几年时间研究的课题。我一方面研究交通安全问题,怎样在道路上画线、安装护栏等,减少交通事故。另一个重点是解决北京拥堵,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来研究,怎么提高交叉路口的通行能力。 从中国的交通史说,先有铁路,才有公路。中国人先认识铁路信号灯,再认识公路信号灯。铁路信号灯强调的是“一慢二看三通过”,所以中国人脑子里留下的教育是,过路口一定要慢。但如果大家开车过路口都很慢,就极容易造成堵车。我提出路口交叉面积越小越好的时候,一些一线执勤的民警不同意,他们认为交叉路口越大越好。但是只有当交叉面积小的时候,才能缩短每辆车在路口通行的时间,才更容易疏通。 几个重点交叉路口包括西单路口、东单路口、工人体育场附近的场东路路口、西四路口等。每个路口面临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既要现场做实验,也要用计算机模拟。西单路口可以很好地利用胡同来做微循环,把左转弯车、右转弯车从胡同里分流出去。东单路口的胡同很难利用,但是这里路面比较宽,可以增加进口车道,将停车线往前移。 工人体育场附近的场东路路口自行车走起来特别乱,我们尝试在岗亭周围划定自行车禁驶区。但是实验的时候,岗亭的交警不理解,认为自行车和机动车拥堵没关系,不愿配合。我只得叫手下的工程师帮忙,一开始四个人,每人堵住一个方向的自行车,不让它们走到岗亭中间来。后来只需两人,每人堵住两个方向,一直到老百姓有了“自行车禁驶区”这个概念,那里的路面也畅通多了。西四路口当时南进口的车都堵到了丁字路口,西边由西往北的左转弯车特别多,所以增加南进口车道,西进口增强左转弯专用信号。这四个路口的实验做完后,他们的通行能力提高了15%?17%。 治理交通拥堵,没有什么特别灵的药方。当时大家的思路还局限于微观,只能根据不同路面情况,针对性地研究摸索。 2003年的第三次全城大拥堵则更为严重。这次堵车由市中心蔓延到市郊,大面积的堵车,城市道路弱不禁风。一遇到交通问题上的风吹草动,路面就瘫痪了。不仅是二环、三环堵,连刚建好不久的东四环也堵了。北京的拥堵,由上世纪80年代的个别点拥堵,发展为90年代的多点拥堵,然后是21世纪初的多线形成的大面积拥堵。管理者开始认识到交通管理是个宏观的问题。 2001年的小雪造成全城堵车,2004年7月大雨、2006年京广桥附近路面塌陷,都带来严重的堵车问题,我把它们称之为“蝴蝶效应”。这时候城市管理者意识到更宏观的问题了,修路或解决交叉路口的拥堵,只是相对单纯的技术问题。但是现在应该对北京的整个交通系统动大手术,所以提出来要制定一个交通发展战略。2003年首都交通委员会成立,确立了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的想法,大力提倡公交优先,搞好停车管理,实行地区差别政策,尽快实施交通管理智能化,完善道路网系统特别是加强环线间快速联络道的建设。这些措施将在北京交通发展史上起到标志性的作用。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