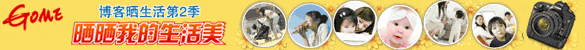四川什邡基层官员雷兴保:笑着撑起这一年

雷兴保 男,46岁,什邡市红白镇木瓜坪村人,红白镇人大副主席,地震中失去妻子。
失去亲人的基层官员,比常人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他们要用更多的坚强和微笑,包裹悲伤,撑起人生。
一面之缘
雷兴保的家在红白。红白是个好地方,紧邻矿山,物产丰富,豆干、茶叶川内闻名。他在这里生活了46年。
我和雷兴保能成为朋友,是因为去年的那场地震。红白当时是重灾区,我去采访遗体安置,一个工作人员把我领上山,在忙着挖坑掩埋遗体的人群中,我第一次见到了雷兴保。疲倦、苍老,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干涩的眼睛,他穿着一身沾满了泥巴的迷彩服,晃晃悠悠,朝我们走过来,我觉得他马上就要摔倒了。
他是红白镇的人大副主席,从地震起,就负责遗体掩埋。站在成片的墓群中,他双手叉着腰,靠在一棵树上,沙哑着嗓子,回答了我的一个个问题。后来,他低声和我说,那个坟,是他老婆的。说完,抬起头,望着远处。我看了一眼他手指的方向,坟前插着一块木板,写着“爱妻罗均献”。
有个摄影记者想让他在妻子的墓地旁拍张照片,两米远的距离,雷兴保却不肯再走近一步,我看见他抬手擦掉了眼泪。
后来,我没有问他和他老婆的故事,也没来得及再去看他,就离开了红白,离开了什邡。
一年后,再次来到红白,我拨通了那个一直存在手机里的电话号码,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你在红白啊,我在你们北京,要不可以请你吃饭”。
他还记得我,我没想到。“只是想来看看你。”我对他说,“等你回来。”
那双眼睛
再次见面,雷兴保开着一辆皮卡,到村口接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到墓地看过了吗?”
我点点头,见他前,我特意先到墓地坐了一会儿。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笑了,“怎么样?还成吗?”
雷兴保正在负责把地震时的临时墓地建成一个规范的墓园,已经初具模样,急着听到意见。
我说,不错。他说,真的吗?
我点点头,认真看了看他,瘦了,不过穿得很精神,浅色横条纹的T恤衫,深蓝色的裤子,白头发很多,不过修剪得很整齐。
到了办公室,他拿白开水招待我,我嘲笑他,一个人大副主席,连点茶叶都没有。他说:“我不喝茶。”
我问他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他说:“我?当然好得很。”
我说,家人还好吧。他说:“地震后,父亲查出了癌症,春节后,死掉了,我把他抬回了山上的老家。母亲四五年前就得了帕金森,还是老样子。两个女儿在读书。”
“我胖了吧?”他问,“伺候了父亲半年,他走了,我就解脱了,立刻开始长肉。”他以为自己讲了个笑话,看着我笑。我有点恍惚,无法把眼前的这个雷兴保和记忆对上号。
“老婆呢?”我试探着问。他停止了微笑,把头倚在墙上,望着天花板,似乎瞬间陷入了悲伤,“还不想想这个”。
屋子里一下变得安静,只听得见外面的雨声。白晃晃的光穿透窗户,打在雷兴保的脸上。我又看见了那双熟悉的眼睛,疲倦、忧郁、伤感。
明天会更好
在红白,雷兴保是个官——人大副主席,震后分管遇难学生安置和学校重建。
我们在办公室闲谈,有个妇女来敲门,进来没说两句话,就开始抹眼泪。她是来找雷兴保谈迁坟的事,墓地重新规划后,她孩子的坟要迁到山上,做母亲的不忍心,觉得惊扰了孩子刚刚安逸的生活。雷兴保得做通她的工作。
“大家都在上面,你不迁,孩子一个人也孤单啊,到了上面,和大家一起耍,多快活。”雷兴保说。
孩子的母亲又担心工人活儿干得粗糙。
“我老婆就在那里,你还信不过吗?放心,一定给他找个更好的地方。”他说。
孩子的母亲点点头,想想还是伤心,坐在办公室里,把孩子遇难的经过,又讲了一遍。
雷兴保不打断,听完,安慰她:“都过去了,娃娃不在了,你还得好好活下去……”
送走了访客,雷兴保坐回沙发,一只手托着额头,另一只手不停地转水杯。他好像很累,不再和我说话。或许,这一年,他已经倾听了太多的故事,每个都有相似的情节,反复勾画着他刻意隐藏的悲伤。
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沉默,雷兴保回过神,清了清嗓子,和电话那头商量工作。
挂了电话,他又恢复了活力。
“你信不信,地震第二天,我就不难受了。”
我不信。
“真的。”他说。然后到QQ空间里,翻出一张张照片给我看。我注意到,他QQ的签名,是明天会更好。
照片是去年在北京看奥运会时拍的,他挥舞着一面国旗,在硕大的鸟巢前,斯文地笑。
去年,因为在救灾中表现突出,雷兴保获得了很多荣誉,去了两次北京。
除了证明自己过得好,雷兴保没有任何倾诉的欲望。我总觉得,似乎有那么一扇门,竖在我们中间,我找不到那把钥匙。直到见了他的朋友——谢主任。
那些深埋的爱
谢主任和雷兴保是老相识,一起在镇政府干了20多年,我搭他的便车回什邡。路上,我说,雷兴保真乐观。
谢主任说:“见了你们,他当然得撑起来,平时,才不说话。”
我问谢主任,雷兴保为什么不喝茶。
“地震的时候,他正在路边喝茶,地震后,就再也不喝了。”谢主任说,“其实,他就是那么个人,不爱打麻将,不爱吃酒,不爱耍,只是一心忙着工作,顾家得很。”
“一年了,雷兴保怎么没再找个伴儿?”
“他还没想通吧,他和老婆,好得很。她老婆,多好,多支持他工作。我们都不敢和他说再婚的事,一说,他就急。”
这个活在雷兴保心里的女人,如今安眠在他自己负责的墓地里。她叫罗均献,我没机会认识她。在雷兴保的电脑桌面上,我看见了她的照片,白净、苗条,眼睛很大,看上去很温柔。这是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相册都埋了,雷兴保去挖,一本也没找到。
照片放在电脑桌面上,每天打开,他就能看见她。
关于爱人,雷兴保一字不提,只说:“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我们一起过了20多年。”
后来我才知道,雷兴保的沉默背后,藏着深深的愧疚。
谢主任说:“地震那天,罗均献被砸在了宿舍楼里,雷兴保经过,却没有去救,而是直奔了学校。好几个学生家长和我说,他们刚刚赶到学校,就看见雷兴保正在救人。”
3天后,当罗均献的遗体被救援的战士扒出来时,雷兴保还待在学校里,他一眼也没看,直接让战士帮着埋了。
“他是不敢看。”谢主任说。
怎么能难受
我一直试图理解他的选择。可是,雷兴保说,没有什么选择。
“是惯性,直接就往那跑了,是你,你也会这样,地震太强大了,由不得你逃避。”
后悔吗?我问。他用力想了很久,没有说话。
对于“官”的认识,雷兴保似乎也没那么清楚。他20岁开始在红白镇政府当临时工,用了26年的时间,干到现在的位置。其间当过会计、村支书、镇委副书记。
他最牛的一件事,是1995年,在木瓜坪当书记的时候,带头开发了欢乐谷。“这个项目,不夸张地说,带动了红白乃至什邡的旅游业。”说到这里,雷兴保面露少有的兴奋。
不过,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个很有事业心的人。
“本来想着,这届人大到期后,就换个轻松点的工作,45岁了,也不可能再升了。”
我问他年轻时是不是还有点理想?他说,没有啥想法,每走一步,都是顺其自然,干好工作,就完了。
或许,当官,对于雷兴保来说,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甚至都没有选择,只是路走到了那里。可是,地震让一切都不一样了。雷兴保体会到了一种不由自主的责任感。
因为这种突然爆发、无法解释的责任感,他甚至放弃了去救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妻子。同样,因为责任,这一年,他撑着自己。
“你一出去,就代表政府,谁有事,都要找你说,你怎么能难受。”雷兴保说。
反正我不会死
雷兴保不能难受,他只能忙。先是忙着处置遗体,然后忙着安置学生家长,接着又是残联的工作。父亲查出胃癌后,他还要每天往返什邡和红白,忙着照顾老人。
9月份以前,他几乎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难受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笑,笑着笑着,就笑到了现在。”雷兴保说。
我们去了正在施工的墓园,他指挥工人干活,对妻子的墓视而不见。
走到最高处,他回过身,望着下面成片的板房,长出了一口气。
那里是他生活了40多年的故乡,承载着他所有的回忆,他亲眼看着这里变为废墟,碾成尘埃。
“真想休个大假,再也不回来。”雷兴保说。
可是,手机马上又响了,他再一次打起了精神。我听出那彩铃是《我想有个家》。
我们聊起了他的两个女儿,雷兴保很愿意讲小女儿给妈妈的誓言。
“春节的时候,我们去上坟,女儿说,妈妈,你放心,我会把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烧给你。”
地震后,雷兴保把很多东西都看淡了,以前想着把女儿培养成才,现在只想把她培养成人,“今天过得快乐,比什么都重要,明天还不知道在哪里”。
说到这儿,他突然和我提起了北川,提起了刚刚自杀的冯翔。
五一假期,雷兴保独自一人去了趟北川,他只想看看让冯翔绝望和悲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理解他,为了工作,总要回老县城,一次次把伤疤揭开,能不难受吗?他的压力,我们每个重灾区的基层公务员,都有。”
我突然很担心雷兴保。他却又笑着安慰我:“你放心,反正我是不会死的,过去这一年,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还不是过来了,以后,只会更好过。”
本报记者 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