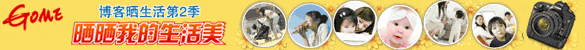成都档案局调研员姬勇:为凋亡的稚嫩生命存档

姬勇
男,52岁,成都市档案局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地震后,他和同事一起收集遇难学生遗物,在档案馆立档。
以“生命尊严”的名义,将那些在地震中匆匆凋亡的稚嫩生命的遗物保存下来,将他们的笑脸、他们的作业本、日记、球拍、视频,永久存身于档案馆。这是成都市档案馆调研员姬勇震后的选择和行动。
编号365
一排竖立的档案柜,循着锲入地面的轨道,被徐徐开启。
一本、两本、三本……每次一本,姬勇顺序抽出柜架上列放的簇新档案夹。他是成都市档案局调研员。
档案夹上,全宗编号均为:365。
365,只是一个没有特别寓意的序列号,它可以是一年中的天数,或者别的什么,但对于许多孩子而言,这个编号,是他们的一生——
一张如花儿般美丽绽放的笑脸、一帧定格于2008年5月12日前的日记、一篇充满童真想象的作文、一份地震前才批阅完的试卷、一个少女的共青团团员证、一摞奖状……
这些档案,它们的主人是地震中遇难的孩子——都江堰新建小学和聚源中学的学生。
来到档案馆之前,它们原本散落在震后的废墟里,散落在沾满泥淖的书包里,散落在爸爸妈妈一时哀伤无力的手心里,散落在香烛素纸的漫漫追思里……
姬勇小心翼翼地,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打开档案夹。
“没有汶川大地震,这些孩子们还会继续书写,继续画他们的画,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画家,会成为诗人,可是地震发生了,他们花一样的生命终结了,留给我们的,除了悲痛以外,我想,还应该包括这些孩子美好的一面,因为,他们曾经是那么鲜活地存在过。”
他们姓甚名谁
第一件被存放到档案馆的遗物,是一位记者上门交给姬勇的。那是一个叫杨萍的学生画的奥运福娃。
《成都晚报》记者傅艳震后采访时,杨萍父母带她看了女儿生前的房间。那是一个被绘画张贴得花花绿绿的小房间,画是杨萍画的,有反映环境保护的,有关于北京奥运的。
傅艳想保存一幅画。“她爸爸妈妈当时是很欣慰的一种表情,没有任何不舍,完全就是很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愿意留存他女儿的一幅画,立刻就说所有的画你选,都可以。”
傅艳突然被触动了。她后来在成都市档案馆对姬勇这样表述:“一百年乃至更久远的时间之后,如果后人查阅汶川大地震时,在档案馆里面发现了一幅小朋友的画,画的是福娃,你说,这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一刻,姬勇形容自己像是被一道光轰然击中。
“死了那么多人,他们是谁?姓甚名谁?他们曾有过怎样的年华?我们是国家的档案馆,为什么没想到主动收留这些死难孩子的遗物呢?”
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档案收集管理工作,姬勇打交道的对象,是党政机关的各类红头文件、各种官方资料。记录普通人的档案,几乎没有。档案,成了柜架里冰冷的数据。
可是,生命原本是那般鲜活啊。
姬勇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意识到,大灾当前,他们其实可以更加有所为,“不然,若干年之后,也许我们都不在了,后人会拷问,那场大地震中死难的人,他们是谁?你们为何不在档案中记录下他们?”
而实际上也是,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时,有关部门曾征集地震档案,但时过境迁,大多数与那场浩劫有关的记忆碎片早已零落,能征集来的,只剩了残缺的数字和寥寥的人名,失魂落魄,不知归路。
灾难记录
5月下旬开始,姬勇一行出现在聚源中学和都江堰新建小学。他们要为死难的学生,立档。
一座坍塌的三层教学楼废墟前,学生家长、救援人员,黑压压地站了两三千人,不断有学生家长撕心裂肺地哭喊,空气中弥漫着消毒药水的呛人味道。姬勇和同事们只能先和这些家长们耐心沟通,慢慢赢得他们的信任。
一位叫周乐康的家长,是一位农民,他的儿子周静波,一个有着绘画天赋的优秀特长生,倒在废墟下没能出来。得知姬勇的来意后,这位父亲仍十分不解地问:“我们是农民,国家的档案馆真要收这些东西呀?”
姬勇郑重相告:“你也知道,5月19日那天,全国人民都在为遇难的同胞默哀,国旗也为所有离去的生命降下了半旗,这是国家对所有遇难生命的尊重。我们来这里收集和地震有关的档案,就是要通过真实的实物,记录下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纪念包括你儿子在内的所有生命。”
一张没有填写完毕的奖状,是周静波留给父母唯一的遗物。周父把它交给了姬勇。
抹着泪的家长们闻讯渐渐聚拢而来。虽有不舍,许多人还是递上了孩子的遗物,“只要对记录历史有用,你们就拿去吧。”
姬勇为遗物登记造册。照片、绘画、作文、日记,每一件遗物的登记表,都对应着家长的详细信息,像是为迷途的孩子留了回家的路。
对死者的尊重
姬勇禁不住会痛惜,很多有意义的遗物,已经被家长们在祭奠时烧掉了,或者被其他收藏者捷足先登收走了。
在聚源中学,看到一家民间机构的人在废墟上翻翻捡捡,他就忍不住上前说上几句:“这不是捡垃圾,你们应该登记造册,让家长们知晓。这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许多时候,他都是眼里带泪,接收下一件件遗物。
遇难学生胡娟,她爸爸妈妈把她很多遗物都烧掉了,只留了两件:一件是她的共青团团证,另一件是她的一篇获优秀奖的作文,叫《父母的爱》。最开始,胡娟妈妈拒绝了姬勇的捐赠请求。
她说,孩子小,还没有身份证,“她到了那边世界后,别人不认识她,把这个团证和她的作文放到她的骨灰盒里边,别人就认识她了,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知道她是哪个学校的,也知道她是个乖孩子,爱爸爸妈妈的。”
姬勇愣了一会儿,他不忍心了,“如果换成我,没有人来找我,没有国家的档案馆来找我的话,我也会和你们一样,把孩子留下的东西好好地存放在骨灰盒里。”
这位母亲没有再说话,她翻看团证,一直看着孩子的照片,一直看。最后,把它合上,递给姬勇,“你们拿去保管吧。”
那一刻,姬勇说,他真的没敢单手去接,他觉得其中承载的,太重了。
办完造册手续后,胡娟妈妈突然说,能让我再看看吗?姬勇马上会意,“没问题,快,把盒子打开。”这位母亲再次翻开团证,用手摸着她女儿的照片,一遍遍摸……
当时在场的人,都哭了。姬勇说,以后,你随时都可以来档案馆,看你的女儿。
心理抚慰
档案馆与亲人留存逝者遗物,二者最大的不同,在姬勇看来,前者是国家行为,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生命表达尊重,对于逝者的亲人来说,这本身就会是一种心理抚慰。而且,存身档案馆,那些流落的情感记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记录历史,百年钩沉。
心理抚慰,姬勇和同事们在收存遗物时,也在刻意为之。他们会对家长们说:
“孩子不是在作文里说要做个坚强的人吗?那他也一定希望自己的妈妈是坚强的母亲。”
“好好地生活下去,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纪念。”
……
谢鑫婧,长得有些像《长江七号》中的小女主角,遇难时刚刚10岁。父亲谢家强是一个水电维修工,他接受不了女儿离去的事实。姬勇了解到,最开始的那段时间,谢家强晚上睡不着觉,经常悄悄地起来,去院子里偷偷地哭,吸烟,似乎还在写什么东西,写了揉掉,然后再写。
他写的,是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写给女儿。上面的字,密密麻麻。
姬勇见到他时,他两只手的手指皮开肉绽——震后,他疯狂地用手刨废墟,想把女儿救出来。姬勇搂了搂他的肩:“凭你这双手,你够格了,我也是父亲,但灾难这次实在太大了……”
这位父亲哇地一下哭了,他抱紧姬勇,一下一下地捶他后背。哭过了,他从床板下取出那封信,希望档案馆能收藏。
后来,这位父亲又把姬勇拉到旁边,和他说,“我不能再这样了,我得坚强起来,四川话讲雄起,我不能再让我爱人为我操心了。”
后来姬勇再见到夫妇俩时,他们说打算要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来档案馆看看,让他(她)知道,曾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姐姐。
花落知多少
目前为止,档案馆收集的遗物共有500多件。
相对于整个灾区几千名学生的死亡,这个数目太低了。这是姬勇最大的遗憾。“档案工作是属地管理,人力、财力,再加上一些你们不知道的因素,我们几个人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现在,如果家长送遗物过来,档案馆仍会收存,不会设置截止期限。“因为记忆没有期限。”姬勇说。
经此一遭,姬勇常常禁不住想,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我们的思维和观念,是否还能更开放一些,除了保管好各级党委政府的档案外,是否也能把地震的亲历者和遇难者,也系统地纳入视线?
姬勇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把这些档案搬出来,做防虫、防霉变处理。那些孩子们,像是又被集中管起来了。
在做日常维护时,姬勇也会翻开档案夹,再一个个看看孩子们——
曾雨朦的绘画日记,里面有花草、许多孩子,还有小动物、家。她说,“今天老师宣布了当班干部的名单,可是没有我的名字,我很难过。当时我想,如果没有我的名字,就是我字写得不好,爱说话,只要我改正就有希望。”
“今天老师说要开家长会,我一听心里很害怕,因为我怕老师说我上课不认真。”
刘星宇,喜欢古诗,喜欢绘画。档案里,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妈妈,节日快乐!”5月11日把贺卡放在书包里,当天他忘了给妈妈,地震后,妈妈才在孩子书包里看到。
张怡佳的练字本上,抄写着古诗。最后一篇,停留在了去年5月6日。那是一首《春眠》——“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花落知多少,姬勇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