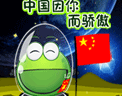巴金生命历程映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轨迹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00:00 华夏时报 | |
|
巴金101年的生命历程,映射了一个独特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他丰富而独特的人格,他的赤诚,他的忧郁,他的反思,无不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良知。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中国的良知,是世纪的良知。 这一家的罪恶我来救赎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性格的根柢。” “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101年前的11月25日,一个婴儿在成都一个大家庭中降生了……“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巴金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是从广元开始的。那是1909年,父亲李道河被任命为广元县知县。那时,巴金5岁,仁慈的母亲成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老师。三哥打了丫头,受到母亲的责备;父亲在审案时动用毒刑,经母亲劝说过后不再用刑……母亲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爱的种子。 因为要“爱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个告诉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轿夫老周,称做是除母亲之外的“第二位先生”。 “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巴金的心灵深处,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通过《灭亡》中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炮火中的“世俗”作家 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年至1949年初,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因此,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讨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牗《序跋集》牘影响他此时思想判断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牗《〈寒夜〉再版后记》牘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识分子反抗王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 1948年前后的上海,为读者摄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时的“身影”。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也是巴金所独有的、带有巴金式的姿态和气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牗要是长篇,赵家壁还肯接印牘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当年5月5日,致沙汀的书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 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 10月26日,又告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 12月21日,对来约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 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 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同时也非常真实的印象。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到处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然而,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 跟着别人高呼“打倒巴金”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 1957年6月,巴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历时半个多月。他一到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正好此时,《文汇报》记者向他约稿,他“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巴金躲过了一场劫难,他也“想多找机会表态”,因而写了一些文章。这时的巴金丧失了自己,丧失了他一向主张的“独立思考”和“讲真话”的勇气。 跟着别人说假话说得多了,巴金似乎渐渐不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了,他跟着别人高呼“打倒巴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死心塌地地做起“奴隶”来了。 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坚持真理、不软弱不说假话的中国人可能不多,但巴金老人并没有以此来原谅自己,他反省,他忏悔,他自我批判;为了几十年前对路翎的批判,上世纪80年代他郑重写出《向路翎同志道歉》一文。 巴金发现自己在那段日子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综合)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