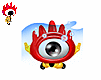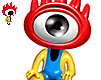| 异乡人迈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3日17:39 时代人物周报 | |||||||||
|
- 文 北岛 我刚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说:生命是坟墓上的舞蹈。让我们相见。你的美国叔叔迈克(Michael)。”明信片是张带有怀旧情调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着一朵野菊花。上面印着英文“地球书店兼咖啡馆”。典型的迈克风格。大概他此刻就坐在布拉格这家英文书店,呷着咖啡,在黑白的忧郁情调中等待他绚丽的情人。
我和迈克是1985年在荷兰鹿特丹诗歌节上认识的。 那是我头一回出国,语言和文化上的时差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但迈克忧郁的眼睛让我记住了他的话,他要请我第二年春天到伦敦朗诵。我果然如期来到伦敦,在市中心最热闹的考文特花园的一个小剧场朗诵。和我同台的是一位罗马尼亚的女诗人,可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她的政府不肯放行。迈克站在聚光灯下,挑选着词句,委婉地批评了齐奥塞斯库政府,他不想给这位女诗人带来麻烦。散会了,迈克把我带到酒吧,介绍给他的同行们。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凑够请我来的经费,他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去敲开一扇扇官僚机构的门。 迈克长我3岁。他70年代初从美国搬到伦敦,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染上了一口伦敦腔。为什么离开美国?他在一次访问中这样回答记者:为了寻找诗歌上的精神家园,像前辈诗人庞德、艾略特那样。可大英帝国并未向这位孤军奋战的美国骑士致敬。 他请我到他家做客。他们的生活,按英国人的标准算得十分清贫了,但仍保持着一种读书人的尊严:书在家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他在区图书馆有一份半日的差事,勉强养活四口之家。他的夫人汉娜是波兰人,精明能干。小儿子刚出生,大儿子嘎比四五岁,有着同龄的孩子没有的谨慎。我想这个小迈克多少反映了他父亲的窘迫:用刻板的小职员的生活来捍卫他的诗歌世界。谈起诗歌,他的眼睛湿润了,言辞也变得犀利起来,这无疑才是当年来伦敦闯天下的迈克。 与英国有缘,赞助这次活动的英中文化协会请我到杜伦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1987年春天,我和妻子带两岁的女儿来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幽静的大学城。这里低头看书,抬头看著名的大教堂。我有时去伦敦办事,顺便看看迈克。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也请迈克有空到杜伦来玩。没想到迈克竟全家出动,应声而至,让我们有点惊慌失措。我们比他们更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穷人间并不嫌弃,没床就打地铺。离开伦敦,离开那个临时图书管理员的位置,迈克变成一个可爱的梦想家,他有很多关于诗歌的计划,向我这个惟一的听众娓娓道来。在邵飞两次做饭的间歇,也被他拖进梦想的行列。他坚持要邵飞为他的第一本诗集配画,一家爱尔兰的出版社正在恭候巨著的诞生。那昏天黑地的诗歌的梦想穿插着孩子们的哭喊。第三天早上迈克一家走了,我连书也不看了,只看大教堂。 离开英国,我们又去了美国,回到中国,接着是多年的漂泊,我中断了和迈克联系。1990年春天我到英国朗诵,在伦敦试着给迈克打了个电话。迈克愣了一下,惊呼起来:“我的孩子,你在哪儿?我一直在找你!”对一个在街头电话亭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来说,这话的分量太重了,我不禁流了泪。我们约好在一家餐馆见面。迈克又是全家出动。坐下,他紧紧盯着我,眼镜后面聪明而忧郁的眼睛布满血丝。他明显发福了,看来年龄和家庭压力正在逼他就范。不,另一个迈克在说话。他愤世嫉俗,大骂英国诗歌界的堕落和势利,让我吃了一惊。 我问起邵飞为他配画的那本诗集,更让他生气:出版社毁约了。看来这个世界成心要毁掉一个诗人。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在倾泻了对世界的所有怨恨后,突然沉默了,喝着杯中的残酒。我看着他的儿子,提议去买两本书给他们作礼物。进了附近的一家书店,迈克的表情变得明朗起来,像被内心的灯照亮。他为他的两个儿子各挑了一本书,让我签名。他叮嘱嘎比要好好保存,仿佛这不是本书,而是他的精神遗嘱。嘎比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一别又是几年,我偶尔收到迈克的明信片,都是简短的,跳跃式的,像诗歌笔记。他的字迹小得几乎消失。我请他用打字机,他最后屈辱地接受了。他把愤怒和绝望诗意化——诗越写越好,每个词都获得了重量。 九三年我在荷兰,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兴奋地说,应该热爱生活。接着告诉我他不在图书馆里混了,而成了布拉格国际书展的主任,公司设在伦敦,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也就是说,他下海了。我真心为他高兴,这也许能让他在吞噬灵魂的官僚体制外透透气,至少他可以用“公家”电话跟我聊聊天。我搬到美国,早上总是被来自伦敦的免费电话吵醒。他的话题跳来跳去。除了诗歌,他开始抱怨工作,抱怨老板和同事,然后转而抱怨他的老婆。汉娜几乎成了魔鬼,要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写作。我闻出家变的味道。 九五年春天,迈克坚持要我参加他主办的布拉格国际作家节,但又无法负担路费。我有生头一次自费去朗诵。能看得出来,迈克真心地喜欢布拉格。几乎每天晚上他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但我嫌太吵。在心惊肉跳的节奏中,迈克告诉我,他在伦敦暗恋上一个捷克姑娘。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又告诉我,国际书展的主办权已被捷克人夺去,他们公司只好改行搞服装展览。我安慰他,至少他能整天和漂亮姑娘在一起。 同年夏天,我从巴黎坐火车通过海底隧道去伦敦,正赶上迈克的生日。他请我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我带着一条法国名牌领带和一瓶波尔多红酒,和住在伦敦的诗人胡冬一起赴宴。迈克已经和老婆分居,等着办离婚手续。他在伦敦北郊的富人区租了一个相当舒适的公寓,后窗临湖,晚霞铺在水面。家中并没有别的客人,孤独的迈克。我们打开一瓶红酒,为他的生日干杯。酒后他的话多起来,抱怨汉娜通过离婚抢走了嘎比,还要进一步敲诈他。在我们去饭馆前,他给嘎比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儿子,北岛在这儿。我又想起我这个精神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迈克失业了,他决定搬到布拉格去。这从美国出发的旅行,经过伦敦,最后终于抵达欧洲的中心,历时25年。他的旅行速度远远赶不上跨国资本对梦想的覆盖速度。布拉格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他又晚了一步。再说,嘎比怎么办? 前年年底,我和迈克在迈阿密海滨的遮阳伞下喝啤酒。这是我们头一次在美国见面。他的老父亲就住在附近。我突然问:“你不想搬回美国吗?”“不,这不再是我的家。我没有家,像你一样。”他笑了。 黄家驹:除了天才,还能说什么 - 文 刘卓辉 一转眼十三年了。应该是1991年的一个晚上,在我们一帮文艺青年经常聚集的咖啡厅,我最后一次碰见家驹。我们没有事先约定见面。那时,我们一帮人有空都会去那,遇到谁就跟谁坐到一块谈天说地。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先到,家驹一个人后到。他一坐下就说起Beyond乐队准备去非洲的事。 之后我们有两年没见面。我在北京做大地唱片,工作很忙。Beyond进军日本市场,家驹长期住在那里。在北京的时候,通过他们的经理人、我的好朋友陈健添,寄来家驹作曲的原始小样,只有他哼着的旋律和吉它伴奏。我写了跟他合作的最后几首歌《长城》、《农民》和《情人》。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两年后他出殡的那天。 我第一次知道Beyond是在1983年3月6日。那是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由《吉它杂志》(主编是黑鸟乐队的郭达年)主办的乐队比赛。这个日子我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我当晚看到一个美女观众,后来竟然在街上重逢而发展为一个暗恋故事,让我日后为张学友写了多首情歌去怀念她。那次比赛,Beyond以一首progressive rock(前卫摇滚)风格的作品《Brain Attack》(脑袋侵略)得了冠军。 1985年,我的朋友陈健添正在经营一家独立制作的唱片公司,当时租住在我家。有一天,我问他知不知道有个乐队叫Beyond的,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Beyond不错,过几天有演唱会(就是那个在坚道明爱举行的“Beyond再见理想”演唱会),可以去看看。我也在1986年参加了一个填词比赛得了冠军,就是1988年夏韶声演唱的《说不出的未来》(原曲是李寿全作曲/演唱、李大春作词的《未来的未来》)。就是这个缘故,陈健添找我帮Beyond的下一张专辑写了《现代舞台》(1986),开始了跟家驹的合作。而第二次合作的《大地》(1987),让大家初尝成功的果实。 1988年夏天,刚刚冒出头的Beyond到北京举行了两场演唱会。我因为到过两次北京,有幸作为导游被他们邀请同行。当年,一个唱粤语歌的乐队,能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开演唱会,从各方面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我的推荐下,家驹准备唱崔健的《一无所有》,我也临时写了《大地》、《旧日的足迹》的国语版。听家驹说,他们走台时,崔健去看了。不过以家驹当时的普通话水平,相信大家很难聊到一块。那趟旅程,我和家驹同住一室,让我发现男人原来也可以有很多美容用品的。 很多记者问我,怎么跟家驹合作的。其实在为他填词的六七年里,我从未直接和他联系过关于写歌的事,一般都是通过经纪人、唱片公司和制作人。我每次把歌词用传真机发出后,都不会收到任何人的回音。我常想,如果家驹不会写词,不是英年早逝,我们合作到现在,我应该可以赚很多很多版税。 那夜在咖啡厅,他说要去非洲。我问去非洲哪里,他说去非洲首都。我当时一笑。他为什么去了肯尼亚,回来就能写出《光辉岁月》、《Amani》?除了天才,还能说什么。 相关专题:新浪人物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浪人物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