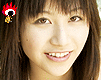经济观察报:漫长的告别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2日19:17 经济观察报 | ||||||||||||
|
花上12美元与30分钟时间,你就可以坐上奔驰出租车从耶路撒冷到达设在拉姆安拉的检查关卡。几位只露出面部的以色列士兵在巡逻与盘查,他们大多是20来岁、不无稚气的年轻人,笑容展开时,单纯灿烂。作为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拉姆安拉是巴方政府所控制的6020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繁华的地带,由于与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相接,巴勒斯坦人有机会在那里获得工作,还可以做一些最原始的小生意。
通过检查关卡那道转动的铁门,就来到了名义上的巴人控制区。你可以看到那座仍在不断延伸的隔离墙。“某种意义上,它就像你们的长城。”一位以色列学者解释说。这座8米高、由坚硬的岩石与水泥构成的墙壁减少了进入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者。当然,它不会知道巴勒斯坦人的感受。24岁的亚德·塔哈是拉姆安拉的Beir Zeit大学英语系的四年级学生,他有深陷的眼睛与卷曲的头发,穿牛仔裤与运动鞋,喜欢美国作家Pat Conroy的作品。每天清晨他从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家前往学校,需要穿越三个检查关卡。“他们(以色列士兵)让我觉得很屈辱。”塔哈说,“他们知道你身上什么也没有,还拼命地搜查。”至于隔离墙,塔哈觉得那是监狱的象征:“以色列想把巴勒斯坦人围起来。”自2000年以来,加沙与西岸地区就被完全隔开。“我从未去过加沙地带。”塔哈说他也没有去过杰宁等西岸地区,因为“那里很危险,有可能被枪打中”。 隔离墙的两端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耶路撒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它的商业与娱乐活动就像它的宗教精神一样浓厚。而在隔离墙的另一端,同样享受地中海沿岸充沛阳光与温暖气候的拉姆安拉,却衰败破旧,垃圾成堆。巴勒斯坦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而它的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只有18岁。在大部分时间里,店铺有气无力地开放着,这些店铺都拥有丑陋的、千篇一律的、锈迹斑斑的铁或铝合金门。 在阿拉法特正式宣布死亡的11月12日清晨,在通往拉姆安拉的克劳地亚检查关卡四周,拥挤了更多的人,尘土更加飞扬,以色列士兵更多,盘查也更为严格。大批被刷成黄色的出租车拉着一批又一批本地人与仍不断到来的记者前往市中心广场和阿拉法特昔日的官邸穆卡塔。 是的,你可以感受到,飘荡在空气中的情绪更为激动了,但不像新闻媒体期待的那样激动。自从阿拉法特在10月27日病情恶化并在28日前往巴黎治疗以来,关于他死亡的这一时刻就变成一场不断进行的演习。谣言与猜测充斥着每一个电视台与每一张报纸。他先是在吃饭时晕倒,然后发现饱经风霜的身体似乎每一处都有毛病。到达巴黎后他再次昏迷、深度昏迷、脑出血。最后,在现代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开始争论什么是死亡,因为不同的媒体至少两次宣布了他已经死亡。 他每一次咳嗽的加剧,都将一批新的记者带到了拉姆安拉,他们匆匆到来,雄心勃勃地试图比别人更早报道这一历史性时刻对中东和世界的影响。在那个地中海沿岸的狭窄的地区,有漫长的故事可以讲述。一些历史学家相信,那里隐藏着了解世界秘密的钥匙,蕴涵着世界上最难以梳理清楚的情感纠缠。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那里代表着似乎永远也不可能终结的混乱,没完没了的爆炸与冲突使那里成为苏联解体后世界第二大新闻产地。一些既清晰又模糊的图景主宰着人们的印象:抛石块的年轻人、自杀性爆炸与谁也不相信的和平会谈。 关于刚刚逝去的老人,他的印象同样既鲜明又模糊。他显然是我们时代所剩不多的几位具有符号意义的政治人物,他的花格头巾、永远不更换的军装与那张似乎定格的脸在过去的40年中有过不同的含义,从未从舞台中央消逝过。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他与同伴创建的法塔赫组织,他成为第三世界革命阵营中的新兴角色,与埃及的纳赛尔、古巴的卡斯特罗、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一样,是反殖民运动中的重要声音。 1965年,他与他的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对以色列的攻击。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惟一合法领导人得到了普遍性的承认。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难以相信没有了阿拉法特,巴以和谈该如何进行。他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外交部长佩雷斯分享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完成了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惊人的个人转变——由一名暴力信仰者变成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他说他至少逃脱了40次暗杀,他惊人地节俭,他用一种冲动却缺乏逻辑感的方式讲话。他终于成为一个由多种角色构成的混合体:一名永不停息的战士,一名受人尊敬的父亲,一位亲密的兄长……他几乎单枪匹马使巴勒斯坦问题赢得了全球性的关注,他几乎比任何同代政治领袖都更善于获得媒体的注意力。 “不,他们不了解阿拉法特,他有优点,也有缺点。”一位叫穆罕默德的本地人这样对我解释阿拉法特的批评者们对他的指责,“他像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他用爱而不是武力来领导这个国家,他有他自己的方式。” 在穆卡塔官邸四周,摄像机镜头充斥了每一个角落,寻找任何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人们抑郁的表情、高高举起的阿拉法特的照片、挥舞的巴勒斯坦国旗、游行……关于记者们都试图捕捉到的情感,亚德·塔哈的表达再准确不过了:“我的父亲年轻时,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我出生时,他也是领袖,他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失去他会意味着什么。” 他的死亡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吗?这个真空会导致内部冲突从而导致更大的混乱吗?当你置身在风暴中心时,你常常感受不到风暴的力量。生活仍在继续,11月4日夜晚,在一间拥挤的本地咖啡店里,巴勒斯坦人平静地吸着水烟,喝着姜汁味的本地咖啡。在墙壁的一角挂着一台电视,画面是半岛电视台对于阿拉法特身体状况的报道。那天晚上,拉姆安拉充斥着“阿拉法特已经死亡”的说法。“你知道,在过去10天里,我们听到了各种消息,我们不想再谈论,只想等待。”一位一脸平静、正在吸水烟的老年巴勒斯坦人说。经过过于漫长的等待与猜测,阿拉法特的死亡已被当地人所接受。在矗立着四座来自中国的石狮子的城市中心广场上,在过去的一周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挤满了人群与摄像机镜头。本地人对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他们随时等待着被访问,就像他们热爱与追随的领袖一样,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在摄影机前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要学会利用它。”我在广场上至少碰到了阿卜杜拉三次,他的眼睛很明亮,他用不流畅的英语解答我的疑问。他没有参加过游行和声嘶力竭的口号呼喊行动,但是他说:“他们的情感都是真实的,没人强迫他们到这里,他们都是自愿的。”像亚德·塔哈一样,他相信“没人能取代阿拉法特的位置”。但他也说不会有所谓的内部武力冲突出现,因为“人们需要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暴力”。塔哈甚至说,“比起独立,我们更倾向于更好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巴勒斯坦地区的500万人口拥有着令人沮丧的物质条件,而且看不到什么希望。在市中心广场周围是拉姆安拉的商业中心,也很可能是整个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最繁华的商业地带,那些来自中国沿海不知名工厂的服装与皮包,充斥在每一个摊位上。按照现代国家种种标准衡量,巴勒斯坦都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准,尽管它同样拥有税收、警察、商业、教育体制,却几乎都难以运转。 “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却可以改变未来。”在接受BBC采访时,以色列工党领袖、阿拉法特多年的谈判对手西蒙·佩雷斯在他的老对手死后这样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与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一样,期待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重新开启与以色列的和谈。美军在伊拉克费卢杰的战斗仍在继续,再次当选的乔治·W·布什将继续他的革命性外交政策,中东的确处于另一个转折时刻。阿拉法特的离去,是否真的说明那个旧秩序已经结束?巴以冲突正是中东棋局上的那个死结。 一条钢筋水泥围墙,将方圆不超过1平方公里的阿拉法特的官邸包围起来。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建筑物与围墙四周的房顶上,各家电视台付出12000美元获得一个可以拍摄到院内景象的地点。自从1994年起,阿拉法特就工作与生活在这里,2001年,他迎来了一生最屈辱的时刻之一。这一年12月3日,以色列军队的坦克开到了他的住宅前,将阿拉法特“围困”在官邸中,22日,以色列内阁决定,禁止阿拉法特离开拉姆安拉前往伯利恒参加圣诞节庆祝活动。阿拉法特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 那也是阿拉法特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一直到2000年前,他似乎仍因作为奥斯路协议的缔造者之一而受到尊敬。但之后的因地发打运动再次将巴以关系推入僵局。不管是新上任的以色列总理沙龙还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布什,都相信阿拉法特是一个足以被抛弃进历史垃圾桶的人物,他个人的存在阻碍了和平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阿拉法特仍展现出他无法被忽略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没有他,不管是库赖还是阿巴斯,似乎都难以拥有足够的能力与政治资本来达成和平协议。 “即使猴子穿上西装、打上领结,它也仍是猴子。”一位极端的犹太教徒这样评论人们对于阿拉法特死后可能开始的巴勒斯坦选举——人们期待选举可能造就一个值得信赖的机构,并展开新的谈判。“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取得这方面的成功,没有一个。”自由选举真的能将巴勒斯坦带上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吗?亚德·塔哈则干脆说,他觉得所有竞选人实质上都差不多,在表面的差异下,他们的观点其实都是一致的。 几个月后,塔哈会从大学毕业,他期待能去英国读书,他认为那里比美国好,因为英国人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更为宽容,而在美国,“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政府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恐怖分子。”但在毕业前,他每天还得必须穿过那些令人感到羞辱的检查关卡。“在有些时候,我的确也想攻击他们。”曾经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都短暂工作过的塔哈说。如果那些自杀性爆炸者不去攻击咖啡店、医院与超级市场,而是针对士兵,他是完全支持的。“他们的士兵也杀害过我们的孩子。”而一位叫德维亚的26岁的以色列年轻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在他的国家,每个男孩子都要服三年兵役,女孩子是两年。在那三年中,德维亚经常在加沙地带巡逻,并根据情报突然闯入被确认是恐怖分子的家中,将其擒获或射杀。“听着,我不喜欢杀人,那些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心灵。”在退伍后,德维亚甚至不愿再谈论那段经历。24岁的塔地阿亚是耶路撒冷的一名警察,在2003年一起著名的自杀性爆炸发生时,他看到一条胳膊从眼前飞过,汽车上满是尸体的碎片。 令人难以忘记的历史与仍在不断进行的新的冲突,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复杂得难以梳理,而且理智的作用往往有限。阿拉法特的个人悲剧,既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悲剧,也是整个中东悲剧的某种缩影。他的离去的确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感空白,但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淹没在阿拉法特个人魅力之下的那个民族的真实情感与渴望,这种渴望与需求将在未来不断被表达与释放出来。伟大人物的作用总是两面性的,他既唤醒了你沉睡的情感,又抑制了你的真实感受。终其一生,阿拉法特都未能放弃他年轻时就塑造出的自我模式——一个不断革命的人。-本报主笔 许知远 巴勒斯坦拉姆安拉报道 特约稿件,如需转载请获特别授权 相关专题:阿拉法特逝世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阿拉法特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