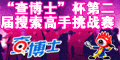撰稿/王怡
最近南方某省冬季征兵工作,冒出一个不太和谐的报道,即要求曾经是SARS患者的治愈者,不要参加征兵报名。理由是谁知道有没有治愈,有没有潜伏的后遗症呢?并且还拿军队高密度的集体生活来强调万一的危险性。
谁啊,谁知道呢。这句话的背后潜藏着我们内心对一切不可知事物的不安全感。前不久一位朋友曾问我敢不敢和艾滋病人握手,我说当然可以,艾滋病是绝不会通过握手传播的。但他说,这是尚未攻克的绝症,科学日新月异,万一哪天发现握手也有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呢?我记得在当年为艾滋病人遭受的歧视而抗争的美国电影《费城故事》里,扮演律师的丹素·华盛顿也曾这么问他的医生。我是这样回答的,假设有万分之一的几率,第一,不是和我们上街被车撞死的危险差不多吗?第二,和你握手的人也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所以你的问题不是“敢不敢和艾滋病人握手”,而是“敢不敢和人握手”。
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经注意到,当我们谈论正义时,自由和平等总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但群体的安全在内部的法律秩序中,总是被置于较次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安全感是和信息有关的,有关部门之所以觉得有SARS病史的人是不安全的,正是出于我们的无知,我们在信息上的不对称。而这种信息不对称是人类的一种命运,用哈耶克的观点说,我们的知识是高度分散的,不可能有一个中心掌握全部的知识。因此也就不可能会有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拥有绝对的安全。只有上帝是安全的,因为只有它才知晓一切。
如果把增强人群的各种安全放到过分重要的地位,就将必然直接伤害某些人的平等和自由。因为当危险尚未发生时,安全仅仅和某种概率有关。刑事法学史上曾有一种理论,根据某些生理指标把一些人视为“虞犯”,也就是有可能犯罪的人。这个虞犯人群的犯罪率在统计上的确比一般人群高。就像把有SARS病史的人排除在征兵之外,甚至排除在更广泛的就业和生活之外,那么从概率上也的确可以增加剩余人群的安全感。但概率是这样一个冷漠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每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价值被数学化了,被小数点化了,换言之在这样的社会政策中,有SARS病史的人根本就不再是“人”,至少不再被视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毫无道理地把我们自己的安全凌驾在这个少数人群之上,暗含的意思就是我们比他们更重要。这是一种无耻的暗示,它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它是怯懦的,以至于仅仅倚仗人数上的优势去支持这种暗示。
同时,概率也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概念。但每个人生而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条)的意思,就是我无须为别人的行为负责。如果我是一个有SARS病史的人,社会无权要求我为其他有SARS病史的人负担一种连带责任。如果我是一个黑人,社会也无权根据黑人的犯罪率在统计上比白人高,而要求我为黑人这个群体的犯罪率买单。我首先是我自己,我是王怡,而不是一个黑人,一个“乡下人”,一个有SARS病史的人,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甚至一个男人(比如“男人都是坏人”这句话就是对我的严重歧视)。社会怎么对待我只能取决于我做了什么,而不能取决于和我类似的那些人做了什么,或有可能做什么。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存的。这句话不仅意味着每个人都在分享他人的劳动,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分担来自他人的风险。我们不仅因为对劳动的分享、同时也因为对风险的分担才变得亲密。只要社会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某一人群具有一种现实的、高于一般的风险,社会就绝没有权力在任何方面歧视他们,要求他们作出牺牲。-
相关专题:新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