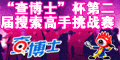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商务周刊》社论:刘涌死了,法治不能死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25日18:17 商务周刊 | |
|
作者:高昱 刘涌死了。看到最高院近2万字的判决书,尤其是看到新浪网上数万条评论中铺天盖地的欢呼、对十多位为刘涌和二审判决进行辩护的律师和法学家的唾骂,我感到异常失落。说句自嘲的话,像丧家之犬一样失落。 一个坏人该不该杀,这大部分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坏人能不能杀,在一个法治社会,则是不折不扣的法律问题。然而,在刘涌通往死亡的道路上,我们却没有看到法律本身权威的力量。尤其在2003年8月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后,一些最早在中国实践和传播法治精神的律师、学者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法治这个曾被毫无保留寄以期望的法宝,在它还没有开始参与到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全面改造的时候,就成了不辩好坏、为虎作伥的帮凶,它的精神遭到痛快淋漓的嘲笑,它的条文被用做可以量体裁衣的工具。 新浪网站调查80%的认可度说明,这一复审结果是符合民意的多赢胜利。但胜利者中果真包括法律这个主角本身吗? 细查最高院的复审判决书,我不得不对这一点再次提出质疑。尤其是是否对刘涌及其同案被告动用刑讯逼供这一关键环节,一些法律人士也认为,疑问依旧无法获得解答。 在逐条细致列举了刘涌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之后,判决书用十分简单的理由认定刘涌及其同案被告人并未受到刑讯逼供:“刘涌的辩护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明公安人员存在刑讯逼供的证人证言,取证形式不符合有关法规,且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同一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 然而,判决书并未说明,来自6位武警证明“存在刑讯逼供”的证人证言,在取证形式上哪一点不符合有关法规,不符合什么法规,是不能够明示,是证人没签名盖手印,是笔录有涂改,还是取证人主体有问题,抑或是证人主体有问题? “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同一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这一句同样含混,不同证人对同一事实的描述、同一证人前后的描述不可能完全一致是符合生活常识的,那么究竟是细节性的、非本质的差别,还是本质性的差别?如果说是本质性的差别,既然前一句只是说“取证形式不符合有关法规”,没有说6位武警做了伪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记忆差别?是他们6个人都出现幻觉了吗? 对刑讯逼供的认定理由仍有漏洞,因此,如果完全依照最高院公开的判决书分析,对刘涌指使他人故意伤害致死的指控就依然证据不足。该判决书对“指使”二字所认定的证据都是同案被告人供述,并没有物证,且6名提取口供的同案被告有5人翻供。由于有利害关系,对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映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锁链的情况下,法庭不应轻率采信,对一个只有1人口供孤证的关键指控,辽宁省高院本着“疑罪从无”的法定原则不予认定,我以为,仍比最高院的再审定罪更经得起考验。 对于刑讯逼供的问题,正如4个多月前我在《商务周刊》发表的《刑讯逼供救了刘涌?》一文中所阐述的,其实二审法院的逻辑很清楚:由于在刘涌有没有指使手下进行伤害致死这一个关键问题上各被告翻供,法庭“经复核后认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刑讯逼供的行为”,所以依法不予采纳相关口供证据——由于合法证据不能支持对刘涌指使故意伤害致死的指控,虽然其他证据能证明刘涌其他罪名成立,但那些罪名只能判死缓,不够判死刑。然而,很多人却在愤怒的情绪下,简单地理解为“因为有刑讯逼供,所以减刑”,甚至一些法学家和媒体也有在意无意这样误导公众。 作为采访过多起大案、冤案的记者,我深知刑讯逼供之普遍和丑恶。我更深知,同样被诸多民众所唾骂的“专家论证会”,在当前中国社会维护公平、法律救助和信息公开等方面,恰恰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当多遭到枉法对待的公民,在四处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只能和他们的律师一起,求助刑法和刑诉法专家,冀望于法律这条最后的救济之路,冀望专家们的意见能够在面对权势和国家强力机关时本就不公平的天平上投上一块砝码,虽然他们仍然常常无法改变不公的命运;而记者在持正报道中,同样需要从律师和专家意见书那里听到不同的声音,哪怕它是如此微小,却可以向公众告知事实的另一面,甚至更多被掩盖的信息。尽管不可否认这里面可能会有各种弊端,但专家论证会和专家意见书,确实是目前对抗行政干预司法、并让公众获得更多知情权的很好的武器。而事实上,各级公检法机构也常常就某起案件邀请法学家座谈咨询。在中国司法人员的职业素质还没有超过法学家之前,专家论证会仍然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良性力量。然而,这一切都在公众对刘涌的仇视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长篇判决书前动摇起来。黑社会可以不把人命当回事,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信仰法治,只有法律才能如此剥夺一个人的性命。刘涌很可能死得并不冤枉,但他的死亡之路上却搀杂了太多了法律之外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次的“负负得正”,但每个“负号”,都意味着法治遭到了漠视,难道我们就该为这个最后的“正号”欢呼吗? 如果我们信仰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和它站在一起。在我们这个人治还常常大于法治的前法治社会,法律常常令人失望,但那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另一种规则的罪过,我们不能因此而像30多年前砸烂公检法一样,把不作为的罪责归咎于法治的身上;在一些法治已经成熟到遭到滥用的后法治国家,法律也常常令人失望,但我们不能因此像50年前想当然认为可以跨越市场经济,直接用集中计划安排社会生活那样,因为某些权势者钻法律空子开脱罪责而质疑法治的功用。 如果不依靠法治这个制度权威,我们依靠什么?中国从不缺乏明主清官,更不缺乏响彻云霄的崇高口号和广场上手臂的森林,但太多的教训让我们终于认识到,人治会比法治让我们牺牲更多宝贵的自由、权利、幸福和尊严。 法律并非万能,它并不能负担维护社会正义这个责任,它最多只能维护公正,正如哈耶克的名言:“只有程序正义是可能的。”它最大的作用不是惩罚犯罪,而是维护权利,是保障每个人依照制度受到公正的保护。所以才有“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刑诉原则,才有庭审制度的改革和对程序公正的追求,也才有“无罪推定”和“坦白从宽是诱供、抗拒从严是逼供”的保护沉默权的呼吁。换言之,法治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机器和强势者行使约束力——它们太强大了,在披露孙志刚被毒打致死的报道中,《南方都市报》写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谁不是小人物?谁不是普通公民?”同样的法治精神,我们不能因为它没有发生在孙志刚身上而呼唤它,却因为它发生在了刘涌的身上而质疑它。 1999年,研究法与“本土资源”问题的法学家朱苏力在一篇文章中警告说:“法治这个舶来品在中国一个无法规避的代价是,在一个发生着迅速变革的社会中,即使是长远看来可能是有生命力的秩序、规则和制度,也仍然可能因为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验证它的生命力——甚至有可能夭亡。”面对无处不在的犯罪,对重典和严刑的呼吁是人们自然的反应。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社会治安是现实而具体的,在司法面前的个人权利反倒成了抽象的概念。要现实的安全和惩治坏人,还是要似乎还很遥远的司法人权,人们给出的答案几乎是可想而知——这个抉择与法学家们的声音该是多么的不同。从传统的人治到现代的法治,不仅仅是一个法治是否权威的问题,更多的是对法律功用的认识,对以夜不闭户为最高社会理想的中国人来说,如同“刘涌不死,则法律必亡”的口号一样,法律对少数罪犯和嫌疑人的保护,被视为对大多数人奢侈的犯罪。 中国法治的每一个进步,都必须与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公众心理进行艰难的博弈。诚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所说,制度是一种内在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东西。法律不是一个产品,法治也不是某种可以“建设”的项目,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它只能将社会中已经形成的秩序制度化,因此,法治依赖每个人对它的规则和权威性的认同。 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利用每个机会,弥补法治这个目前很多时候还只停留在口头上和学术精英的观念中的权威,与行政系统工具主义思维和公众因果报应意识之间的巨大鸿沟,并为它的每一次荣辱而发出声音,让法治精神为公众所接受,让法治的规则为权力机构所遵循。 它意味着,如果我们信仰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坚持地和它站在一起。哪怕现在它看起来还如此天真,甚至无能。 相关专题:新浪评论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浪评论专题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