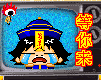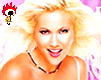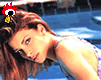| 新民周刊:收藏是一份缘(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24日10:38 新民周刊 | |||||||||
 古典家具展现场  某酒家的山西老家具营造出一个文化氛围浓郁 的时尚空间  随着古典家具收藏热的升温,大量仿制品也出现在 市场 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著名收藏家马未都专访 撰稿/沈嘉禄(记者) 5月中旬,2004中国国际出口古典家具展览会暨中国国际古典家饰及艺术品展览会在虹桥地区的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它是商业的,更是文化的。正如主办方瑞欧展览服务有限公
再说,主办方为观众请来了古典家具收藏家马未都,这是个在收藏界响当当的名字。这三个字往往意味着机遇、胆识和财富,足以构成一部现代传奇。在一场题为“中国古代家具与起居”的学术讲座之后,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第一件收藏品差点被小偷扛走 记者:面对收藏家,一般人总想知道他从多少资金起步,而现在已经拥有多少财富。那么您能否先告诉我,按中国富豪榜设计者胡润及中国坊间的评判标尺,您的身价有几位数呢? 马未都:不提钱,一提钱就俗了。咱们就谈收藏。 记者:那就请您谈谈当初是怎么想到搞收藏的? 马未都: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一份青年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里当编辑,自己也写过小说、报告文学。在这之前,我是一名工人,文化程度不高,我在杂志社填个人简历时,文化程度这一栏里就填“文盲”两字。为什么呢,我中学没毕业就随父母去了干校,后来又插队,然后就当工人,那不就等于是文盲吗?后来我是写了小说,比如《今夜月儿圆》被《中国青年报》整版刊登,小小地震动了一下文坛,才被杂志社发现,嗬,也算一个人才吧?就这样调进杂志社,摇身一变成了文化人。 我从小爱看书,特别是历史书。懂了历史后,顺便对记录历史的器物也产生了兴趣。我开始收藏的时候正是中国艺术最不值钱的“文革”时期,那时候天津的文物市场形成较早,我在北京厂里上班,一有空就往那里跑。那时我收入不高,每月才40多元。不过当时东西也便宜,我把抽烟的钱省下来就可以买东西了。 70年代末,大概是出于发展外贸的考虑,国家恢复向民间收购古玩旧货了,在北京国营文物商店收购点,每天早晨没开门,外地农民已经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老瓷器在那里等着,排的队伍足足有一里路长。价格啊?当时一个清初的青花大瓶,收购价才10块钱。 记者:您收藏的第一件东西是什么? 马未都:第一件藏品是1982年花1600元买的四扇屏,也称钧瓷挂屏。当时我是用家里买彩电的钱买的。那东西原来也不是卖给我的,已经卖了外国人,标价是2000元外汇券。那家店就在王府井一带。后来那东西不让出境,外国人买了也没用。我赶紧要下了打了八折,1600元。这件东西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它既是瓷器,又是家具。 后来我家里被小偷光顾了一回,我跑回家一看,四挂屏还在,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它就摆在电视机边上,小偷把它挪到一边,偷走了电视机和音响。 记者: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而您这是四扇屏,每片至少镶嵌五片钧瓷,放现在少说也要十多万吧。您这一说往后得注点意,日后有小偷跑您家,可能抱了挂屏就走。再问您,刚涉足收藏,您有没有打算日后办一个私人博物馆? 马未都:没有,绝对没有。我完全是凭兴趣收藏的。钱也不多,不可能有计划地收藏。看中了买一件,纯粹玩玩。据我所知,从事收藏时间比较长、藏品品质比较高的人,基本上是出于自身爱好,很少考虑藏品的经济价值,也不受市场起伏的影响。主要是感情起主导作用,并不指望它天天升值。我就是这样入道的。 收藏界没有圣人,吃药总是难免的 记者:收藏界有一句话:吃药总是难免的。你一开始收藏,有没有吃过药? 马未都:这是谁也免不了的,搞收藏总要付学费。比如收进了一对鸡腿瓶,对方说是明代的,因为当时交易环境光线暗,没能看仔细。抱回家一看,是老冲头,也就是晚清仿明的。但这样的东西还是有价值的,放在今天,这种清仿明的老瓷器怎么也要好几千吧,当时我拿下来也不过90元。再比如买老家具,一批几十件,不可能件件看仔细,整个拿下来,后来发现其中几件是修过的,有几根档子是后来换上去的,不是原先的材质,那样的事就多了。但也不能说吃大亏。 还有一次,我买下一个农民的瓷器后,见他的形象跟一难民似的,就把他请回家,让太太做饭招待他。那人吃饱后说:“这是我一个月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您对我太好了,我实在不好意思骗您,刚才卖给您的瓷器都是假的。”说完撒腿就跑了。后来我把这件东西拿到琉璃厂给专家看,谁都看不准。现在仿古的水平很高,即使是博物馆专家,不经常到市场转悠就可能打眼。 辛苦,并快活着 记者:我不是要替读者问您一声,比如说,当初以较低价格买来的东西,放在今天已经升到多少价位了? 马未都:我告诉您啊,当时我在国营文物商店内销部买老瓷器,清代的碗,非常精美,一摞摞地搁地上,任我挑,10元钱一个。现在这样的碗在拍卖会怎么也要三五万吧。再跟您说,北京南郊有个姓张的老头,专门收农民从乡下背来的各种瓷器,块儿八毛地卖给他,他再加点钱出手,慢慢地成了北京一个老瓷器集散点,他就成了倒爷。收藏爱好者都奔那里去觅宝。他嫌人多了,就订了规矩,上午收进,下午卖出。他还在屋里贴了一张纸条:“现在流行肝炎,请大家不要久留。”我在他那里买了不少东西。一个雍正的民窑盘子,一尺直径,才几十元。一把唐代的越窑执壶,100元。现在唐越窑执壶没1万元根本别谈。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张黄花梨桌子才几十元,他是没钱才买旧货的,现在这样的桌子少说也得几十万吧。 到了1988年,我已经初具规模了。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瓷器收藏转向古典家具收藏的? 马未都:没严格界限,好像是一开始就并行的。当然,收藏古典家具有一个麻烦,特费地,需要场地搁它。那时候大家都住得不宽畅,家具抱回来得有地方供它。我也没想到租个仓库存着,当时没那个概念,更没想到日后要建个博物馆。所以一开始收家具不很多。纯粹是为了实用,我结婚那时家里全是老家具。既可用,又可欣赏。这是收藏家具的好处。 记者:买老瓷器您可以到文物商店,那么您到哪里去买老家具呢? 马未都:农村啊。休息天,跟几个同好坐车到乡下去转悠。带着图书资料什么的,一进村就找村长。家具有个特点,它不像瓷器,藏起来比较容易,家具是明摆着用的,谁家家里有,别人都看见,而中国农村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串门。我们把照片给村长看,村长马上就说,这个谁谁家里有,我带你们去。一进门,果然摆在屋里。谈价钱,成交,这比较容易。当时破家具不值几个钱。但是,奇怪的是,人对家具是有感情的,老家具记载着生活的印记,日子长了就跟家里的成员一样,舍不得离开它。比如说吧,我们在一家农民家里看到一对柜子,明代的,式样很古朴,但家里的家长,是位老大爷,他不肯卖掉。老人脾气倔,说不通。跟我一起去的朋友是个古典家具商人,他真有心眼,记下地址:某某县某某村,村口大树下某某家,回北京后写信给他的邻居,里面再夹了一封写着自己家里地址的信,说一旦那老头死了,就把那封信寄出,到时候我再来,给您100元钱。后来他真收到信了,老人死了,他立马赶到乡下,从老人后代手里把那对柜子买回来了。当时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通讯远不如现在快捷。通讯方便后,好东西也难找了,谁都像侦探那样四处打听,一有货,立马开车去了。 当时我们跑农村确实很辛苦。有一回,朋友说某地有一件老家具,一起去看看。当时还没有轿车,坐吉普,路也不好,一路颠簸,开出去一小时,我问在什么地方?朋友说就在不远。三小时了,我问到了没有?朋友说,已经剩下一半路了。这时您再想回去,也得三小时,得,继续赶路吧。又过了三小时,朋友这才说实话,这下真的只剩一半路了。十几小时路程,颠得我骨头都散架了,到那里一看,什么都不是,原道返回。这样的事多了,搞收藏就要吃得起苦,餐风宿露,节衣缩食。一开始别指望人家扛着好东西上门来找您,您得自己找。 传奇故事,多半来自缘分 记者: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除了眼力,还有机遇也是很重要的。所谓的缘,大概就是指这个。 马未都:对了,我的收藏生涯中故事很多,最有感触的一件是1998年的一天,李翰祥导演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很想见我:“我找您好长时间了,我的那些老家具想不要了。您帮我处理了吧。”那天我下午有事,我说我要出去,要么您早点来,要么下午4点以后。他说那我4点以后来吧。结果中午我吃饭的时候他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在路上了,要我等一下。他到了的时候是12点多了,他给了我一个清单,十几件有年份的硬木家具,列了价钱。我说行,那咱们谈谈价钱吧。但他很快就走了。我想反正接下来有时间谈,我要还掉一点,这是规矩。谁知,第二天晚报就登出来说“李翰祥猝死”,当时我就奇怪:哪个李翰祥?是不是还有一个李翰祥?我昨天还看到他了,其实他从我这里出去后就直奔拍摄场地了,到那儿拍了一个镜头就死了。他好像是有预感的,把十几件家具交给我了。死后他儿子找我,说既然李先生生前把这些东西都托付给您了,就是这些东西跟您有缘了。我想这就是缘分吧。后来我没法还价了,就照单全收了,几十万美元,是分几次付清的。 记者:我见过李导留下的一张清康熙紫檀螭龙三弯腿大画桌,是照片。据我估计,就这一件现在也值几十万了。当然您不会太在意这批家具的经济价值,您现在对这些家具挺有感情的是不是? 马未都:是的,不仅因为是李翰祥留下的,更因为它见证了一段人生经历,太离奇了,也太有启示性了。 老家具是能够承载一种感情的 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书画、陶瓷、玉器收藏几乎已经到了全民动员的地步,而古典家具收藏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您认为呢? 马未都:是的,这是因为长期来我们一直认为家具不过是生活用品,家家户户都有,不稀奇。再说过去家具收藏,主要盯住硬木家具,而这类家具存世量很少,一般人不易接触。现在白木家具进入收藏家的视野,它的价值正在被发现。其实从收藏的意义上说,家具收藏在国外已有70多年了,在中国只是近20年的事。但中国古典家具的价值在国际上是被认可的。中国古代工艺品创下世界拍卖纪录的都是古典家具,比如去年香港索富比拍卖行拍的一件清紫檀十二扇屏风,以2300万港币成交,创下了中国古典家具的成交纪录。但英国、法国、美国的古典家具,动不动就超过一个亿。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还是很大的。 但在中国城市普遍的怀旧情绪中,家具担当了承载感情的主要角色。这是人们看好它的理由。还有一种因素是不少古典家具的设计是文化人完成的,他们在家具中渗透了中国人的审美精神,这种精神历经沧桑,至今还能打动我们。中国人过去置一套红木家具,就想着要传代,现在家具是工厂化生产的,人文精神几乎失落殆尽,加之材料不行,不值得传下去,用几年,过时了就一扔。 有一回,一个大学教授要将他家里29件老家具转让给我,还有一袭式样很怪的灰鼠皮大衣,价钱谈妥了。他那在国外的女儿就打电话来说,小时候离家很早,家里的印象都淡漠了,只有一件柜子上的花纹还记得清清楚楚,希望将这件家具留下做个纪念。您看,一件家具给人的印象会很深,它记录了一个人的成长和感情。后来我就留下这件家具,谈妥的价钱不变。 没有文化人, 收藏不可能玩得那么转 记者: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一般有两个支流:宫廷、文人一路,另一路是民间。但民间艺术更为活泼,更有生气,它是文化人的灵感源泉。不过文人的参与,对提升中国传统艺术是起到了引导作用的。 马未都:是的,在古典家具收藏热的兴起中,文化人也起到了引导作用。首先重新发现了古典家具的艺术价值。这个文化人包括外国人。我要说有三本书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本是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写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将中国古典家具介绍给世界,引起轰动,不少外国人就是在这本书的引导下来中国寻找古典家具的。它带动了全球性的中国古典家具研究热。第二本书就是安思远先生在1971年写的《中国古典家具》。安是美国人,被西方世界称为“中国古董教父”,就是把《淳化阁帖》卖给上博的那位。但这本书没译成中文。另一本是中国人写的,王世襄写的《明式家具珍赏》,应该是第三个里程碑,它的价值现在还在被不断证明。当时是80年代,有一次我跟王世襄先生到农村寻找家具,看到一个山西的农民,在炕上放着这本书,看样子已经攻读了很长时间。当时这本书初版要100多元,我想也是整个村里最贵的一本书吧。一个农民他肯花这笔钱买这本书,就是为了了解家具的文化、经济价值和它的投资空间,他准备出手了。 现在,中国人自己收藏古典家具的压力来自国外。国外人跟您争好东西啊,您的经济实力不如人家,好东西就流到国外去了。国际拍卖市场的精品要拍下来也不容易。 记者:去年王世襄的俪松居长物拍卖专场您去了没有? 马未都:那几天我正好闪了腰,但通过电话委托拍了几件。 记者:那次拍卖的成交价普遍比平时的市场价高好几倍,您是否想通过此举对老前辈表示敬意? 马未都:整个收藏界都在表示敬意。 收藏再丰也不过是过眼烟云 记者:您在创建中国第一个私人家具博物馆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马未都:我从90年代初开始想做一家私人博物馆,当时借人家的场地办过几次家具展,参观的人挺多,感觉不错。那时候生活开始得到改观了,就想国家没有私立博物馆,我何不办个私立博物馆呢。可1992年打的报告被枪毙了,到了1996年才算批下来,名字叫“观复”。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原先坐落在琉璃厂西街53号,这座房子是建于民国初年的老字号,我接手后恢复了老古玩店的古旧风貌。面积并不大,但我设了一个茶室,朋友来了,可以聊天。后来觉得地方不够了,2000年就搬到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馆的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对称蝶状布局,展线清晰明了。内部的装修使用了不少中国传统工艺,如手工雕刻、大漆髹饰等。现在还准备搬,到机场路那边去。茶室肯定保留,我要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学术探讨、朋友交流和休息的场所。 记者:这不远离市中心了?会对参观者带来不便吧。 马未都:真正的爱好者是不会觉得远的。我要纠正一个错误:参观的人多了,展览未必成功。国宝展的人多吗?几十万,要排好几小时的队才能看一眼《清明上河图》,国内的专家来了,日本人坐了飞机来看,结果也要排队,这样效果其实并不理想。我们应该分层次接待观众,让普通人看热闹,让专家看门道。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是通过门票价格和时间来控制观众的,效果不错,您是专家,就看专场,门票贵。一般学生甚至免票。它也接受富人捐赠,有时一个艺术展会安排三场开幕典礼,捐100万美元的人参加第一场,与政府要员和著名艺术家一起出场,捐50万美元的参加第二场,捐10万美元的参加第三场,大家都作贡献,又都给了面子。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这个博物馆的社会意义? 从1997年1月18日正式开放以来,我这个博物馆已经走过了不轻松的7年:没有政府拨款,没有大企业赞助;举办了十余个展览,接待了数万名国内外参观者,其中有国内外政要、外交官和艺术家,连古斯塔夫·艾克的夫人也来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博物馆、西雅图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海内外研究机构的专家同行专程前来交流切磋。这个博物馆对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对扩大古典家具的文化影响也起到了作用。现在我们在杭州仿宋的河坊街上有一个馆,最近在山西榆次还要建一个,几万件山西家具将在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寺院里展出,榆次市委书记给了很大的支持。厦门鼓浪屿也有一个。 我觉得博物馆的教化是对全民族的,会有一种长期的作用。从博物馆注册以后,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让这个博物馆对社会有用,而且一定要完整有效,不能因个人的情况变化而消亡。接下来我还想建立股份制,我的博物馆是私立的而不是私人的。这一点请注意。也就是说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通过股份制的运作,产生经济效益,使博物馆的建设进入更佳的状态。 记者:您现在拥有多少件收藏品?您想过没有它们将来的归宿? 马未都:瓷器和家具大概各有一千多件吧。至于归宿,我的想法很简单,将来把博物馆完整有效地转交给社会,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是卡耐基,他有一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一个人在巨大的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神话结束了,空间还有吗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在上海也建一个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比如买下一座老洋房,在里面摆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家具? 马未都:曾经想过。1998年5月我就办过一个“海上怀旧展”,用海派家具营造出一个老上海的生活场景,结果参观人的很多。请柬上这样写道:“阿拉请侬来白相”,北京人都读不明白,但见到海派家具都啧啧赞叹。 记者:这是在京派的大本营张扬海派文化。这些海派家具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马未都:都是从你们上海收的呀。海派家具记录的文化信息很丰富,是中西文化在家具中大融合的见证,它说明当时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心态是很轻松的。 记者:有人认为,上海的艺术市场还不够成熟,同样一件艺术品,在北京就能拍得很高,而在上海拍不高。您认为上海现在的民间收藏态势如何?现在的艺术品还有没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马未都:上海人投资艺术品比较理智,不像北方人容易冲动,一冲动就会把价格推上去。上海在过去是中国收藏界的半壁江山,有历史文化底蕴,收藏事业的繁荣是必然的。将来上海还能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收藏家一定会越来越多。 至于说到艺术品的升值空间,过去的20年是复苏期,基点太低,结果导致价值旱地拔葱,一翻就是几十倍,这样的传奇将来不大可能再现了。但中国内地的艺术品与国际市场普遍认同的价格是有很大距离的,这就是我们进入收藏界的理由吧。简单地说,今年您买下的一件古典艺术品,只要看准了,明年一定升值。80年代初,一对老红木太师椅才二三十元,还没人要,抱回家特占地啊。当时我在上海陕西路旧货商店买一个清雍正青花大盘,直径一尺,才16元。我买的时候,柜台上挤满了人,看热闹。 记者:上海人光看热闹,只有您这个北京人果断下手了。这个盘子的价格在今天至少加三个零再翻一番吧。 马未都:差不多吧。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董都比10年前的价格增加10倍以上,尤其陶瓷,每隔几年就刷新一遍,过去卖几百的现在甚至能卖几千万。因为不少收藏家买进后不肯再拿出来了。流通少了,价格肯定会上去。10年之后一件文物在市场上突破亿元大关不是没有可能。 记者:投资中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马未都:中国不像西方国家,它有委托理财,您可以托专家帮您增值,我们更希望把东西拿在自己手里,然后守着天天看它升值。但我们自个儿作主,学习就很重要了。投资要找那些寓意好的东西,文化要素多的,而且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东西容易升值。 世上没有一件东西像古玩一样,拥有众多的属性:历史遗证、文明发展的坐标、人类精神活动的审美对象等等,携带着隐藏了数千年的信息,没有人能够一次性全部破译。所以,带它回家,并不意味真正拥有。它像一个不知足的情人,让您花费大把大把的金钱、时间,却用沉默来考验您的智力、信念和审美。这也是收藏的最大乐趣。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