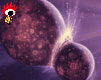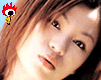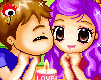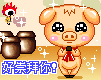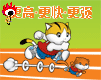| 傅洋:记我的父亲彭真二三事--难忘的日子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8日10:20 法制日报 | |||||||||
|
傅洋 父亲去世快4年了。但于我而言,他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常常让我产生他并未离我们而去的感觉。的确,父亲的思想,永远不会离我而去。 父亲的思想,对我的世界观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思想,已经比较系统、
揭示谄媚者 父亲曾经说:“拍马屁股,是为了骑马。拍你的马屁,也是为了骑你。”谈笑间,父亲将谄媚者的嘴脸揭露无遗,揭示了乐于接受谄媚者的愚蠢。 我做律师以后,父亲对我说:×××在旧社会是名律师,蒋介石也很给面子。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也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能放人。解放后,有一次他为一个坏人向毛泽东主席求情,他也不清楚那人做了什么。主席要我处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两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给他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他再也不说什么了。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 巧论判例法 大概是1975年下半年,父亲刚刚被流放到商洛山中。那里煤炉子很怪,我们都用不好。特别是封火以后,再打开时,往往被我们左捅右捅捅灭了。父亲琢磨了一些时候,找到了办法。他在打开火时,看准位置,用炉钎子一下子捅到底,火苗一会儿就呼呼地冒起来了。 他说,这和干工作一样,没弄清情况,一通乱捅,就把火捅死了。一定要看准了,一下子捅到底,气顺了,火就上来了。 对于搞判例,父亲认为:不能那么搞。判例法在中国早就有了。大唐律例,律是皇帝定的,例就是大理寺的判例。清朝有大清律例。那时绍兴师爷很有名,刑名师爷和你们律师差不多。一代一代形成的案例堆成山,很多自相矛盾,县官也弄不清。你有案子求师爷,你想怎么办,他都能给你找出对你有利的案例。我们的法律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搞了一大堆案例,谁也说不清,那怎么行? 判例的问题,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父亲的观点,总还是渗透着历史的反思的,也代表一家之言吧。 实事求是公私分明 父亲多次谈到:我只管一万,不管万一。不能事无巨细都管。 他复出工作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也是如此。父亲曾回忆说:我是负责协调政法政策,不是批具体案子。那时我只批过××儿子的一个案子。我批的是,不能因为是××的儿子就放纵,也不能因为是××的儿子就重判。那也是谈政策问题,不是具体谈案子。 八十年代父亲主持修改《宪法》时,我对修改草案想提点意见,写成一封信。还给母亲写了封信:“妈妈:宪法中一点问题老想和爸爸谈一下,但总看他很疲劳,就写了一下,等爸爸有空时看一下。” 父亲把信转给王汉斌、项淳一、胡绳同志:“汉斌、淳一同志:这是傅洋的一点意见,请阅后退我,也可给胡绳同志看看。因为他也是个公民、群众,当然这是句笑话。彭真三月十八日” 家中政治纪律之严,由此也可见一斑。 妙言“批评与自我批评” 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父亲有段很有趣的话,他说:一个人做事基本上对的时候,他作自我批评容易。基本上做错的时候,就难作自我批评了。所以要有别人批评帮助。 谈起“文化革命”蒙难,父亲少有戚戚之情,倒是有时颇为“自豪”地讲些那时的故事,充满了乐观之情。 “文化革命”初,一些红卫兵冲进家里批斗父亲。那天我回家听父亲说:红卫兵要我下跪,我说你们不是‘破四旧’吗?下跪是封建的,怎么还要我下跪?红卫兵也不好再要我下跪了。 “文化革命”后父亲曾提起:受批斗要会对付。反正批斗要揪后脖领子,要斗我时,我领口从来不扣,他就勒不着你了。冬天批斗时,他反正不让你戴帽子,所以那些年冬天我就是露天也从不戴帽子,也就不感冒。 历史不能改写 父亲多次对我说:搞案子一定要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他不说,你就逼,你逼他就供,他供你就信,这就是“逼、供、信”。历史上搞错案,很多都是这个原因。所以,刑诉法要规定,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没有口供,而其他证据确实的也可能定罪。所以,刑法还要规定刑讯逼供是犯罪。 我们参加整理父亲的文选。他说:我过去的东西,有的可以不收,有的话可以删,但不能改、不能加,那是历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序,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新思想,那是因为宣言是历史文件,不能改,只能通过写序补充。 也谈婚姻法 父亲常说:没有人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曾说,有人把他的《体育之研究》找出来重印,那时他根本还不懂马克思主义,里边很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人的思想总是不断在实践中变化的。父亲特别向我们推崇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父亲在谈离婚的法定条件时,曾提到:婚姻能不能继续的基础,只能是看感情。你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我在延安当组织部长,那时离婚要找组织部。来打离婚的人,如果还有感情,劝一劝就和好了。真没了感情,你怎么劝都不成。 即席讲演 父亲的即席讲演是出了名的。但只有我们知道,每次讲演前,他都不知要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去思考、准备。他说:这个习惯是在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会儿又不能拿讲稿,只能事先下功夫想清楚讲什么,怎么讲。 父亲讲,自己实际只有“高小”文化,上了中学就搞革命,没有真正读过书了。可我们看他四十年代初,就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给中央的报告,深感他那时在法律方面就有很深的造诣,很是奇怪。 对此他说,我是在国民党监狱里坐了六年半牢学的法律。监狱不让看别的书,但可以看《六法全书》。我们首先是要研究怎么对付他们,对法律也就作了研究。 上面是我对父亲一些思想片段的回忆,虽然有些零散,但它仍然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正是因为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其中,才使这些小小的思想片段也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父亲生于一九○二年,卒于一九九七年,近于与世纪同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之际,刊发这篇短文,也算是寄托了我对父亲的怀念。(作者现为全国律协副会长、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 相关专题:新浪人物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浪人物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