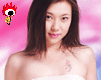毕飞宇:有理想就会有疼痛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5日16:05 中国青年杂志 | ||||||||
|
毕飞宇 40岁,著有中短篇小说近百部。近两年来,他成了获奖专业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冯牧文学奖、小说月 报奖、小说选刊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庄重文文学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去年非典期间,他又 出版了小说《玉米》。毕飞宇说:《玉米》是他的最爱,是他为年轻一代人写的,他希望他们喜欢。
今年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毕飞宇的文集,一套四卷:《这一半》 《冒失的脚印》《轮子是圆的》《黑衣裳》 。 毕飞宇说,十多年前,因为年轻,更因为自负,他总是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去做。他说,那时候,他的创作是那样的 仓促和义无反顾,贪大,逞能,倔强和执拗…… 采访-本刊记者高晓春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饱经风霜 《中国青年》:许多人是通过《青衣》知道并喜欢你的作品的。在这之前是《上海往事》,导演张艺谋把它拍成了电 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之后是《玉米》,去年非典期间出版,一出版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你从事写作十多年,出版 了近百部中、短篇小说,从一开始的明清题材(顺便说一句,阅读你早期作品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位70岁的老翁)到后来的 ,你常常写一些发生在农村的复杂故事,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你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 毕飞宇:我喜欢读传记,那里面饱经风霜的人物,常常令我羡慕不已。我也希望能和他们一样饱经沧桑,可惜的是, 我的经历很简单,并且还特别的日常化和大众化,出生、读小学、读大学、分配工作,然后是写作,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其 实,生活本身并没有提供给我那种足够的材料,让我去从事文学创作。 如果真要从经历中找些引领我走向文学道路的原由,那只能是——在咱们的国家,它的乡村,它的小镇,它的县城, 它的小城市,它的中等城市,它的大城市,我是一路生活过来的,是它让我有机会见识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当我对它们 作判断的时候,当我写这些人和事儿的时候,就来得比较方便,就有了比别人多的参照系。 《中国青年》:按照王蒙先生的话说,就是你敢“抡”。可在我们的印象里,你“抡”得最好的还是乡村生活。 毕飞宇:我生在乡村,那时候,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尽管我的父母不是农民,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到了那里 )。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我们家搬到了镇子里,那种既时髦又守旧的——在农民面前,它显得时髦,在城市面前,它显得守 旧的那么一种怪怪的地方。紧接着我们到了县城,可以这么说,县城是中国“最大”的地方了,等你再往上走,你到了城市, 到了大城市,又会忽然发现,生活的圈子其实又缩小了。不是吗?在县城里生活,你几乎可以认识这个县三分之一,甚至是一 半的人,你和他们是熟人,你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能传播得很远,传到学校,传到机关,传到政府,传到工厂,甚至传到郊区 的农民那里。在这种意义上,县城比城市大,比城市有意思。而在规模上,县城具备了城市的影子。等你到了城市后——小城 市还好一些,比如说,到了南京、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刚才咱们说过,到了这样的城市,你的生活圈子实际上是缩小了 的:是的,你住在一幢20多层的高楼里,但可能你连对门的那个邻居都不认识;然后,你去上班,大马路上车水马龙,想一 想,其实它也和你没有多大的关系,它不构成你的生活,充其量是你生活的背景而已;你到了单位,见到的就是有限的那么几 个同事......然而,城市虽"小",但它高,正因为高,也就看得远--你站在北京,站在上海,站在南京,一下子, 你就能眺望到纽约,眺望到巴黎......是大城市给你提供了无限眺望的空间。不像在乡村,李家庄到王家庄,信息就不 通了,就阻断了。这就是乡村和城市的差别,正因为这种差别,人的感觉就不同,心态也不同。 《中国青年》:你的意思:写作是生活给予你的馈赠? 毕飞宇:对。现在想来,我可能未必写得好,但是确实没有什么我不敢写的东西——因为我经历过,因为我从那里来 。 争斗与疼痛 《中国青年》:无论是乡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你常常写到“争斗”:人与自然的争斗,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为什么 ? 毕飞宇:人就是个矛盾体,矛盾就是疼痛。只要你内心有源源不断的理想,疼痛就会继续下去。是的,我的小说里是 记录和描摹了形形色色的“争斗”,可能因为我是60年代生人的缘故吧--在那个无视自然法则的年代,其一是人与自然争 斗。我看见了--乡村的人们为改良盐碱滩,决定"用土地埋葬土地",结果呢,世界是稻米的,也是蒲苇的,但归根结底还 是蒲苇的。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人群中有"窝里斗",例如,为沾点儿"鱼腥",机关算尽,但最终是什么样子呢?最 终是臭烘烘地收尾。 《中国青年》:你的笔下,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是不一样的,比如,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争斗,女人与男人的争斗。 毕飞宇:同性之间是紧张对峙的关系;而异性之间,不管他们是同居、已婚,还是离异,肉搏和“冷战”是家常便饭 。女性在战斗之初总占了上风,她们会呈现出可怕的战争耐力、才华、创造性,女人会建立最强大的统一战线,会凭空激发起 同情心、爱、权利、义务等伟大话题,揭发批判男人的“乡巴佬”身份、无能、负心、“不是东西”。男人只好无力地逃走, 沉浸在苏格拉底般的冥想当中。男女“斗”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婚姻成为替罪羊,同时也伤害了孩子。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因为心中有梦,我们才会去斗争;也因为心里有疼痛,我们才活得如此真实。 写《玉米》的时候,我就写了玉米与形形色色的人之间的争斗。我沿着自己的想像力,沿着自己的情感,搅在玉米的 争斗中,于是,小说就变成了生活本身,它没有那么多所谓美学和艺术上的难度——我与玉米交流,与玉米相处,我陪着她争 斗,我看着她成功后得意,失败后不甘心,有的时候,她会自然而然地做出一些动作,当她做出这些动作的时候,不仅吓了读 者一跳,也吓了写作者一跳。 《中国青年》:你总是说到疼痛,你如何理解这两个字? 毕飞宇:我说出我的判断,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批评我。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压抑的,包 括我们的内心和外部的环境,因为,生活远远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放松、舒展、开阔。于是,当有评论家问我创作的母体是什 么的时候,我回答了两个字:疼痛。我抓住了这两个字,就不愿意放弃。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许多作品,许多作家,比如说,他们写农村,写城市,或者写军人,故事不一样,人物不一样 ,最后表达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而我不同,我写农民,写工人,写知识分子,写航天员,故事不一样,人物不一样,但最终 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于是,到现在为止,我只觉得自己写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有不同的名字罢了。 我写《青衣》——唱青衣的筱燕秋是多么迷人的女性,可是她“疼痛”,整部小说写的也就是这两个字。为什么?改 革开放了,我们富裕了,过上好日子了,但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开心不开心?我们的心灵有没有被扭曲?写《青衣》时 ,我特意地把时间限定在1979年到2000年--这21年里发生的故事,这21年里筱燕秋的心灵之痛:年轻的时候, 她没有机会登台唱戏;40岁的时候,机会来了,却又发现自己胖了,已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嫦娥的样子了。之后,她开始减肥 ,以戕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减肥,进一步说,她是热情洋溢地去做这种戕害的:用刀子去割自己的脂肪,用指甲抠自己的脂肪 ......为的是要达到社会认可的女性形象,这种社会认可的形象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她的心灵--她的那种"疼", 从头到尾洋溢在小说里,爆发在小说的结尾。 《中国青年》:是的,生活是压抑的。与筱燕秋一样,女性要参与各种各样的竞争,尽管,其中有些女性因为年龄、 身体等等原因,竞争力下降了或者失去了竞争力,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女人依然要与男人一样承担生活的重负。 毕飞宇:有一次,我应邀去南京大学讲演,一个女同学站起来问:我不觉得有什么疼痛啊?我打了个比方:我和她青 梅竹马。青春期时,我玩儿得很快活,她就不行;我们结为夫妻,新婚之夜,我很幸福,她也不行;我们有了孩子,她还要经 历生产的痛苦……这些还不包括她们所背负生活责任和精神上的痛在内。 我的“人来疯”于是上来了 《中国青年》:说来说去,又说到了生活。 毕飞宇:不是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没有什么,但是,我和这个世界有关系,这就是我活的理由和写作的源头。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简单,已经简单到最为充分、最为饱满的程度,就像是,这个世界里,因为阻隔,男人成了男人,女人成了 女人,父母成了父母,儿女成了儿女。然而,谁都不会为此而绝望,相反,我们精力充沛地延续了生活:男人爱上了女人,女 人爱上了男人,父母生下了儿女,儿女成长为父母。这不仅是一个世俗的场景,也是我们存在的力量。 《中国青年》:写作在你的“世俗场景”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毕飞宇:我并未觉得写作有多么重要,好像离了它我就活不了了,没到那个程度。我觉得,世界是两面的,一面是我 们生活的现实的世界,还有一面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虚拟的世界。为什么许多从事写作的人很快乐?就是因为他有机会进入两个 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他的心中相互补充,两个世界相互印证,两个世界相互说明,两个世界都能成为彼此的借口。对于写作者 来说,可以张开双眼向外部现实世界寻找答案,也可以闭上眼睛向内心寻找答案。这种状态同舞台艺术很相似,使我可以有机 会体验不同的人生。 《中国青年》:你说过,你的人生,有一些他人不知道的精彩,也有一些他人不知道的困惑与沮丧。我们想知道,这 些困惑和精彩是什么? 毕飞宇:我真正开始写小说应该是从1987年的秋天算起。那一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一个人来到南京的一所偏 僻的学校里教书。由于刚刚从繁重的学业中解脱出来,除了教课、踢球,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没有能力处理无穷 无尽的时光和无穷无尽的精力。这是一段失重的日子,更是一段迷惘的日子。现在经常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说, 这是命运。当你百无聊赖的时候,当你一点都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你的面前潜伏了无限多样的可能,而事实上,你最终放 弃了所有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顺从了你的本能。本能潜伏在我的血液中,季节一到,势必春暖花开。所以我说:这是命运。 到了晚上,同事们都睡下了,我睡不着,顺手拿起一枝笔,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或者3点。每天都是这样。都写了些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生理行为,我必须依靠写作把无穷无尽的时间折腾完,同时把 无穷无尽的精力折腾完,然后,心安理得,洗洗睡下。如果,允许我打个比方,那个时候我只是一辆油箱里装满了油的汽车, 钥匙一转就轰隆作响,只不过,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也没有目标,甚至没有道路。 《中国青年》:于是,就写了被退,退了再写? 毕飞宇:是的,从1987年到1991年,这几年的光景我就是在写了被退、退了再写的状态下过来的。我决定把 自己当作赌注,全部押上去。因为年轻,更因为自负,也许还因为郁闷和狂妄,我总是挑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去做。我的创作 是那样的仓促和义无反顾,贪大,逞能,倔强,执拗。 《中国青年》:这是许多文学青年共同的经历。 毕飞宇:我知道,我的作品并不像我当初以为的那样,字字句句闪金光,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小部分。这之后我写了 《上海往事》,你上面提到过它,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小说,是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本,因为我不熟悉剧本的 创作,在样式上,我就把它写成了小说。再之后的一些小说,它们就不断地获奖了。当然,这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可是让我 振奋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这个门外汉似乎离文学的大门又靠近了一步,透过大门的门缝,我终于看到了文学神奇的光芒 。它是迷人的,也是仁慈的,它不管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幸运者还是倒霉蛋,只要你爱它,亲近它,它就一定会给 你温暖。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温暖来自文学的身体,它就是文学的体温。在今天我只能这么说,当我孤立地站在遥远的地 方自认为感受到文学的体温时,我夸张了这种温度,也得到了异样的鼓舞,我的“人来疯”于是上来了。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青年》杂志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