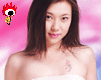探访陕西省商洛市艾滋病后遗症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1日09:25 新周报 | ||||||||||||
|
《新周报》驻西安记者杜光利方正 四年前的“重型丙肝调查” 2001年初,陕西省商洛市有关部门曾在所属7个县市 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这次对外宣称为“重型丙肝普查”的调查,实际上要查的是HIV病毒(艾滋病毒)
元旦和春节前后,大批卫生防疫人员走村串乡抽取血样,再由专车送达商州市“重型丙肝流调办公室”,当时的检测现场保密措施很严,除了5名检测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入内,连“现场复印和打字的废纸都要及时销毁掉”。 据说,由于疫情相当严重,考虑到负面影响,持续了3个月的“重型丙肝普查”突然陷入“是否还要进行下去”的争论漩涡。这期间,趁春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相对集中而进行的卖血人群普查计划被搁置。直到8个月后,被中断的调查才得以进行。 2001年3月中旬,有媒体对商洛的艾滋病状况做了调查报道,引起卫生部和国务院的重视,朱镕基总理并作了相关批示,被艾滋病困扰的村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据后来学术渠道公布的数据,当时7个县共有5739人被调查,但据当时的普查摸底,至少有12700多人有过卖血史,这个卖血数字仍被认为远远低于真实的卖血者人数。而这12700人中的大多数,最后都没有被普查检验。 5739名受调查对象中检测出HIV阳性27例。而当地卫生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曾讲,初筛实验室检测HIV呈阳性的人数“远比27人要多,仅第一天检测就发现了26例感染者,后来总共发现有300多例感染者”。 当时任《羊城晚报》记者的赵世龙与《三秦都市报》记者杜光利、王武一起调查此事,并在《羊城晚报》、《南方周末》、《三秦都市报》上予以报道。但西安市公安局一个重案组奉省上命令前来商洛调查“记者资料的来源”和“是谁接待了记者”的情况。“跟审犯人一样,”对知情者逐一谈话做笔录,一位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在外被连夜唤回接受问话。 因为参与报道此事,《三秦都市报》先后有四名记者被当地有关部门点名批评,并遭除名,杜光利、王武先后二次被警方传讯,并被限令不得离开西安。陕西省有关部门还成立了西安和商洛二个专案组,对记者报道内容进行详细回访调查。但最终,记者报道的真实性保护了记者——一名调查组成员私下告诉记者:“上面明令要以泄密罪名治记者,但调查组调查发现的情况比记者报道的内容要严重得多,并据此形成了报告,所以,报道的记者们才没事过了关。” 在官方最终“确认”的27例HIV感染者中,山阳县占26例。 2003年11月,山阳县被列入国家第一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成为陕西省仅有的两个示范区中的一个。 后来,商洛市政府又进行过一次筛查,在这次筛查后,公布的HIV感染者人数上升至34例。 据官方透露:目前,商洛地区艾滋病人已普遍接受国家免费药物治疗,并且每年进行5次血化验,大多数病人服药后基本没有药物反应。而且,在我国1995年前后有偿供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普遍进入发病和死亡高峰期时,商洛地区2002 年已知的艾滋病人死亡人数仅为8人,2003年仅死亡2人,2004年还未出现死亡案例。 艾滋病的遗痛 2004年10月17日上午,《新周报》记者来到山阳县高坝镇小洛峪沟村。小洛峪沟村远离镇上,深藏在大山沟里,举目四望,群山连绵。 当年,山阳县高坝镇、中村镇、银花乡的偏僻山村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区,后来,这里成为商洛艾滋病重“灾区”。从2000年开始的三、四年间,小洛峪沟村及周围村子里约有12个青壮年死于艾滋病,这些失去“顶梁柱 ”的家庭和10个现症艾滋病人家庭一样,赤贫化在继续。 小洛峪沟一组,15岁的张玲化名 在脏乱的土屋里给弟弟洗衣服。她在高坝一中上初三,每两个星期只放一天假,放假她就回家照顾一天弟弟。平时,她的13岁的弟弟一个人在家做饭吃。 姐弟俩的父亲张新来是老共产党员,在老山前线的部队服过役。他由于在山西卖血染上了艾滋病,于2002年农历 2月去世,留给家里8000元债务和一个没钱继续施工的“烂尾楼”。父亲死后4个月,母亲到西安打工去了,每月挣300 元钱贴补家用。 “我妈一年回来二、三次,有时打电话到小卖部里,和我们通通话,”张玲说,8月30日,母亲回来丢下350元钱,第二天就走了,现在,姐弟俩手里只剩下20元钱了,母亲还没寄钱回来。去年,民政部门曾给她家190元钱,“今年没有了,只是村上补助了100斤小麦和50元钱”。 屋后山坡100米的地方是父亲的坟茔。张玲说母亲让她好好念书,如果考不上高中就外出打工供弟弟上学。说这话时,眼泪无声地在她脸上划过。 小洛峪沟三组有5位现症病人,只有2人在家。带病的叶全才和妻子到坡地里干农活去了。41岁的杨锦绣正痴痴地坐在家里的火盆旁烤玉米棒,她用木棍翻动着火盆,冲天的灰屑在屋内乱飞。火盆里的火光映红了屋内的一口黑漆棺材。 杨锦绣和她丈夫都是艾滋病人,7年前都在山西稷山县卖过血。现在,丈夫刘世俊已弃她而去。她知道自己的病意味着什么,17岁结婚时没照过像的她,去年专门照了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夹在本子里。 “前年政府给了1000元钱,今年给了200元,一袋米、二袋面和两床被子,”杨锦绣说,“我不识字,无法出去打工,就这样混着”。 瞿诗权和老婆陈淑芳都感染了艾滋病,陈淑芳于2002年6月去世。临死的时候,她留下遗言,“把你的身体顾好 ”。瞿诗权有3个孩子,一男二女,家里欠着9800元债,要账的人把家里的家具都抬走了。 瞿诗权曾一度丧失劳动能力,儿子辍学后到山西煤矿打工,一年挣1000多元养活家庭。2003年春节后,吃完退耕还林的800斤玉米后,吃粮断了顿,后来政府送来了米面油。 瞿诗权是村里惟一的高中生,他用一张红纸写下了自己和妻子卖血的情景,也写了4封对政府提供援助表示感谢的报恩信,贴在墙上。2004年4月,瞿诗权也出门打工去了。 小洛峪沟八组的瞿成财也是艾滋病患者。瞿成财的儿媳妇得知公公的病情后,一生完小孩就跑了,找回来,再跑,再找回来。为了成全儿子一家,瞿成财无奈之下只好外出打工,已有一年多不敢回家。 因为艾滋病,这里的青年人讨不来外村的女子做媳妇,几年时间,小洛峪沟三组没有听到过喜庆的鞭炮。 感染者的自我隐没 在“重型丙肝普查”后,商洛市政府又耗资60万元,对商洛既往有偿供血人群进行了一次筛查,还到山阳县看守所、商州戒毒所和商州监狱等地,对吸毒和性过错人员进行了抗体检测。此次检测后,官方宣布当地HIV感染者增至34例,分布于山阳县、镇安县、商南县、商州区,其中11人已死亡。 但有艾滋病人介绍,当时商洛有数千人去山西卖血,一些到山西卖血的人不想暴露自己,有的常年不回家,政府根本找不到。瞿诗权的弟媳说,光他们村卖血的就有40多人,但抽血检查的只有一半。 距小洛峪沟村15公里的中村镇烟家沟村共有8个组,有800多口人。有很多村民卷入过卖血热潮,但现在公开确定的仅有七、八人。2001年检查“重型丙肝”时,村里动员全村人抽血采样,并当场给一条毛巾作奖励,但好多人检查时跑了。 “我也知道好多小伙卖过血,但他们就是不承认,都害怕传出去找不到媳妇,他们太可怜了。”村主任席忠孝说。 赵强被公认为商洛艾滋病防治工作第一人,曾任商洛市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具有7年的艾滋病防治临床经验。他给《新周报》记者讲述了一个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的案例。 2002年1月,在河南一所大学上学的商南籍学生王涛被查HIV呈阳性,他称当年高考后在同学们凑份子吃饭时拿不出钱,在商南县单采血浆站卖过2次血浆。 2003年7月,王涛的父亲带着他到西安重新进行抗体检测,HIV仍是阳性。他留下的个人资料:王涛,23岁,商南县富水镇人。然而,此后,王涛很快从艾滋病防治中心的视野中消失了,防疫人员在富水镇查无此人,到各派出所查户口也没有找到他。“他的资料全是假的,可以想象他早已做了自我隐没的准备。” “商洛对1994年至1997年有卖血史的人抗体检测能达到90%,但也不可能达到100%,肯定会有漏掉的。”赵强说。 性传播的潜在威胁 “艾滋病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让更多老百姓都知道。”山阳县艾控中心主任席虎斌打算在山阳县城矗立一个大型的艾滋病宣传公益广告牌,但他担心这样是否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向县领导打报告也不知能不能获得批准。 “国家加大了血液采集的管理,这一层的感染也少了,母婴传播已经有了阻断的药物,”赵强断言,性也是商洛HIV 感染者今后传播艾滋病的主要方式。 去年,瞿诗权被雇给别人挖黄姜期间,和商南县赵川镇东河乡的一个寡妇相好了,为此父子反目。今年5月,瞿诗权一甩手又到赵川去了,儿子只好时常送药过去。8月,按他留的电话打过去,找不到他。镇上防疫人员让他的儿子去找,但两天后儿子称已经找不到父亲了。 “山区没有暂住人口登记,我非常担心另外一例感染者就会在那里出现。”赵强估计瞿诗权的病毒载量高,且中断治疗很危险。“我手里有一个社会慈善项目,本来要带他到北京地坛医院或佑安医院去接受治疗的。” 事实上,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是中青年,属性活跃期人群。吃药后症状控制住了,有了体力,和正常人一样,自然也就有着生理和自我完善的需求。 “山民也有性伙伴,而且他还是个艾滋病人。”小洛峪沟三组的艾滋病人刘世俊,四、五年前和本村一个姓夏的有夫之妇吃住在一块,现在县城里租着房,“比两口子还好。” 刘世俊中秋节回来只在自家屋里转一下,就公开住到夏某家去了。2003年抗体检测时,夏某已经被传染了艾滋病病毒,夏的丈夫在外打工,经查没有感染。 丈夫患艾滋病身亡后,山阳县银花镇泉水湾村艾滋病感染者赵淑琴给自己找了一个“上门女婿”(丈夫)。防艾人员几次上门,想指导他们过上安全的性生活,但赵淑琴硬是阻挡,不让检测自己的“女婿”。防艾人员给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讲解自我保护措施,他也只是嘿嘿地笑而不语。 在尊重基本权利的同时,“对艾滋病人行为的干预和‘另一半’机会性感染的预防,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赵强说,这件事操作起来有难度,当地人性观念很保守,政府虽然免费发送了安全套,但他们究竟使用了没有、使用完后是否主动找政府索取,这些都是未知数。 2003年9月,商洛市撤消了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赵强由艾滋病控制改做卫生监督工作了,但他一直想做一件事:为商洛定购、安装10台安全套自动售卖机。 (注:文中部分艾滋病患者及其子女为化名,本版图片已作技术处理。版头题图为艾滋病患者杨锦绣在家里烤火) 相关专题:新周报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周报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