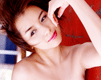专访杜宝良: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钱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6日03:18 新京报 | ||||||||
 昨日,杜宝良蹲在居民大院里翻阅有关杜宝良报道的报纸。  杜宝良抿了抿嘴,头发因为刚睡醒而显得有点杂乱。 对话人物:杜宝良“105次”违章当事人,安徽芜湖地区农民,在京12年以卖菜为生。 对话动机: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记录在案,缴纳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 昨日下午3时,在南礼士路一居民大院内,记者见到刚在小货车里睡了一觉的当事人杜
6月13日,杜宝良将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告上法庭。按照法定程序,该起诉讼目前正处于“7日审查期”,法院将在近日决定是否受理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 据西城区法院介绍,杜宝良的诉讼请求共有三项内容:撤销错误的处罚决定书;返回已缴纳的万元罚金;依据“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交管部门应承担错误处罚后果,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3000余元。 “人家都说我违章了,我就死心了!” 新京报:你的事,报纸上都有了。你是周一向法院提交的诉讼申请,按照规定,本周五前,法院是否受理才有定论。等待法院结果的日子是不是有点难熬? 杜宝良:等待法院出结果,这没什么不好受的。天天睡不着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段日子才难受。 新京报:据市交管局通报,当初你是主动缴纳的罚款,自愿放弃了申请听证、复议的权利,为什么不为“万元罚款”多做些努力? 杜宝良:我做过努力,我是5月23日知道这码事的,迟了一个星期才交的罚款。外地人买车不给上牌照,我前年买了小货车,就托人找了个公司办手续。5月23日,公司通知我,有人投诉我的车跑起来冒黑烟,不环保,我就赶紧到工行去查;工行查不了,我又到西单交通队,他们告诉我得到月坛执法站。在那,我才知道,冒黑烟不是问题,可我有105次违章,都是摄像头拍的,得罚1万多块钱。 脑袋当时就不好使了,什么事都反应不过来了。后来,我跟执法站的人商量,能不能少罚点,人家说不行。我又找到市人大、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想让他们帮我说句话,少罚点就行。人家都说我确实是违章了,我就死心了,觉得这事只能这样了,罚款不交,小货车就废了。还是保车要紧,因为还得靠它上菜、赚钱。 新京报:开了一年多车,你应该知道有摄像头拍摄这样的执法手段,为什么还要违章呢? 杜宝良:我1993年就到北京了,一直在这(南礼士路一居民大院内)卖菜。 原来是用农用车上菜,走的就是真武庙头条,走了10几年,习惯了。虽然后来路上有了禁行标志,可我没注意,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出来得早,路上车很少,我觉得我没妨碍交通秩序。 我是高中毕业生,在我们老家,也算是一个读书人。可是,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半夜两点多就起床;晚上7、8点钟,别人都吃完饭了,不再买菜了,我才回家。到家吃口饭就睡觉了,不读书,更不看报。家里有台电视机,基本上不看。我真的不知道摄像头这么厉害,也不知道自己得去查违章记录这条规定。要是别人不投诉我“不环保”,这1万多块钱罚款没准涨到多少钱。 “我这是民告官,我心里很清楚。” 新京报:听说,为了交罚款,你借了不少债。交完罚款,你有没有动过找律师的念头? 杜宝良:没有。但是一回家就睡不着觉,觉得冤。 杀了人,投案自首,还能得到宽大处理呢。我是主动找到执法站的,而且也没造成一丁点恶劣后果,为什么就不能从轻发落呢?想来想去,还是自认倒霉。 按迷信的说法,这阵子我有点走“背”字。三月份,我爸得了咽喉癌,手术费八千多块,我爸有两儿两女,我和弟弟分摊,我承担2/ 3.办完这事,我手头就剩2000多块钱,所以,交罚款时我又借了八千多块。卖菜忙活一年,除去房租3600元,吃喝和孩子学费还得花上3000多块钱,顶多能剩一万来块钱。 新京报:从交完罚款至今,有没有再跟交管部门打交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跟交管部门“理论理论”的念头? 杜宝良:交完罚款,就再没跟交警照过面。来北京这么多年,属这段日子最忙,见了好多专家、记者,可能这辈子也见不了这么多。我记得很清楚,交完罚款第二天,我就成了“反面教育”典型,上了报纸。所以,听说有报纸替我喊冤,我压根不信。可记者把报纸送过来了,白纸黑字写着,好几个专家说交警不对。没过两天,找我的记者就不断了。我开始买报纸,上面全是替我说话的,我这时才有点相信了,交管部门可能真有不对的地方,要不,这么多陌生人不可能帮我。 新京报:现在,你是否确信,交管部门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起诉前,心里是否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杜宝良:我这是民告官,我心里很清楚。起诉前,我琢磨了两天,后来觉的律师说得有道理。只要站在理儿上,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帮我,而且不是记者,就是专家、学者,这官司打起来就不一定输。交管部门是有不对的地方,但应该告诉我,我违章了。 最起码,头几次没发现,后来也应该发现我这个“违章大户”。再有,律师说那个禁行标志过期了,无效了。他找来的资料我仔细看了,真的是过期了、无效了,所以,我最后就在起诉书上签了字。 “我只想要回我的钱,别的,我想不了那么多。” 新京报:在你的诉讼请求中,涉及到了国家赔偿,要求交管部门依照国家赔偿规定,赔偿3000多元损失。提出这个请求时,你心里是否有把握? 杜宝良:这个没多想。 我的想法挺简单,还是最开始时的老想法,少罚点就行,退回来一部分就行,家里缺钱用。弟弟来电话,说我爸也听说这事了,全家人都没瞒住。我还没跟他通电话,不知道电话里怎么说。 新京报:现在,你的105次违章已被媒体称为“杜宝良现象”,尤其是提出诉讼请求之后,你与交管部门的纷争不仅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更引起了包括驾驶员群体、法律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交管部门如何认定“失效禁行标志”,法院是否受理这起诉讼,这些问题已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将影响“交通执法”的大事。你是否预见到了这个效果?是否渴望出现这个效果? 杜宝良:说实话,我没想这么多。律师总说,这件事意义重大,这两天,我也看出这个苗头。可是,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钱,别的,我想不了那么多。 “杜宝良现象”备受关注,杜宝良之妻称 “钱肯定要不回来” 本报讯(记者王姝)“天天说,天天说,你累不累啊?过来卖菜!”昨日采访时,杜宝良的妻子兰姐经常对杜宝良瞪眼。“钱肯定要不回来了,他就知道胡忙活。”她说。 下午3时至5时,正是夫妻俩菜摊的黄金时间,买菜的人常排起三五人的小队。兰姐手脚很麻利,账算得很快,一个人撑起了整个菜摊,杜宝良蹲在一边看报纸,找跟自己有关的报道。在南礼士路这个居民大院里,他们的菜摊已经摆了十几年,每个买菜的人都是老主顾,所有人都要问一句,“今天有什么新进展?”“老杜,你的事我们天天关注。” 只要碰到想多聊几句的人,杜宝良就马上跟着对方站到摊位对面,谈自己从专家那里和报道中学来的新观点。这时,兰姐一直用眼盯着他,忍耐五六分钟,就命令杜宝良过来帮忙。杜宝良总是要迟疑一下,兰姐忍不住就要发作,冲杜宝良大喊,“天天说的都是这套话,你能不能不说了?” 她认为,已经交的罚款是要不回来了,所以,两人应该“向前看”,好好卖菜,多多赚钱,这才是正事,没有理由牵扯精力,继续纠缠。“天天睡不着觉,闭上眼睛就是这事,菜都卖不好。”她说。 相关专题:司机为何105次违章 本文采写/本报记者王姝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李冬 相关专题:新京报-核心报道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京报-核心报道专题 > 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