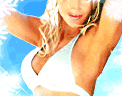新闻记者拍摄5集纪录片记述常德细菌战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2日17:55 南方周末 | |
 以这张老照片为线索,曾海波找到了熟知那段历史的人 □本报记者 万静 8年前的1997年,曾海波作为湖南经济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开始跟踪报道731部队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国原告方败诉。 作为跟踪拍摄的记者,曾海波见证了从起诉到调查、判决的整个过程。他深知中国原 到2003年,他已经拍了90多条关于细菌战诉讼的新闻,收集了八九千分钟的素材,最终和大家见面的,是一个5集的版本,记录了1941年常德细菌战的过程。每集15到19分钟不等,合起来总共80分钟。这是经过六次各级审查之后的版本,最初的版本有6集,每集30分钟,共180分钟。 众里寻他千百度 不论哪个版本,片头的第一个画面都是一张模糊的合影。那是66位参加常德防治鼠疫技术人员的全体合影。 曾海波希望能找到那张照片上面的人,通过他们的口来讲述当年的灾难。曾海波他们拿着那张照片到处去找、去问,但也只能够辨认出中间的五六位。 在寻觅过程中,他们遇到一位87岁的见证者,是民间诊所的医生。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在常德上空投下鼠疫病菌后,国民政府动员所有的中医西医来参加防疫,他也参加了防疫。他突然提到,有一个叫做李杏荪的,当时是红十字会的。 按照这位老人提供的信息,剧组的编导熊泽伟找到了李杏荪。据李杏荪说,他参加的防疫队正好是奥地利医生肯德所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731救护队。当时市民谣传救护队解剖尸体“化验”是拿那些内脏去炼油制药,就不愿意打防疫针。救护队就把打防疫针的摊子摆在戏院门口,不打防疫针就不让进去看戏。他们在全城各地都设了点,但是进城、出城的老百姓一看,就绕着走。 他们通过互联网还找到一个人,叫王诗恒。在常德细菌战的档案中有一份《王诗恒报告》,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松村高夫的著作中曾引用过其中很多内容。报告是用英文写的,但这个名字显然是个中国人名字。曾海波就很奇怪。问松村高夫,但他也不知道。后来曾海波他们通过Google查到,这个人还在协和医院当高级医生,是老专家。他们马上就打电话去问,协和医院的离退办说这个人还活着,但是在高干病房。他们又赶紧辗转打到高干病房,终于找到了她。 王诗恒当时是在美国人办的贵阳医学院读书,要到湖南去实习。听说常德发生鼠疫,她就要求去参加常德防疫队。学校也被她感动了,批准她去。就这样,她作为一个实习医生,去常德参加防疫。那份英文报告就是她的毕业论文。 诉说的未必都是真实的 为了拍摄纪录片,曾海波他们需要去寻找当年的受害人,亲耳听他们诉说日军投下“谷子”(带病菌谷物)之后的事情。 1997年的时候,也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时很多受害者都不愿意谈。 石公桥的李丽枝,她十六七岁那年,跟人订了亲,男方家里害了鼠疫,病得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的族人们就说,这不好,要冲喜,非要两口子在灵堂上成亲。结果也没有挡住鼠疫。他们家染了病的还是都死掉了。就剩下他们一对小夫妻。当时他丈夫还是个学生,在城里读书,所以免过一劫。 他家里本来很富有,结果家破人亡。财产也被亲戚们瓜分完了。小夫妻相依为命,这件事情对丈夫打击非常大,一直郁郁不乐,沉默寡言,后来就自杀了。 东京女子大学聂莉莉教授多次到常德去考察受害者,问到李丽枝的时候,她就说,我都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聂教授的解释是,受害者因为承受太多的灾难和痛苦,只好用失忆来遗忘,减轻自己的痛苦。 但曾海波他们没碰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现在说起来头头是道。” 口述史专家认为,对于久远的、伤痛深刻的事件,回忆者的主观叙述往往会失真。从大量庞杂的叙述中鉴别真相,需要专业性很强的方法。 从年龄来看,如果是80岁以上的,那他1941年时已经20岁了,记忆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摄制组把他所说的跟档案进行对比,看说得是否合情合理。 像李杏荪、王诗恒这样的老人,他们说的就非常可信。他们就说他们知道的那些东西,不知道的就不说。尽管摄制组会失望,但反过来看,他们所说的就更有价值。 即使是杨智慧,因731部队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而广为人知的细菌战幸存者,曾海波他们也还是调查了一番。因为当时留下来的患者名单上写的是“杨珍珠”。曾海波问一个叫龚积刚的早年的调查者,他也怀疑这个杨珍珠可能就是杨智慧。结果就问到杨智慧小名叫珍珠。 越是有仇恨情绪,越是对自己警惕 在最初版本的第五集中有个镜头,是常德市德山镇枫树岗村的诸百万。他的左腿颜色斑斓,淤黑、粉红和石灰状的碎屑交织在一起,而脚趾已经看不出形状,远看就像一段腐烂的木头。另一条腿,也瘦得可怕。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拖着这样一条无法痊愈的伤腿,至今无法站立,只能借助两个小凳子来“行走”。像诸百万这样的“烂腿病”患者,常德并不少见。王选力促成立的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在走村串户中发现,1950年代,当地有不少像诸百万这样的烂腿者,被放在板车上轮流由各村供养。 而这一切,正是源于1941年前后日本731部队对常德的细菌投放。 无独有偶,在浙江省金华和东阳一带,还有“烂腿村”这样的叫法。那也是1940年代日军反复进行细菌战的地区。 面对这些伤痛的故事,曾海波不满足、也不愿意让片子仅仅停留在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层面:“我用得着那么明白地去说吗?”他想传达给观众的,也是他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的:生物战争不能再发生。 “不要以为自己不是受害者,自己亲戚中没有受害者,你就可以漠不关心,实际上世界上的事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曾海波说。 克制正当仇恨的蔓延,克制不良情绪的宣泄,这简直就是一座心灵的炼狱。 “越是有仇恨情绪,越得对自己警惕,因为是在拍纪录片。”曾海波说。他会在片子中努力压制那种情绪,不让它影响这部片子的主题。 在跟一濑敬一郎这样主动调查细菌战的日本人打交道时,曾海波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一方面很尊重一濑这种认真做事的日本人,另一方面,他又会刻意去问一些让一濑难堪的尖刻问题。“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老爸在中国干了坏事?”“你们举证的时候日本国内会不会骂你叛徒卖国贼?”或者,“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在这样问的同时,曾海波又会在心里承认一濑他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而且,一濑他们在面对那些尖刻问题时表现得很大度,仍旧是认真而客气,这一点也让曾海波觉得很佩服。 跟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接触过程,又让曾海波实实在在感到了日本人踏实做事的一面。松村高夫是日本研究细菌战的专家,曾在其著作中引用过《王诗恒报告》。要跟他讨论的话,就必须问具体的问题,比如王诗恒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英文报告,你引用的《井本日记》说到日军飞机为投放病菌下降到800米高度,为什么要到那个高度?这样,他才会觉得这个中国人是有根据的,而不是笼统地讲大道理。 曾海波认为,这部片子归功于所有的工作人员,那些老人家,那些志愿者。“他们的努力最后都浸润到片子里面来了”,“当尾字幕黑压压地蝗虫一样向上翻滚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力量”。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南方周末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