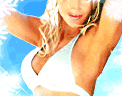陈凯歌:我不在江湖但江湖中有我的传说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2日18:07 新周刊 | |
|
采访/黄俊杰 “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市场做好。” 《新周刊》:你一直对外宣称,包括7年前接受《新周刊》采访的时候,都强调“一个非职业的导演”。你的正当职业是什么? 陈凯歌:若干年前我的意思是说,职业导演如同一个在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负责这一道工序,当产品通过传送带到了你眼前的时候,你不能不做,哪怕就是拧一下螺丝。从导演的角度讲,我不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螺丝来了我一定要拧一下的这样一个状态。 《新周刊》:觉得超出了职业导演,更上一个层次? 陈凯歌:如果说做一个职业导演,其实可能有更多机会,在经济上的收益,你不想做职业导演,你就可能会失去更多商业上的机会。 《新周刊》:感觉很像你所说的那种无极的状态,回到最初。不是职业导演,却随心所欲。这是你一直坚持的吗? 陈凯歌:我不愿意用坚持这个词,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新周刊》:我们一方面看到你的坚持,一方面也看到了你的变化。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变化? 陈凯歌:变化是绝对的事儿。一定有一个力量去推动你,我们希望的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力量。但实际上,也有外部力量去推动。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处于一个变化求存的状态。我们都不讲整个中国电影在绝对数量上对市场的占有率,我们只讲我们现在还有多少电影导演在工作。特别是我这个年龄的,没有很多。努力地去发展这个市场,真的把这个市场做得比较大,才可能出现我们一直期待的多样化的,比较理想的电影。 至于《无极》,有人说我是力奔奥斯卡而去的,其实奥斯卡这样的评选,特别是对于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是一个面非常窄的、一些人所进行的专业操作而已。我觉得奥斯卡是需要争取的,但奥斯卡不是一个跟中国的市场开拓有直接关系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市场做好。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很辛苦。确实是觉得有倦意。” 《新周刊》:回顾一下你自己。你觉得你第一次向世界说,哎,陈凯歌来了,是什么时候? 陈凯歌:我更愿意说在1987年,当我住到了纽约跑到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去做客座教授,在纽约的曼哈顿,下层有一个小小的公寓。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有一种你说的我来了的那种感觉。我来参与一件事儿,参加一件事儿,就有这样的感觉。 《新周刊》:在一个世界的中心? 陈凯歌:对。但我对纽约这座城市其实存在很多的观察。它也真的是教了我很多东西,比如说,看到一些HOMELESS,无家可归者冬天在政府办的地方去喝一口热汤。 《新周刊》:在汽油桶旁边那种? 陈凯歌:对,的确是这样的,这样火点着。纽约比北京还冷,常常风雪交加,让人想起一个风雪夜归人的景象。但你可以看到,它是很能够养穷人的城市,它是很能够保护所谓多样性的城市。举这个例子,还是回到我们怎样发展中国电影市场的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它变得很大的时候,它的包容性就自然随之增大了。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做到这样,大起来,可能有很多新晋者,用比较小的资本,却做这种有趣的电影。 《新周刊》:人们过去认为你像一个知识分子,很喜欢絮絮叨叨的,在电影里头讲述道理,给人一种受教育的感觉。现在《无极》也会吗? 陈凯歌:在我早期的电影中间,我感受到很多的沉痛。这很多的沉痛一定变化成一种人的形态,在电影中表露出来。但我自己觉得,你不可能永远沉浸在一个特定的情绪里,《无极》这样的一部电影,我感觉到一丝希望。如果一部电影能够真的向观众提供这种小小的希望,已经是功莫大焉。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很辛苦。确实是觉得有倦意。 “我现在要转型了,因为取悦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新周刊》:可能看你的电影会看到场面很宏大,但细节很精巧,所以人们会说陈凯歌拍一部片子真的是太认真了。 陈凯歌:是,所以对于电影我一直赞美它,说它给了我一种生命的感觉。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处理好电影和我的关系,电影变成了我的心魔了。(双手放在胸前) 《新周刊》:(心魔)不是陈红了? 陈凯歌:陈红也是。这个心魔的意思是,你把电影做成这样的时候,它已经有宿命感了。这种宿命感有时候让我觉得,它对我有控制力。到底是我在控制一部电影的出现,还是电影在控制我。这个呢,你讲到,你既要有宏大,又要有细腻,这是真不容易做到的。 《新周刊》:可见你还是很传统,追求古典主义那样意义和细节的完美、严谨。 陈凯歌:因为现在我们的尴尬在于,必须接受古典主义文学或电影的影响时间很长,处在这样的一个美学的倾向被放弃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尴尬。这是一个技术型的年代,技术的发展带来产品的更新,物质的轮子越转越快,心灵活动的空间被极大地挤压,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新周刊》:所以你变了。 陈凯歌:不是变了。我们一定有很多的彷徨。 《新周刊》:会不会因为你的彷徨,使得你从知识分子加艺术青年,变成了一个考虑商业因素的导演? 陈凯歌:一直有一个两难的情形。你是否能在你的电影中间一直保持你的一个心情:我为电影而做电影,还是说我为他人或为自己去做电影。其实保持我为电影而做电影这样一个心情,会给你的实际操作带来很多困惑和快乐。但你不能回避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所有的导演都会不再提起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商人的问题。这个去争取很好的成绩,包括票房的成绩,是做电影导演的其中要义之一。 《新周刊》:其实想起跟观众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陈凯歌:其实我一直是这样的。像《黄土地》这样的电影,你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代首先想到的是商业?首先那个社会没有商业的气氛。但到《霸王别姬》,我随心所欲地去拍一个看去很热闹的商业的电影,但仍然没有丧失我们最终想表达的东西。不是说一个导演在拍另一种类型电影的时候,是可以很顺畅的,因为意图明确就可以完成过渡,不一定的,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才能。拍《黄土地》我很高兴,拍《霸王别姬》也很高兴。随心所欲地去做事情,没有刻意地想,我现在要转型了。因为取悦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就电影,以取悦为目的,很难成功。 “陈红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怎样更加本性地去看待自己。” 《新周刊》:在《无极》剧情中,王妃倾城被奴隶昆仑用光速带回了过去。如果选择一个人带你回过去,你希望塑造一个怎样的自己? 陈凯歌:(思索)塑造一个命运不同的自己。 《新周刊》:怎么个不同法? 陈凯歌: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工作或者一个职业让我不至于那么辛苦。 《新周刊》:还会跟电影有关吗? 陈凯歌:其实真的无法预测。事实上是难以发生的事儿。可能没关系。 《新周刊》:那么带你回去的人会是谁?如果非得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场景,陈导演,你自己导演的,你会选择哪一个演员,在你人生中出现的。 陈凯歌:只能是我自己的母亲。她真正给我力量。我现在变成今天这样,全是因为我母亲。大家印象中,我好像是个知识分子那样的。大家没有在意我有没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但其实我的这些所谓气质,全是从我的母亲那里来的。一方面她从小让我接触了很多文字,另一个方式是,我母亲长年抱病在家,她使我有一种无形的精神上的紧张。我一定要把我该做的事做好,不然会使我卧病的母亲更加不安。我走路永远都是轻手轻脚的,因为怕影响她。长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造成了我其实对事情的看法比较紧张。 《新周刊》:那现在影响你最深的人是谁? 陈凯歌:我和陈红有夫妻和合作的关系。她也常常会给我建议。 《新周刊》:她会拿你的片子和其他导演的片子比较吗? 陈凯歌:不会。陈红不是一个研究者。她是很本能的。陈红的本能很好。大家都以为陈红帮我打理制作上方方面面,这个工作当然她做了,也做得挺成功。但对我来说,陈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怎样更加本性地去看待自己。 “我没有江湖心,我没有想做老大。” 《新周刊》:如果现在要研究中国的一个电影史,我们谈到陈凯歌,无法忽略张艺谋。其实你是否发现《无极》和《千里走单骑》这两部片发片前,有特别多的媒体研究你们俩。你会因此困扰吗? 陈凯歌:我这个人对所有的事儿都不知半点,基本没有什么评论。我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没有反应。 《新周刊》:如果说电影圈是一个江湖,你觉得自己是哪一个派别? 陈凯歌:我真实的状态是,我是人不在江湖。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纷争都与我无关。因为你有江湖心的话,你必要在江湖中行走。我没有江湖心,这个确实,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做老大。所以我就是人不在江湖上。但是就我这样一个人不在江湖上的人,江湖有传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能说我人不在江湖,我还是在江湖。但只是,从我的角度讲,我觉得我不在江湖。 《新周刊》:你是一个非职业的江湖人。 陈凯歌:对。我觉得江湖是要有江湖的行头。 《新周刊》:你起码是个掌门吧。 陈凯歌:我没有江湖的行头。说到掌门,就更加不可能了。为什么呢,因为掌门必有地址。我是没有地址的,是无门。我一直对所有的事情处之淡然,我遇到什么问题都不会与人激辩,去求一个公道。江湖一定要求公道的,讨一个公道,或讨一个说法。其实当你不要讨一个说法的时候,这个说法已经有了。是不是? 不过我很感谢你问的问题。如果你不问,我还真不会这样表达。你问得对了。我一直是这样,我没有江湖的恩怨和是非。 《新周刊》:听上去你很超脱。 陈凯歌:因为这个也是对我们现状的一个间接的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们这样一个激烈变动的社会环境里,出现大的小的摩擦和冲突是经常的事,但你能够在电影里头去表达一些你……我觉得我是用爱去涵盖起来,包括《无极》,这是我间接的态度。 相关专题:新周刊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