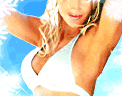社会责任感还能带来快乐吗?(上)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2日19:13 中国青年杂志 | |||||||||
|
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社会责任感之于人们的重量是不尽相同的。但在任何社会形态里,责任感对于人的作用与意义却都是相同的——正如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当一个人富有责任心时,他的自我便真正开始形成,同时,其立志开始,影响力随之增大,义务随之增多。 与自我、影响力以及义务同时到来的,或许还有责任感所带来的情绪上的烦恼甚至痛苦。当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责任感的人似乎生活得更快乐更轻松,而那些有责 整个社会的痛感,难道一定要由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来分担吗?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社会责任感是种荣耀,那么在如今,它还能带来快乐吗?又有多少快乐可言? 为解放更大的痛苦而承受痛苦,就是快乐 文-秦兵(律师) 在某市一件非法拆迁案件中,我是原告,也就是住户的代理律师,我们的被告是开发商。 几百名居民陆续领取了几万元补偿款离开了自己家,他们的房屋也已经被拆除,东西被强制拉走,区政府的裁决书也下来了,裁决居民败诉;必须在七天之内从家中离开,否则将强制执行! 我一遍遍地看卷,我们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区政府的行政行为,我不断假想,开庭的时候区政府会如何举证呢?他们会怎么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开庭当天,当法官即将宣布进行法庭调查时,我举起了手。 法官说:原告律师,有事吗? 我说:刚才法庭进行身份核实时,我知道对方的代理人分别为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说:是的。 我说:我们希望法庭注意,我方提交的证人名单里,就有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看了看名单,说:是的。 我说:在我们提交的出庭证人名单里,也有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看了看另外一份申请,说:是的。 我说:今天王先生和赵先生都到庭了,我们希望法庭明确他们的证人身份。 法官沉默。 我大声说:我们希望法庭明确他们的证人身份。 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低头商量,然后说:我们继续进行法庭调查。 我坚持:本人希望法庭明确证人。 法官问:秦律师,你到底想做什么?你现在必须说明,否则法庭将继续审理。 我说:根据诉讼法第25条的要求,我们有权申请证人;根据诉讼法第30条的规定,王先生与赵先生是合格的证人;根据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根据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证人不得旁听开庭。因此,我们希望法庭确定两位先生的证人身份,然后请他们退庭! 法官问:秦律师,他们两位退庭后,被告方就没有人了,怎么审理? 我说:这不是我要关注的事情,是对方的事情,我只希望依法办事,请两位证人退庭。 法官又问:秦律师,如果两位证人退庭了,这个案件就不能审了。 我说:我不管是否能审,只希望法庭依法审理此案,从程序上保证诉讼法的权威。 这时,坐在法庭后面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一挥手…… 几位法官都看着他……然后主审法官说:现在休庭。 15分钟后,法官再次出现。说:考虑到本案的情况,法庭不同意原告律师的申请,继续开庭。 我问:法庭为什么不同意本人的请求?本人的请求违法吗? 法官说:法庭有自由裁量权。 我说:本人认为法庭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体现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上,目前的情况是,法律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庭应当遵守,法官不应首先违法。 法官说:法庭认为应当继续审理。 我说:我希望法庭首先尊重法律的尊严,法庭不应当违法。 法官说:秦律师,如果我们同意你的请求,让对方证人退庭,本案今天就不开庭了。 我说:为什么不开庭呢?诉讼法上不是已经写明了吗? 法官说:你不就是想用诉讼法第5条:被告退庭的,视为没有证据没有理由,可以直接判你方胜诉吗? 我说:对,我们就是要用这一条。 法官说:我们不同意。 我说:这是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庭也应当遵守。 法官最后说:本庭已经确认,决定再次休庭,具体开庭时间另行确定。 第二天,业主来电话说,他们当天晚上与法院一直谈到深夜,法院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与开发商进行协商,尽可能满足业主的要求。 我们事后才知道,那天开庭时,坐在最后面的是他们的院长……第一次开庭的结果给予对方巨大的压力,区政府和法院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谁都不敢轻易为开发商解脱责任。 不久,我们得到若干消息,已经有人开始向区长提出建议了,市里也要求他就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很多记者从各地来到当地进行采访,大家想不到中国民主选举竟然从拆迁中展开了,50多年来选举第一次在当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这时谈判也在不断进行,人大、市政府和法院都加入了谈判,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这件事情的性质升级,所以每个人都比较积极地参与进来。 有一天,我正在陪女儿玩游戏,法院打来电话说:秦律师,咱们都省心了——原告撤诉了。 也就是说,我们胜利了——开发商同意赔偿! 现在回想,这件事情确实费了我不少心血,作为一个律师,他的职业目的当然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如果说其中有快乐,多数时候,只是短暂的一瞬。更多的时候则是愤怒、忧心与痛苦。然而,为着解放更大的痛苦而承受痛苦,却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快乐,它使你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尽管微不足道,但是在推动社会正义的进程中,融入了你的力量。 对于一个生命个体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你的价值。 责任感的快乐,源自对自己的尊重 文-张大诺(临终关怀志愿者) “有没有人管啊,有人被推河里了,出人命了。” 在北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一个快90岁的奶奶在院子里喊着。 我走过去,问了几句,明白了这其实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她或者做了一个梦,或者想起了过去的什么事情,把它当作真事了。 做了两年临终关怀志愿者,我清楚地知道事情是假的,但她的急切是真的。于是就有了我们以下的对话: “奶奶,那个坏蛋已经被抓起来了。” “是吗?” “他们没有告诉你吗?这里的人都知道了,我以为已经告诉你了呢。” “噢,那他们忘告诉我了。” “现在知道了,没事了,没事了……”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奶奶没事了,不喊了,继续坐在轮椅上,面容安详地晒太阳。 在做临终关怀志愿者前半年的时候,每周我只来这里一次,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明白,这些病人对我来说不仅是“献爱心”的对象,而且是一种“逃不掉”的责任。 一个快90的奶奶一直以为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所有人都心怀恐惧,我知道后,心想着下一周去看看她,看能不能帮上她。 但当我真的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 她常坐的轮椅还空荡荡地放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是在对这个世界的恐惧中走的,在对每个人的恐惧中走的,而我,本可以减轻她的恐惧,只要我能多来几次。 在把爱心转为责任的时候,我首先体会到的是一种疲惫,甚至痛苦。一周去三四次,合在一起将近十个小时,每天来回三个小时路程,回家的时候在地铁里一坐下就开始睡觉,借以恢复体力。周末的时候我会在医院待一天,中午没地方午休(必须放松一下大脑),没办法只能到城铁车站里,坐在候车椅子上睡觉。那时候我也问自己:真的要守住这份责任吗?把它改成以往那样,方便的时候偶尔看一次,不也一样吗?也没人说你什么。 但每次,当我下午再走进医院院子时,那么多老人一看见我,刹那间眉开眼笑的,看着这些老人,我甚至觉得他们像是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一刻,我的内心非常快乐。 后来发现,这份“责任”带给我的快乐远不止这些。 走在走廊里,医生、护士以及护工都在对我微笑,整个一天下来,能“收获”几十次这样的微笑。想一想,有谁能够在一天里拥有这么多真诚的微笑,心灵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份瞬间而生的温暖,它真的让我这一天仿佛都有阳光的味道。如果我没有这份责任感,这微笑不会属于我。 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我常去看的一个奶奶的女儿,信中表达着对我的感谢,言语非常诚恳,还附带了一份小礼物。那一刻真的有一份惊喜,不自觉间,这之后三四天内,一想起这封信,我都很高兴,包括在我心情沮丧的时候。后来我想,在我有这份责任感时,就注定了会有这样一封信,或者类似的东西,注定了它将带给我快乐以及对生活中某些沮丧时刻的慰藉。 责任感,与其说是一种感觉,不如说是一个有趣的链条,它开了头,就必然会引发什么,“躲”也躲不掉…… 两个同室的临终病人吵架了,他们分别向我诉苦,我分别作着调解,告诉她们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把原来两人认为的对方人格问题转为生活习惯以及性格的冲突,后来我再去她们屋子时,发现一方托人为另一方买了一小盒烤肉…… 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我多大的“成绩”,但过后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来说,生命是按小时计算的,而我帮助他们抢回了一大段快乐或者平静的“小时”,那一刻,内心中突然有了巨大的成就感以及一份深沉的快乐。说它深沉,是因为在这个快乐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它能持续一生。即使我到了像他们那样老的时候,只要我还能记起这个事,就还会有这份快乐。 其实,有责任感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理所当然,在“理所当然”中也就不觉得那么快乐。但经过了这件事,我开始告诉自己:你并没有真正发现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除非你明白: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在做着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你,在某些方面,事情真的有点不一样——这么想不是为了获得快乐与幸福,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一旦有了这种尊重,就有了幸福与快乐。 如此,我想,对这些临终病人的关怀会是我一生的责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将有一生的快乐? 有些东西比快乐更重要 文-刘鉴强(《南方周末》记者) 当我回忆采写“两个男孩高尔夫球场神秘死亡”时,会再一次陷入痛苦之中。这是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最难以忍受的采访经历。 去年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两个8岁男孩进入邻近的高尔夫球场玩耍,失踪17小时后,被发现死在高尔夫球场的人工湖里。根据种种可疑迹象,死者亲属认为,孩子死之前曾遭遇了暴力折磨,甚至有理由怀疑孩子是被成人投入水中淹死。 2004年的3月12日,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我听两个父亲对我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作为父亲,我能体会到那种痛苦。在聆听讲述的五个小时里,我感到周身发冷,时时要压抑住大哭的冲动。 第一次采访结束,我没有坐车,只是匆匆地走着,用脚步来整理杂乱的思绪。 我的心怦怦跳着,我听到它的呼喊:“我一定要写出来!” 我不能容忍。我不能容忍那些恶劣的黑手伤害孩子。 我知道,采写这样的稿件有风险……情绪激动地走在街上,我想,如果我最终因为得罪权势而受到惩罚,比如被上头强制开除,值得吗? 值得!没有什么比孩子的生命更重要! 我第一次有这样强烈的冲动: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报道出来。不是惩罚谁,不是要伸张正义,只是告诉人们,我们对此不能容忍。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孩子。理由只有一个:我的儿子不要受到这样的伤害,所有的孩子有权利免于这种残暴。 但作为记者,动机可能由感情所驱使,其谨慎客观的求证却必须超越感情。在对此事的调查中,我接触了所有能得到的信源,包括死者亲属、球场保安、警方、球场旁边的住户,并拿到了最重要的证据:警方询问笔录。但有一个疑问仍然存在。 警方的结论是“溺水死亡”,但孩子家长发现疑点:如果是溺水死亡,孩子身上怎么会有大量的挫伤?其二,案发时是寒冬,北京所有的池塘,包括这家高尔夫球场里其他的池塘,都结了厚厚的冰,为什么独独发现孩子死在其中的水塘没有结冰? 因此,家长怀疑,两个孩子经受了暴力折磨之后,被人砸开冰面,投入池塘淹死,造成失足溺水死亡的假象。 尽管如此,警方的结论还是“排除他杀”。对湖面没结冰的疑点,解释五花八门。高尔夫球场先是说砸开冰面“给鱼透气”,后来,口径改变,说那湖“本来就不结冰”,至于原因嘛,说底下是流动的水,所以不结冰。最后,花样翻新,另有一种说法:那冰窟窿下面有个直径315毫米的出水管道口。 这,也许为蹊跷的“不结冰”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作为记者,要对事实负责,不可不查个明白。我想知道,孩子死亡的冰窟下,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管道口?高尔夫球场是不是又在撒谎?我打电话询问过当时打捞尸体的当地农民,他告诉我底下没有水管。但是,我能相信这样的二手信息吗?他当时忙于打捞尸体,真的注意到水底的状态吗?他的话,只能描述为:“他没有发现底下有水管。”却不能说明底下确实没有水管。 在此之前,我曾去过那个球场,但被保安赶了出来,因此,我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潜入球场,实地勘察。 4月15日夜里,我从北京市里赶到高尔夫球场,手持一根铁棍,与孩子的父亲和亲戚,翻过有尖刺的铁网,潜入球场。 拎着铁棍,穿过树林,眼前是一条壕沟,约有一人深。跳下去,再爬上来,便是球场核心。那是一处旷野,极易暴露,不远处有明亮的灯光,是保安亭,我们压低身子,沿着球场的低洼处小跑,避开视线。突然远处有明亮的灯光射来,吓得大家蹲在地上,不敢动弹。一会儿灯光挪开,才知道那是汽车的车灯。 翻过一个小坡,便见到那湖。我们迅速跑过去,蹲到黑乎乎的柳树底下,才出一口气。 这时大约是半夜,一个孩子的父亲刘丙亮和亲威老马陪我下水。我们找准方位,轻轻跳下水。尽管我预料到水会很凉,但没想到会凉得那样刺骨,那样难以忍受。我们到达那个冰窟的方位,水大约深1.6米,肩膀以上,下巴以下。我们用脚在水底下“摸”,没有异样。也就两三分钟,他们两个冷得受不了,跳到岸上,我也坚持不住了,慢慢用脚在下面趟着,走到岸边。但是,我又犹犹豫豫地想,如果搜索范围不够大,探索不仔细,一跳出高尔夫球场,想要后悔都来不及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又回去,这一次扩大周边范围,脚在水底一点点地蹭出去,直到心中一点怀疑也没有了,才跳上岸来。 现在我确信,在当初冰窟窿下的方圆几米内,水底一律是防渗漏混凝土,坚硬结实,连个细缝也没有,所谓有315毫米管道口的说法不实。有人又在撒谎。 坐在柳树底下,一边迅速穿衣服,一边为那两个可怜的孩子默哀。我见过他们生前的照片,那么活泼可爱,可是,四个月前,他们不明不白地死在此处,留下父母每天流着眼泪。 我回到家里,妻子早就睡了,那天是她的生日。这样冒险的采访,我没有告诉她,怕她担心。 两个星期后,我的报道《两个男孩的神秘死亡》刊登,文中我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孩子的死亡有疑点。我在报道的结尾,一反平时冷静客观的风格,加了一些感情色彩,算是对两个孩子的吊唁:“五一临近,北方已经初夏,B4湖边(孩子死亡地点)高尔夫球场的草已青青,有人在湖边挥杆游乐。两个8岁男孩却仍然静静躺在太平间的冰柜里。那里寒冷异常,正如同那个漆黑的寒夜。他们没有等到这个春天。” 读者反响强烈,对我们对“正义、良知”的追求给予赞赏,并肯定记者小心求证的精神。一位新浪网友在留言中甚至说:“这位记者像侦探。”他说得有道理,作为一个调查报道记者,他的目的跟侦探一样:追求真相。 然而,当记者得到赞美时,这篇影响巨大的报道,却对孩子的家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警方直到目前仍未改变最初结论。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我尽了最大努力,却没有任何意义。 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摆脱这种情绪。但我不再看孩子的照片,不再回忆这件事,不再与孩子的父母联系。我怕这种联系,会再次揭开我们的伤口。这次出于责任感的报道,自始至终带给我的是悲伤和愤怒,没有一丝一毫的快乐,哪怕是因报道得到读者的肯定时。 但是,孩子的父母感谢我,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我所代表的《南方周末》关注了他们,并想帮助他们。我的报道,他们也许不敢再看,但他们会珍藏起来,也许会在孩子的忌日,烧给孩子们,让孩子们知道,社会并非对他们的凋谢漠然相对。 我没有得到快乐,但是,有很多东西,比快乐更重要。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青年》杂志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