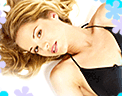那些鲜活着的摇滚灵魂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7日16:55 时代人物周报 | |||||||||
|
杨天赐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中国摇滚了20年,前浪基本都已经去沙滩晒日光浴了,现在自然都是后浪的天下,纵然良莠不齐,浪尖在日光的照耀下总还能泛出几点眩目的光芒,让人为之眼前一亮。
小河:最神经质的单纯 如果从小河出道的时间来算,他也能算是前浪了。1999年他就组建了“美好药店”乐队。那是一个有着紧张的分裂感,表达上超常荒诞与执拗的乐队。但“美好药店”与“小河”并不能划上等号。 2002年前后,小河开始在“河”酒吧演出,随后出版了一张名字长达16个字的专辑《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他忽而温情,忽而忧伤,忽而无意识地吟唱没有歌词的曲调,忽而像个孩子般咿咿啊啊,他就这样简单轻易地抓住了每一个听众的心。他给所有人打气:“别轻易倒下,你是一面旗帜。”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将这张专辑推入CD机,原有的情绪就会完全被小河营造的氛围所替换。听张玮玮的手风琴温柔地夹在郭龙的手鼓里,放弃了电吉他的小河抱着箱琴浑厚又清澈地唱出一个又一个虚幻的空间。这种奇特的感觉和小河的另一个乐队“美好药店”是不同的。“美好药店”仿佛一个小型话剧团,上演一出又一出嘻笑叫闹的试验音乐剧。在“美好药店”里,小河只是一个神经质的主唱,而在小河自己的演出里,他是真正的主角。依然是神经质的,民谣味更重些,又没有那么简单。你刚刚被手风琴的莫斯科怀旧音调打动准备陷入温暖的过去,小河去跳出来告诉你:“敌人是注定要死的,豆浆却永远是甜的,就像你注定是要离开的,世界却不会因为你走了而停止。”如果你将这当成是小河的呓语,那就继续沉陷在熟悉的曲调里吧,如果你开始思考小河的歌词,那就等着和他一起前一分钟大笑后一分钟严肃吧。音乐停止时,你发现自己被释放出来了,全身心的舒畅,来自小河的单纯和率性。 今年6月小河在上海演出,总是侧着身子坐半张椅子,郭龙戏说小河得了痔疮,小河笑嘻嘻一点头,台下观众就放下心笑嘻嘻看演出。而其实他得的是十分少见的“腰椎盘凹进”。坚持演出完之后病情就加重了,如今只能躺在床上站不起来,可他笑着说:“生活终于规律了,我终于有更多时间弹琴了。”看着他似笑非笑的眼睛,忽然想起王小波对幽默的解释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有意思———这就是幽默。 IZ:最干净的执着 “IZ”在哈萨克语里是“脚印”的意思。主唱马木尔于2002年落户北京,带着他的冬不拉和不太流利的汉语,不久以后,来自“舌头”乐队的朱小龙、吴俊德和“美好药店”的郭龙、“野孩子”的张玮玮与马木尔一起组建了IZ乐队。他们只用哈萨克语歌唱。 马木尔唱歌的时候近乎面无表情,只是执着于自己的声音和手里的琴。郭龙的手鼓使人安静,冬不拉的和弦酿出哈萨克的忧郁。他们坚持用以鲜为人知的乐器演奏,用“我们汉人”不明白的语言演唱,用执着于草根的心感动所有听者。 记得在上海,他们与定居瑞士的哈萨克族音乐人萨黛特同台演出。从开始时诸人安静盘腿打坐屏息倾听,到最后大家不分民族(当天有许多哈萨克族的姑娘小伙)不分国界翩翩起舞,直到所有人都把手拍红把脚跺痛,他们才深深向观众一鞠躬,悄悄离开舞台。 前不久,上海举行中韩文化交流活动。IZ作为仅有的三支表演乐队参加,给他们的时间仅仅是20分钟。郭龙给马木尔传递了一个眼神,说:“玩一下吧”。马木尔一点头,弹唱起哈萨克古老的乐曲《jar-jar》。这是哈萨克人在婚礼上的必唱曲目,欢乐情绪溢于言表。果然,那些正襟危坐的领事馆大人们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携起了身边人的手,在饭桌的间隙中跳起了舞,尽管没有一个人明白这究竟是在唱什么,但这传承了多年的欢乐又何须言词。IZ的魅力就在于马木尔们的执着,执着地寻找遥远的净土上最干净的空气、阳光和水。 接下来,IZ乐队的成员将有所调整。朱小龙、张玮玮、郭龙退出,同是哈萨克族的美兰别克加入,他擅长另一种哈萨克族的乐器,叫做“库布孜”。IZ看来是铁了心要在浮躁的乐坛内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了。 顶楼马戏团:最恶搞的严肃 这个乐队算得上整个中国摇滚圈里最最恶搞的了。他们不是朋克,但足以杀死中国所有正经的朋克乐队;他们不是摇滚,却比任何一个摇滚乐队都更明白什么是摇滚精神。 在上海这个被公认为是小资典范的城市里,竟然出现了“顶楼马戏团”这样有着近乎无赖作风的乐队,真是一件怪事。他们在非典时打着“某某居委会文艺小分队”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在台上“送三温暖”;演出进行到一半忽然换上迪斯科音乐自己跑下去跳舞;用经典的朋克腔大骂“朋克都是娘娘腔”,同时悠然伸出兰花指;一边歌颂着爱情一边像只猴子似的爬到音响上,跳到人堆里,趴在电线里;用佛教的法器一边演奏一边讨钱;在别的乐队深沉演出时用破烂的扩音喇叭在台下“唱和”…… 原来,他们可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还有人记得,2002年的迷笛音乐节上,他们曾经“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永远倔强,我们永远纯洁,没有人能消灭我们。”是的,没有人能消灭他们,不管是金茂大厦还是Giorgio Armani,都不能让他们与上海一起沦落到奢华的物质生活里去。反而让他们抛弃了正儿八经的呐喊,他们开始让破洞的背心和褪色的裤衩在城市的上空飘扬。他们指控“你不让我方便”,在你恶心的时候,他们诗意地感叹“东风无力百花残”,但当你想诗意,他们却在台上“露点”,然而在你跟着骂娘的时候,他们的音乐却又是那么优美,在你被他们烦透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在恶搞胡闹的深处,是严肃的指控、刻骨的荒谬。 2003年,“顶楼马戏团”的《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专辑发行,随即就因歌词淫秽低级而被取缔。确实,就歌词而言,没有点黄色段子打底者接受不了。在主唱陆晨与吉他手梅二的母校上海大学演出时,台下的女大学生羞得满脸通红直往台上扔粉笔头和矿泉水瓶。他们脏得像家里水槽下的蟑螂,让人不想正视,可它就是真实存在。上海根本不缺优雅的、光鲜的、时尚的、流行的、空洞的音乐,上海欠缺的是揭开这层浮华遮羞布的勇气。“顶楼马戏团”不管三七二十一,嬉闹着完成了这个任务。揭开之后的伤口让所有人不习惯,可这就是生活,活生生的,甚至是血淋淋的。谁都不是活在真空世界,现实里就有让你无法回避的不爽。顶楼马戏团不避讳这一切,他们悉心捕捉,然后还原成最小市民的样子,让你睁大眼睛看个清楚,不给你逃避的机会。 二手玫瑰:最妖娆的反讽 乍听到“二手玫瑰”的音乐时很容易联想到“子曰”乐队,乍看到“二手玫瑰”的形象很容易联想到日本视觉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以后,他们的现场倒有点王菲演唱会的意思:一半歌迷被奇特的装束吓跑了,另一半就更爱他们了。 其实,“二手玫瑰”谁也不像。“子曰”只是将调侃当作点缀,“二手玫瑰”是将调侃作为全部。视觉系的装束多半与音乐无法联系起来,孤零零地在台上唬人,“二手玫瑰”的浓妆是大俗即大雅的写照,就像他们的歌曲一样。 其实,主唱梁龙的化装癖是刚出道时参加音乐节被激发出来的——因为穿得太土气不被重视,他一生气索性抓起女孩用的唇膏胡乱涂了一把就上台了,心想着怎么土气怎么来,反倒是一下子被认可了,从此以后,他只要一化妆就特别兴奋。因此,一提起“二手玫瑰”,第一个反应就是“骚”。也正因这份“骚”,让“二手玫瑰”给人留下不同于其他乐队的印象。著名乐评人王小峰在他们还没有出名时这样拉人去看他们的演出:“有没有人跟我去看二人转?”。“二手玫瑰”能坚持他们的音乐,梁龙的女扮男装功不可没,不然,他们根本就不会被人记住。 都说“二手玫瑰”是东北二人转与西方摇滚乐的结合,但梁龙却说他并没有听过多少二人转,他的音乐里尽管有着很明显的民族根基,但未必就是二人转,只是像二人转一样俗气、热闹、欢天喜气又直来直去。看着他们红袄绿裤在台上挎着吉他大扭秧歌,不适应的观众将他们斥为伪摇滚,可他们竟然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有名的“乐评人”为他们撰文叫好。仔细听他们的歌词,除了搞笑,更多的是嘲讽,是一种以赖皮赖脸的方式表达犀利的幽默。他们甚至在歌里调侃自己:“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这样你才能继续的喜欢。看那艺术像个天生的哑巴,它必须想出别的办法说话。” 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见识了太多中规中矩的乐队,“二手玫瑰”的异军突起大获成功是意料中的事。崔健都曾经夸他们“没见过技术这么差的,也没见过这么有想法的。”这一群在台上吹着唢呐狂捣鼓的大老爷们已经引起了摇滚乐坛相当大的争议。有争议并不是件坏事,你看周杰伦、李宇春不都是有争议的人么,麦当娜出道那么多年,依然还是个有争议的妞,他们可都红得胜过了夕阳。 fm3:最简约的律动 这是支电子组合,这是一支被不喜欢的人称为“永远只有两个音”的电子环境音乐组合。fm3自己的解释是“fm3”是个概念,是个理论,是两台电脑和一条地毯。它由两个人操纵:老赵和张荐。 2002年,fm3正式成立,尽管他们并不是中国第一个做电子乐的,却是“中国最早的现场电脑音乐”。与丰江舟、孙大葳、王磊等人不同,老赵和张荐的音乐是缓慢的存在,而不是一般提起DJ就会想到的“群魔乱舞”。这两台电脑通常传来以下这些元素:难以觉察的低频振动、超低速的4/4拍重音、零散的民乐器采样和loop、逐渐推进的极简派变化、抽象的声音漂浮物……他们安静,但保持着律动。 这种在国际上已经十分流行的做法被称为极简主义音乐。要接受他们的音乐,最好先学会打坐或是培养出超人的耐力,要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去将他们当作背景音乐随便干点什么,因为听起来他们的音乐还真的就是无节制的不断重复“两个音”。但在适应了fm3的“慢”之后,听就成为一种享受。他们已经将肉体虚无化,只剩下精神世界。这是冥想时间,在事事讲求效率的21世纪,能坐下甚至躺下冥想的时间真不多。太多浮躁的喧哗使人们忘记了“慢”的存在,忘记了内心的声音。fm3做的正是让人重新省视内心,然后平和地去为人处世。 我听过的fm3最好的一次现场是在双廊,隔着洱海正对着大理古城。这不是一场演出,不过是张荐、老赵、颜峻去休假时的即兴玩耍。对着满天繁星,身边是波澜不惊的洱海,耳边是他们并不缺乏变化的“两个音”,那一个晚上,仿佛身在桃花源。 声音与玩具:最美妙的旅行 有时我们必须相信奇迹,就是信任听见的魔力。“声音与玩具”从成都地下乐队里冒出头来连续三年站在迷笛音乐节的舞台上,不喧哗,不吵闹,不砸琴,不搞怪,甚至不能POGO,和上述乐队比起来,他们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偏偏这时候,奇迹它就出现了。 显然,“声音与玩具”是受了迷幻摇滚的影响,再加上主唱区波偏爱的英雄主义观念,“声音与玩具”走向了艺术摇滚。无论是戴上耳机听他们2003年发行的《最美妙的旅行》还是与数万人一起站在演出场地注视他们在台上认真地拨弄琴弦,“声音与玩具”都以精湛的技术和游离状的歌词狂轰滥炸你内心最柔弱的角落。 “声音与玩具”习惯以一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作为每场演出的开场白。有人认为他们的音乐如同这句话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诚然,要想好好享受音乐,享受生活,不带任何一点杂念,真难。你有多久没有安静听一首歌了?有多久没有被一段不经意的旋律,一句不经意的歌词打动了?“很明显迷恋一个人的身体远比爱他的灵魂更加容易……可我只想要轻松自由的关心,这就是问题,我们的问题。”——“声音与玩具”在最受欢迎的单曲《爱玲》里低低地这样唱道,像是从睡梦里发出的声音,在耳边轻轻问你灵魂在哪里。“梦里不知身是客”的都市人被他们唤醒,这场华丽摇滚的背后是中国摇滚仅剩的希望与梦想。其实音乐也不是最重要的,它是源于你内心和身体的一种语言,它带给你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理解为美,你就去享受它吧。 那些鲜活的灵魂:滚石不生苔 2005年,不仅仅是摇滚乐坛处在一个低迷状态,整个流行乐坛都呈现出不景气的颓废劲儿。真正走红的是新鲜出炉的网络歌手。显然,摇滚歌坛要想走出低谷,必须求新求变,重新定位。能够像“声音与玩具”这样纯粹靠音乐取胜的乐队并不多。更多需要新一轮的冲击力,所以出现了“小河”、“二手玫瑰”、“顶楼马戏团”这样从视觉上和听觉上双管齐下的乐队。如今都已经进入到“读图时代”,密密麻麻的文字书籍已经为人们忘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让音乐穿一层漂亮的外衣。只有不断滚动向前的石头才能不给苔藓生长的机会,当然,石头还得是石头,实质变了的话,多华丽的外衣都会变成皇帝的新衣。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时代人物周报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