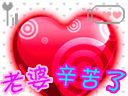东村人的幸福生活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17:03 《法律与生活》杂志 | |||||||||
|
本刊记者/吕娟 李云虹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东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会新认为,用这句话来形容东村人这些年生活的变迁,再恰当不 过。 2006年1月12日上午十点多,原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黄土东村41岁村民张富国(化名
自东村拆迁失地后,张富国一直没有工作,而这样悠闲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一年多。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东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会新认为,用这句话来形容东村人这些年生活的变迁,再恰当不 过。 阵痛 东村家园,原回龙观镇黄土东村,位于北京地铁十三号线回龙观站以南一公里处,东、北紧邻回龙观经济适用房文化 社区。在北京城市紧锣密鼓地向郊区扩充、市内房价急速飙升的进程中,这里的低价、交通便利无疑成为低收入北京市民以及 进京打拼的外地青年居住生活的首选。 在这样的环境中,东村家园用不一样的楼体颜色,封闭的社区院落,独立的物业管理含蓄而轻松地宣示着,这里是一 片与众不同的乐土。 62岁的东村村民刘志芩的乐,像盛秋的菊花一样,张扬地“开”在脸上。 40年前刘志芩从娘家北流村镇嫁到黄土东村时,这个村子仅几十户人家。贫穷,闭塞,鸡犬相闻的生活让从小对跳 舞唱歌说快板痴迷的她必须立即收敛起所有喜好,勤勤恳恳地过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当然包括生儿育女。 “汗珠子掉八瓣,见不到一分钱”,那时,所有黄土东村的壮劳力辛苦一天的价值是一毛七分八,对于村里的大部分 农民来说,尽管守着皇城根,但仅往返北京城参观的车票就高昂得让他们不敢奢望,刘志芩跟同村人一样,羡慕城市里的人, 却觉得遥不可及。 辛苦到2002年,刘志芩的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终于长大成人,并各自成家生子。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郊县逐渐 地变为市区,地铁轻轨沿着城市开发的脚步一路向北延伸,黄土东村迅速地湮没在一片片高高矮矮的楼房当中。尽管早些年村 里的田地已被国家征用,“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但城市扩张也同时卷来大批的外地打工者,在原有的宅基地上 尽可能加盖几间平房出租给外地人,几乎成了每户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刘志芩家的小四合院有五间大北房,挤了祖孙一家九口人,同时还要出租几间赚点租金维持生活,拮据可想而知。2 002年,当市政府拆迁的通知正式下到黄土东村时,刘志芩急得直掉眼泪。地没了,赖以生存的房子又要没了,换来个城市 居民户口,却连像城市人一样供养楼房的技能都没有,刘志芩想不出将来的生活还能恶劣到什么程度。找村委会干部吵、闹, 虽然对方拿出各种补偿政策反复解释让她吃定心丸,并一再强调两年后即可回迁,刘志芩仍旧觉得,一旦离开这块土地,未来 的生活就是未知数。 搬迁的日子到了,刘志芩和老伴决定回她娘家暂住,子女留在村子附近租房。破旧的家当一狠心扔了,又转眼心疼地 找了回来,跟随自己大半辈子的缝纫机才能卖5块钱,刘志芩没有舍得,老两口扛着缝纫机含着热泪离开黄土东村。那时,刘 志芩专门为搬迁编了一段快板,现在,词忘了,但那种“心中就像打翻五味瓶”的滋味,她仍记忆犹新。 刘志芩65岁的老伴祖辈生活在黄土东村,虽然他干了一辈子的铁路工人,但对农村这块土地的依恋却有增无减。比 起老伴,他更心疼的是,拆迁将使这个明朝时期就存在,有了600多年历史的小村庄从此彻底消失,若干年以后,随着东村 老人的一一离去,东村富涵的古老传说将永久地被林立的高楼尘封于地下,无人传承。 花儿样幸福 2004年11月15日,黄土东村的改建竣工。曾经像一块疮疤般嵌在周围崭新的楼群中的小村奇迹般消失了,破 旧的平房、随处搭建的违章建筑、零乱狭窄的小路被整齐气派的十栋七层住宅楼以及楼间规则点缀的草坪、室外健身区取代, 小区正门一块醒目的石碑上刻着红漆大字——东村家园。 刘志芩觉得,她前半辈子体验过的惊喜都没有回迁那一刻的多。各种形状、功用的健身设施,杵在健身区一角供居民 健身散步时享受的大屏幕液晶电视,各单元门前的残疾人车道、可视性密码单元门以及铺着瓷砖地面的楼道令她无法置信,这 里是她曾经居住过几十年的东村。 但更令她不敢置信的是即将属于自己的房屋。 按照补偿政策,刘志芩一家九口人,不论男女长幼,每人回迁补偿的面积是70平方米,11岁的长孙因为是独生子 额外补偿2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一家人将拥有9套共650平方米属于自己的房子。同时,东村当时拆迁的现金补偿额为 2700元~2800元/平方米,回购房的价格为1200元~1800元/平方米,一消减,一家人轻轻松松攥着了几十 万元的存款。 房子不愁了,连装修的钱也省了,作为村里的福利,每套房子由村里统一进行装修,瓷砖地面,白墙,整体橱柜,光 洁的卫浴设施,整个房子“搬张床进去就能住”。而更超出刘志芩想像范围的是,屋内统一配备可视对讲,主卧安装应急按钮 ,预防突发事件,阳台窗口装有红外线防盗警报,直接连接24小时监控的物业。 对于刘志芩来说,幸福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子飞进她的心里,压在心底几十年的生活重担转瞬间消失了。一家人经 过合计,9口人按户各住一套房,其余的五套出租。老两口从此的起居生活就像度假,有事就回自家住,没事三个孩子家轮番 转,生活的重心变得简单而轻松:一边含饴弄孙,一边琢磨怎样能让晚年的生活过得“快乐潇洒”。 刘志芩很自然地捡起了自己曾经的喜好。大队办公楼一层400多平方米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她的舞台,除了吃饭 睡觉,大部分时间她是在这里度过。清晨太极,上午秧歌,午睡后快板、合唱、评书,晚上再来趟交谊舞,稍有点事儿耽误了 ,伙伴们催促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刘志芩觉得自己似乎比年轻时还忙碌,但这种忙碌让她的眼笑得像弯月。 刘志芩的老伴张万达喜欢别人叫他“老青年”,因为他觉得自己两次死里逃生,如今却活得这样潇洒,就像获得了新 生,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1995年和2003年,张万达两次因突发脑溢血报了病危,但又奇迹般活了下来。更令家人感觉惊喜的是,自从 住进了新楼房,他因生病落下的行动不便竟慢慢地好了起来,现在,他自动参加了村里的老年乐队,并在刚刚过去的阳历新年 ,与老伴和其他村民共同组织了一台3小时的晚会,正如他说的,“发愁的事没了,身体自然就轻便了”。 65岁的张金林三十年前的梦想是,穿没有补丁的鞋,拥有一块城里人戴的手表,过年的时候可以不用四处借钱。 但现在的生活远远超出了他的梦想。住进了120平米的楼房,看上了40多寸的等离子电视,每月坐收几千元的房 租,买了车,当然也戴上了梦寐以求的名牌手表。 比起物质生活的变化,更让张金林感怀的是村民们精神需求的提高。体弱的老人舍得花钱雇保姆照顾,村民的家务活 都是请保洁工来干,家家户户虽然都有车了,但是却不像以前那样渴望进城了,“污染严重,交通紧张,住的都是鸽子笼,不 如这里的生活原生态”。 张金林认为自己接受新鲜事物享受生活的步伐甚至更快一些,他懂得了什么叫养生,花上万元购买按摩椅,健身器, 组建了村里的老年乐队,最近又筹划着买架钢琴,要不是儿女劝住,65岁高龄的他甚至想学会开车后自驾车外出旅游。 当然,张金林也感到了生活质量的翻天覆地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前邻里串门,推门就进屋,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但现 在一门就是十几户,又记单元又记房号,若干次跑错后,走家串户慢慢地减少了。以前,谁家儿女结婚送一对枕巾就算贵重, 但现在,每年的人情礼就得一两万,“虽然心疼,但都是邻里,必不可少”。 村干部难念的经 四年前,35岁的杨会新被村委会请回来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时,急得牙床整整肿了一个月。 杨会新早先在回龙观一个国有房地产公司工作。照村里老人的话说,这个他们看着长大的穷孩子是少有的几个走出东 村出息的小子。杨会新在公司的待遇不差,部门负责人,几千元的月薪,丰厚的年底分红,工作相对轻闲。他至今都觉得离开 公司是个遗憾,但他也知道,自己没法拒绝那些被自己叫做叔叔伯伯的老村干部的邀请。 杨会新不愿回村的理由很简单:他太清楚农村的工作方式,公司企业有完备的章程,谁违反规定,按章程处理,但在 低头抬头都是熟人、长辈的农村,想不计人情大刀阔斧地办事几乎不可能,“扣谁钱,他们全家上你家理论,不行就搬出最老 资格的长辈坐镇,直到你没法为止”。而更令他备感压力的是,2002年正是东村“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处理不好,“ 在村民的眼里就一辈子不得翻身了”。 回村后,杨会新才发现,新的村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不足40岁,他明白了前任党支部书记所说的“继往开来”的含意 。 杨会新说那时工作的底限是不让村民骂:村民不愿搬,就要反复地向没念过几年书的他们解释北京市拆迁补偿办法, 直到替他们把账算清楚为止;大部分村民念旧情,希望回迁,他们就要一遍遍地与开发商谈判,直到他们点头同意为止;一些 老人认为村东头的正午庙是黄土东村的精气所在,同时也是古迹,万万不能拆,他们就要想法最终让开发商妥协,专门留出那 片场地;年纪大的村民希望能通电梯,他们软磨硬泡让开发商突破经济适用房的楼层限制,硬是多要了一层;之后,从建房、 装修到分房,每一个程序都会组织村民代表到其他社区甚至广州等地参观取经,然后召开村民代表会进行讨论,包括地砖铺什 么颜色,炉具用什么款式,门窗用什么牌子,分房以什么为标准…… 东村分房采用的方式是抓阄,按照标准,杨会新一家三口可分得三套房,有了电梯,谁都希望自家的楼层能高点,但 杨会新接连抽的都是一二层,这令他挺懊恼:“事实就是,干部在这里,没有一点特权。” 农村没了,村委会也改牌成了居委会。除了医疗保险,村里的老人并不是很看重他们曾艳羡不已的居民户口,而年轻 人大多是为了谋得一份工作。根据拆迁协议,一部分年轻村民进入了小区的物业公司,每月拿着七八百元的工资,一部分选择 自己创业,而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过着像张富国一样悠闲的生活,“每月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房租收入足够他们衣食无忧,他们 觉得没必要再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杨会新解释说:“另外,他们也无力承受在城市打工所要面对的激烈竞争和外面对文化 素质、工作技能的要求。”但令杨会新颇为头疼的是,一些曾选择待业在家的年轻人最近又陆陆续续地开始闹着让村里给安排 工作,因为“年轻轻在家闲着的日子太难熬了”。 守着日渐升值的地段,东村人享受着他们迟来的幸福生活。谈起幸福生活得来的原因,有人说是政策好,有人称赞是 “年轻的领导班子开创了东村新的历史”,有人觉得是那座保留下来的正午庙护佑了东村的喜乐平安,但这样的反思大多只在 瞬间,更多的时候,他们在乐此不疲地挖掘生活中更多的幸福。 这样的挖掘过程形成了东村独特的现象:年轻人因幸福驻足,老人因幸福忙碌。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2月下半月刊) 相关专题:法律与生活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法律与生活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