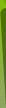作者:孙曜东 宋路霞
我和张伯驹过去是换贴把兄弟,我的大伯父与他的父亲张镇芳,也是换贴把兄弟。由于家庭和银行业务上的多重关系,我们的交往自然非同一般。如今伯驹已去世多年,我也已是垂垂九十老翁,自觉在有生之年,应该还社会舆论以一个真实的张伯驹才能心安。
天马行空的“末代王孙”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1898—1982)是袁世凯的表侄,与袁克定、袁克文等是表兄弟。他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安,1863—1934)是袁世凯的内弟,在清末,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与盐业打了几十年交道,以擅长理财出名,所以晚年创办的私家银行,就叫盐业银行。张镇芳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皇派”,还署理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当年李鸿章坐过的位子。1915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他也是积极分子之一,袁世凯事无巨细均与他商量,还是袁家的私人账房。袁世凯死后,他又积极参加张勋复辟,出任了几天内阁议政大臣……令他难过的是,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而张勋复辟只有11天就完蛋了。
如果按照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的说法以及袁克定的“皇太子”和袁克文的“皇二子”的“份儿”,那么张伯驹老兄,也理应在“末代王孙”之列了。问题是他这个“末代王孙”,实在与人们所想像的有天壤之别,他不仅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更主要的是,在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性”,不真正熟悉、了解他的人绝对百思不得其解,比如:他的父亲是如此地“保皇”,他的大表兄袁克定又是如此不择手段地要当“皇太子”,而他却坚决反对帝制,与袁克定在政治上形同水火,说他是“赖家伙”,而私交又非常之好,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也潦倒了,晚年全靠伯驹接济,直到1958年在张伯驹家里去世。他父亲擅长理财,创办了盐业银行,他作为长子子承父志,于30年代中期接办,然而却大权旁落,不会打理,只是有个总稽核的名义,不真正管事,但是在一些别人无法想像的地方,他却别出心裁,心思极细,令人刮目相看。比如有一年紫禁城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拿到盐业银行后张伯驹说留下来,随便给一些钱宫里就卖了。别人不理解,盐业银行要这些破地毯干什么?原来张伯驹眼尖,他看出地毯的织物中夹有金丝,于是就叫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买下来(那时余已因久病不登台,晚境不太宽裕),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结果仅金丝就卖了3万元,再卖地毯,共赚了6万银元,那时候乡下100元钱就能买2亩地。他喜欢京剧,为捧角、照应京剧界的人士不知花了多少钱,也喜欢登台表演,扯起喉咙唱几段。可是他天生就没有一副好嗓子,坐在台下听他唱戏,第三排以后的人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取笑他是“电影张”,因为电影原来是没有声音的。他的一些习惯行为也很“怪”,有时候高朋满座,大家谈笑风声,而他觉得话不投机了,就坐在一边摸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有时候到我家来找我,我若不在他也不着急,一个人能在客厅里等上3个小时,也不让佣人打电话找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干什么呢?仍旧是摸着下巴壳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漩涡似的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也都不深交,久而久之,我和我大哥(孙仰农)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一品香酒店抢潘妃
张伯驹早年曾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给作主的,一位开头关系还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钟情的、并与之相携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纹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
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那天晚上已经10点了,他一脸无奈,对我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他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现在在哪?”他说:“还在一品香。”我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她接出来!”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我这头一直警惕着臧卓的报复,可是事情也巧,我后来落水替汪伪做事,此臧卓也投了伪,成为苏北孙良城部的参谋长,仍是中将,我们见过面,大家心照不宣,一场惊险就这么过去了。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