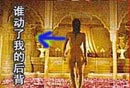国际政治采访之母法拉奇谢幕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9日15:26 南方人物周刊 | |||||||||
|
9月14日午夜,意大利著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在和乳腺癌抗争了14年之后,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安然离开人世。她的逝世结束了世界新闻史上的一个传奇,从此,曾经遭受她暴风骤雨般批判的伊斯兰世界,终于可以在下一个法拉奇诞生之前稍微松一口气了。 -特约撰稿 于英红
“国际政治采访之母”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弥漫着反抗情绪的家庭里,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则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勇敢坚毅的性格。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法拉奇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5年后,全国性杂志《欧洲人》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很有可能是个绩优股,便挖了晨报的墙角。《欧洲人》为法拉奇后来的辉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从此,她的访谈对象不再是小镇上的警官或医院中的工作人员,而是国际知名人士。在好莱坞,她采访了当红影星玛丽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辛·康纳利。 然而好莱坞明星和学界泰斗远远不能满足她的愿望。她的兴趣开始转移到政坛要人身上,从时任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尼尔德·衣阿蒂,到后来的基辛格、阿拉法特、约旦国王侯赛因、西哈努克、甘地夫人、布托、邓小平,这些重大采访为她赢得了“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美誉,她独特的采访风格在让被采访者心有余悸的同时,也让她成为了全世界新闻工作者竞相效仿的楷模。 为了亲历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她主动请缨深入战火纷飞的越南,几年的冒险生涯为她赢得了“战地玫瑰”的称号。1968年10月墨西哥大学生举行反政府游行示威,法拉奇为获得一手资料亲临现场,中了三弹,险些丧命。 她采访过的世界政要,很少有人没被她伤害过 “我的地盘我做主”是典型的法拉奇采访风格。几乎每一个遭遇了法拉奇采访的人,都会身不由己地被她引入一个由她控制的世界,只有被她牵着鼻子走。到最后,绝大部分被采访者都会为接受这次采访叫苦不迭,琢磨着能否把这段采访给掐了。 法拉奇善于偷换角色,把她自己而不是被采访者作为报道的主要角色。她会在报道中不失时机地插入自己或者自己的评论,使读者的视线发生偏移。在报道美国宇航局和宇航员的活动时,为了亲身体验在密封舱的感受,她进入阿波罗号太空船,这是一个展现美国空间技术成就的专题,但法拉奇看着这艘太空船,偏偏联想到二战期间那间曾经囚禁她父亲的昏暗囚室,从这个基点发散开来,她向读者阐释了人类面对孤独与恐惧时的不同态度。 更离谱的是当宇航员提到二战中他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战、并参加过对佛罗伦萨铁路的轰炸时,法拉奇接过话头讲述自己在一次空袭中经历的恐怖,并引发了对航天技术的道德评判。在这个时刻她忘记了这位宇航员当年轰炸的正是她的家庭所极力反对的纳粹暴政。 从法拉奇的《国际风云人物采访记》中,不难看出所有的采访都是围绕着作者预先设计的轨迹进行,不是展现受访者的心理,而是推销法拉奇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这时候法拉奇很像中国的皮影戏艺人,指挥着道具们在舞台上表演。更让这些政要感到恼火的是,法拉奇在采访他们时常常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有时干脆和被采访者争论起来,这个时候,采访已经变成一场辩论会了。 《时代》杂志的讣告说,“在法拉奇采访的世界政要中,很少有人没被她伤害过。” 1971年,在采访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时,法拉奇诱使布托说了一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智慧比不上她父亲尼赫鲁”,这句话无论对布托还是对巴基斯坦都是灾难性的,刚刚结束战争的印巴两国正在进行和谈,这句话彻底葬送了这一光明前景。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受害最深的一位政要。1972年,基辛格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如日中天,法拉奇却故意贬低他,说他完全被尼克松总统的影响盖住了。结果这位国际政治大师的自尊心被刺激得膨胀起来,狂言自己是一个“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的牛仔。他还承认越南战争“毫无意义”。这段言论严重影响了他与尼克松的关系,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与新闻媒体最具灾难性的对话”。 在采访当时外界风传为“南越最腐败的人”阮文绍时,法拉奇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这句话勾起了阮文绍的童年回忆,他动情地诉说了小时候家庭的艰难。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待阮文绍醒悟过来,已经晚了。他不得不开出一份家产清单,而从这份“谦虚”的清单,读者已经能嗅出阮文绍腐败的味道。 惟一从她的采访中受益的是邓小平,当时“四人帮”刚被打倒,法拉奇上来就问一些敏感话题,邓小平幽默机智的回答不仅避开了法拉奇的陷阱,还借此机会通过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向世界作了一次政治立场的正面宣传。 法拉奇的采访还有一个特点,她会把自己的主观性充分展现出来,丝毫不顾及被采访者的感受。1972年她采访阿拉法特时就出言不逊,两人当场吵了起来。后来她在文章中把这位巴解领导人大大地丑化了一番:“他小手小脚,长着一双肥腿;鼻子粗笨,臀部巨大,肚皮肿胀。”1975年采访英迪拉-甘地总理时,一张嘴就问对方为什么许多人觉得她“冷冰冰”、“不近人情”,把气氛搞得很不愉快;采访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时,她又讥讽后者的政治宣言“太小,无足轻重,简直可以放进我的粉扑里。”采访拳王阿里时,阿里当着她的面打了几个饱嗝,法拉奇就把录音机扔到他身上,扬长而去,因为她觉得阿里“无法忍受,像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傲慢”;对前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采访简直就像一出戏剧。法拉奇批评了伊朗政府的女性政策,当时她正穿着穆斯林妇女常穿的黑色长袍,霍梅尼说只有伊斯兰妇女才有资格穿它,法拉奇立刻将长袍扯下,霍梅尼拂袖而去。法拉奇离开后,霍梅尼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有关她的电视节目,为的是让国人记住这张脸,并威胁说,只要她再次出现在伊朗的机场,就马上逮捕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法拉奇的传记作家圣·阿里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法拉奇风格为她写了一本传记《女人与神话——奥里亚娜·法拉奇传》。法拉奇做新闻采写的一个要诀就是稿件在发表之前不让被采访者过目。但是轮到别人给她写传记时,她却要求在出版前审稿,然后把所有不利于自己光辉形象的部分删除。为防止圣·阿里科继续利用这些资料,她要求他当面烧掉那些被她删掉的部分。整个传记都是她一个人操纵提纲并筛选资料,这让阿里科非常不满,他未经法拉奇同意,偷偷把这部著作写成了讲述一个意大利女人如何掏空了心思构造自己神话的故事,让世人看到了真实的法拉奇。 向西方世界发出警告 “9·11”发生时,她坐在纽约的家中,通过电视看到世贸大楼的一座塔楼像一个火柴盒燃烧的情景,听着现场的人们不断恐惧地叫着“上帝,上帝”。当她看到一些人为了逃生从80或90层的高楼上往下跳的时候,她再也坐不住了。她拾起尘封将近10年的笔,在短短的时间里写出了《愤怒与自豪》。在这本书中,她对伊斯兰文明发起了系统的批判。 法拉奇向公众描述了自己采访霍梅尼时遭遇的尴尬与惊险。当她去罗马的伊朗大使馆申请采访霍梅尼的入境签证时,伊朗人看到了她涂得很鲜亮的红指甲,他们认为这是妓女的象征,勒令她赶紧擦掉。到了伊朗城市库姆,她被所有的旅馆拒绝,因为穆斯林妇女不在外面过夜,除非妓女。要采访霍梅尼她必须穿着长袍、戴上面纱,为了换掉牛仔裤,她费尽周折,开始她想在汽车里换,但是翻译警告她,“你疯了?要知道在库姆做这样的事,是要挨枪子的。”于是这位男翻译把她带到了以前的皇宫,一个看守人领着他俩到了一个房间,刚要开始换衣服,门突然被撞开了,一个人冲进来,口中呼喊着“罪孽、羞耻”,因为《古兰经》禁止一个男人和没有结婚的女人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发生了这种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杀头,二是结婚。于是一位负责任的毛拉拿来一份临时结婚协议让她和那位翻译签署。问题是这位翻译已经有妻子,而法拉奇根本不想跟一个陌生人结婚。 文明冲突论的首创者亨廷顿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预言了世界八大文明之间可能会发生的冲突,他没有料到几年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因此法拉奇对整个西方世界发出了警告:“美国倒了,欧洲也要倒,伊斯兰宣礼员会取代教堂钟声,穆斯林披风会取代迷你裙,骆驼奶会取代白兰地。” 她的祖国意大利的法庭对她提出起诉,控诉她涉嫌文化歧视,声称要收押她,但她丝毫不予理会,呆在她纽约的家中,享受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还向意大利发出警告: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国旗由体育场的小流氓们挥舞的国家里,如果遭遇“9·11”这样的灾难,它的状况要比美国这样一个众志成城的国家糟糕得多。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南方人物周刊专题 > 正文 |
不支持Flash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