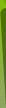不听不听我不听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2日14:05 时代人物周报 | ||||||||
|
-朱映晓 成龙先生也上《艺术人生》了,网站头条里有,我无聊就打开了,和我想象的出入不大:奋斗与传奇,去世的母亲,潸然泪下,等等…… 不过,还是有一点意外——他谈到邓丽君,“十分内疚和动容”,因为当时没珍惜
没错,邓小姐有过同台颁奖一见他就掉头走的举动——多可爱可疼的女人啊——那是多会儿的事,除此她还说啥了?我倒觉得成龙先生更应该说说吴绮莉林凤娇,偏偏只字不提,还说:“已经很多年没有爱情了”;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追求爱情——真是意味深长啊!他总说他读书少,是个粗人,淳朴的,粗人——依我看,细着哪! 然而,他“承认在感情上有时很迷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孝子和好父亲、好男人”。“现在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很多人,包括老婆。”如此,形象就圆满了,我简直要被打动了——如果不是记性太好,记得他如何理直气壮放言:“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犯的错——”还没完,几年后还说这是阴谋,怪吴小姐没有为了他而躲到柬埔寨生孩子,否则他会感动,为她伸大姆指——自私到如此明目张胆丧心病狂程度的人,没见过! 风流不是下流,多情不是过错,就怕根本是个奸人……不不不,我不是想说成龙先生的不是,我想说,《艺术人生》这个节目,这个做法儿——我看过无数期《艺术人生》,也不止一次流下感动的泪珠儿——在一种充满感情的气氛中亲口诉说,我从这里看到许多明星艺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即便有些平时不喜欢的,也会由此转变,接纳——然而,让我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如此亲口诉说一番,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树一个美好动人形象——所有缺陷都事出有因,所有过失甚至作恶都充满无奈?如果可以请胡兰成先生到场,他会说什么,“爱玲啊,我只记取与你那一段乱世的悲怅情缘……”那也一定十分感人吧。可是,你要听吗?!语言啊文字啊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只能“竟无语凝噎”了! 这是一个八卦的时代,人有八卦的本能,所以会有人甚至主动出来八自己,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其实是根本可以不听的——我对你连八卦的兴趣都没有! 怀念德里达 -恰贝贝 二十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发现是,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一个字并没有实在的意义附着在它本身,意义是经由字与字的语音和字形区分得以产生存在的。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进:这一区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a是a,是因为它不是b,不是c,不是d、e、f…… 事实上这一区别的过程是无限的,谁也不知道意义区别终止的界限,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移动的,弥散的,它是无数文字互为参照的“痕迹”(trace)。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说明这个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difference),意义必将向外扩散(differre),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deferment)的状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符号和所指物,指出了符号自行其事的性质,德里达则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所指都是能指无限区分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意义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语言是一张无边无际蔓延的网,没有任何纯粹的意义能够充分地存在于语言之内。德里达由此展开了他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看法:面对面的对话能够直接呈现“我”自身,而一旦诉诸文字,意义就可能开始被扭曲、异化,文字是对“活的语言”的不自然的模仿,声音则是对意义的直接呈现。在这种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观念:相信语言是透明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占有语言,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 但是,正如索绪尔所证明的: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文字如此,“说话”同样如此,德里达解构了这一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式:说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写作的模仿,正如写作被称作是对说话的模仿一样。不存在所谓本原意义上的语言底本,所有的“在场”(presence)都是依靠缺乏(absence)工作的,而任何试图创造这样一种“在场”:终极意义、本质、真实,作为人类的第一原则、标准、目的的努力——都可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逻各斯”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指谓言说、真理、理性,它相信有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超级能指(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它有各式的代理人——上帝、理念、自我、主体等等)作为事物的基础、本质,不会受到语言游戏的污染,它超然于语言游戏之外,成为其它词语、概念围绕的中心。但是,既然没有一个“词”能够逃脱出语言之网,这样一个最初或最终的词就必然是一个虚构,也许真正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哪些历史时段,哪些词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获得了神圣、不容置疑的权威?是什么使得某些概念、知识成为了一个时代主导的核心?这也就是晚近“反本质主义”思潮的滥觞:没有一个所谓的“天然”的本质高悬在意义的上端,人们总是可以证明,它同样是特定意义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意义体系倚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来运作,通过众多围绕先验能指的正项对负项的排斥与贬抑,这个先验能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虚无主义,这是对解构的庸俗化理解。德里达所致力的,乃在于对一些意义等级的质疑与批判,并且,他力图揭示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虽然,德里达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污染与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警觉的资态,“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有效性,无论是对欧洲文化还是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有效。即便记忆内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德里达的解构锋刃因此可以成为极具政治性的解放策略。 变态的权利 -叶倾城 纳博科夫在结婚之初,曾手呈夫人一份清单充当国书,说明他学不会也永远不想学的事物:开车、打字、说德语、和熟人打招呼,以及——合上伞。 我同情他。我相信他不是骄傲,而是真的情非得已,他见到方向盘或者熟人就手心出汗、心跳加速;设若有地毯,他立刻预想自己会绊一跤;花瓶在他经过后就神奇地掉下来,他一点儿也会不惊奇。而合上伞……多么高难度的事。 小时候,我时常用一把笨重的大黑伞,在大风雨里身不由己被它带着,像卡通片一样趔趄向前。我的小学校,建筑结构似祖屋,一进大门就是一个黑洞洞的门廊,穿过去才是操场。在室内撑伞是不允许的,雨天总有一堆中队长在门口乱哄哄站着,监督大家一进门就关伞,出去再打开。 我永远被挡在门外,一滴檐水冰冷地打在我眉睫上,又一滴。我拼命想把伞收拢,手被铁丝勒红了,同学黑潮一样从我身边涌过去,我一边与大黑伞作战一边被挤得乱七八糟。上课铃响了,教室还是咫尺天涯……那一刻绝望的心情,比什么都来得实在。 所有人一定都有笨拙或者荒唐的层面。有熟人至今不会用筷子;在外企工作十年的高层,说英语是他永远过不去的坎,我笑声像银铃般甜美清脆的女友,终于吐露是因为一遇陌生人就紧张,一紧张就乱笑。 然而谁敢学纳博科夫恃弱行凶?谁配?连续剧里“美貌愚笨的富家小姐”,且美且富缺一点儿慧,也是当然的第二女主角;“郭靖憨直善良”,普通人一憨直,叫做二百五。还有那些疏狂、阴暗、贪婪的欲求……洛丽塔的故事在书里在电影里,都勾魂摄魄,在人民群众间,那是“隔壁小区那个老不要脸的”,上2004年度十大鄙夷榜之首。不是红颜,说什么薄命;不是英才,就别提天妒;不是张爱玲,千万不要爱上不堪的男人。高分才有资格说低能,而我们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只能喑哑地活着,没有人会宽宥我们的缺失,包括我们自己。 我的朋友,在28岁才终于确定自己的性向,他却一言不发,转身追逐事业。他说:“每一个天才都是变态--但只有成功的天才,才有变态的权利。”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时代人物周报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