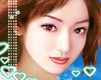在尊严和酸楚之间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9日12:18 新民周刊 | ||||||||||||
|
遥远的企盼和严峻的现实,我就是在写这样的“过程”中的故事。非常非常艰难。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说“忧患意 识”。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这是渗透在我们血液的“东西”。 撰稿/陆幸生(记者)
上周五,我来到上海市作家协会。我把《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放到桌上,对着宗福先说道,为这次采访, 我做了功课,再读这本书,里面有关于当年刊登《于无声处》演出消息先后情景的《一声惊雷撼人心》。宗福先笑了,他说, 我感谢文汇报,感谢马达老师,“从某种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没有文汇报的报道,《于无声处》也许就会湮没在历史的深处, 这样的湮没俯拾皆是,悄无声息;而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也许就‘工人到底’。” 就在上周一,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总工会、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文汇报联合举办“上海市宫剧 作家群作品研讨会”。上海市的这一文学创作群体,自1978年的话剧《于无声处》问世起,20多年来共有23部作品荣 获国家级大奖。于是,我与宗福先约定,作一次访谈。 曾经极致的辉煌 宗福先低调,但访谈须从“曾经极致的辉煌”说起。他慢慢道来。 宗福先:我动笔的缘起很简单,粉碎“四人帮”之后,周围的街谈巷议开始公开“议论”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悼 念周总理的事情。悼念周总理没错,更无罪。这是人民的声音。我写了这个戏,工人文化宫也就上演了。四百个人的小剧场, 最简陋的道具,要看的人一角钱一张票。观众爱看,剧场效果很好,但是开始的时候舆论没反响,没有文字报道,也没有评论 。 记者:文汇报跑文艺的记者周玉明来了,写了长篇通讯,刊发在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文汇报二版上,于是乎“风起于 靑萍之末”。 宗福先:这篇报道改变了《于无声处》的命运。后来知道,那时候胡乔木正在起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他看了 报纸,便到了上海。上海接机的领导询问这次来的安排,胡乔木回答:来看戏,看《于无声处》。 市委宣传部几位领导来到市宫看戏,觉得场子太小,马上决定,搬到现在展览馆的友谊会堂。舞台变大了,事情变大 了,但所有的道具、布景都变小了,原来的都不能用。而且,舞台调度也不对了,得跟着动。连着三天,把所有的“东西”都 改好,1978年10月28日晚上,胡乔木来到剧场看戏,市委领导陪同。 看完戏,胡乔木上台接见演职人员,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你生了什么病?”我楞了一下才 反应过来,是周玉明的通讯里说到我身体有病,坚持写作。也可见胡乔木确实是看到通讯而来。接下来,我说,剧本还要修改 ,胡乔木连说:写得不错。 记者: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就从这一天开始,将《于无声处》的剧本在报纸上连载三天。 宗福先:当时我是不敢出声音的。我是个工人业余作者,尽管《于无声处》已经演出了,但方方面面还有不少的要求 修改的意见。我当然愿意自己的本子能够“站起来”,我也愿意继续修改自己的剧本,更愿意听到社会和报纸的评价。但是, 北京那么高的领导干部,专程飞来看戏,上海的那么一张大报,要全文刊登我的“钢笔字”,那都是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也 不敢想。除了感谢,我只有紧张。 以后的事情,都在我“工人业余作者的经验”之外发生和运行。所以,我后来写过文章,胡乔木看戏之后,《于无声 处》就不是我个人的了,也不单单是上海一个业余剧组的了。 记者:《于无声处》就此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 宗福先:几天后,调我们上北京演出。马达老师在文章中讲到:“是胡耀邦同志指示文化部把《于无声处》剧组调到 首都演出的。” 那时候,中央正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会议第二天,就是1978年11月12日,陈云同志作了“解 决六个问题”的著名讲话。其中第五个问题关于解决天安门事件就说到,“现在外边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16日, 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广大人民群众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当天,人民日 报发表《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的长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那天,我们的戏在北京首演。 我们在北京一个多月,演出41场,观众达6万多人。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专场演出。 记者:中国十年浩劫的结束,人民愿望的强烈呼喊,,使得《于无声处》获得了轰动性质的成功。获得了成功的作者 又是怎么想的呢? 宗福先:开始我很忧虑。我担心《于无声处》成为样板戏,样板戏都没有好下场;我担心自己变成暴发户,暴发户都 没好下场。 记者:你的担心,都不是“艺术担心”,而都是“政治担心”。 宗福先:“文革”十年,结束才两年,天翻地覆,变化太大了,后面还将怎么变呢? 改革没有“即时判断” 我对宗福先说,《于无声处》的成功,是一座金字塔式的成功。最下边,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座,而往上,则 是中国所有各个阶层的赞同,直至顶端,是最高中央领导层的肯定。可以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在艺术表现上, 也已“定型”为经典。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文字写作,具体的剧本创作和演出,又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记者:经过长期和剧烈的斗争,政治生活一旦出现阶段性“转折”的时候,结论表达可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文 革”是错误的,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一个形容词解决问题。被打倒的干部复职,下乡的知青返城。简单明了。但是,在我们 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对于事件和人物的评判,开始变得困难和复杂起来。 比如,企业改制,境外资本的进入,落后工艺摒弃,传统工人下岗,等等,要是说到区别,天安门事件是公开的显性 事件,但是经济的初始运行、资本的谈判,大多隐形,其中曲折不可能公之于众。大到国家级别,小到个体户的第一桶金子, 都是如此。落后的剥离是必须的,但是“脏水和孩子”一同泼出去,其中很多是具有相当优良道德感的有了点年纪的老职工。 这样的时候,“全国一致叫好”、“上下全体同意”的戏,恐怕就没有了。 宗福先:这大概是我们这样的作者,现实创作中遇到的带有根本性质的一种变化。这是一种挑战,既让我们觉得兴奋 ,又让我们觉得艰难。 对于类似我这样作者的创作,有过“跟风”的说法。这是一种现实的误解,或是一种现实的误读。我是不同意的。这 类题材的作品创作,从来不是一种“美差”。 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农民和农村开始变得非常活跃的时候,工厂企业的 现状是凝固的。像我这样当了12年工人的作者,对于中国企业的内部情形,实在是太清楚了。用我们的台词来讲,就是这台 机器轴承牙齿锈牢了,咬死了,转不动了。还要指望这台机器出产品、出效益、交国家、养工人,不可能了。 1979年,我采访一位副部长,这位老革命说道:现在,我们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把四个现代化拼上去,否则的 话,人民群众就会认为,实现革命理想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这些人再被打倒,就不会有人来为我们平反了”。讲这样的话, 听这样的话,真正是忧心如焚。 记者:同样的忧心如焚,但是表现出来的直接利益,在一段时间内却是不一致的。 宗福先说到剧作《谁主沉浮——道拉斯先生到来之前》。这是他和贺国甫听到了沈阳一位劳动模范令人心酸的故事后 的创作。 宗福先:对于国家的爱戴,对于贫穷的无奈;对于如今必定要摈弃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拷问,对于这种经济体制下我 们因为熟悉而产生的观念依赖和现实依赖,对于外来资本的天然陌生,对于传统道德的天然抵触,等等,造成了今天中国现实 社会当中前所未有的各种“不同一”。 面对初期阶段的这些必然的“不同一”,我就只能写“不同一”。矛盾是绝对的,当然,写“不同一”,是为了在现 实和历史的长河中,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来呼唤科学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终和谐“同一”。 处于国家经济形态转型时期,对于关注这样的巨大转型特征的作者,写出来的作品,不可能是简单的“即时即刻判断 型”的。这与当年《于无声处》得到的“待遇”,立即获得毫无例外的感情呼应、全国一致的肯定,大不相同。而且,《于无 声处》说的是政治平反,不涉及经济,而我们现实当中遇见最大量的是经济现象,而在经济现象当中,最吸引老百姓眼球的, 是分配这个“根本课题”。 记者:从感情上说,从在职到下岗,生存马上就是严峻的。从时间上讲,从投入到产出,距离可能就是遥远的。而且 ,即使在决策和实施都完全正确的情况下,都是这样。何况,在现实生活中还一定会出现那么多的“故事”。 宗福先:遥远的企盼和严峻的现实,我就是在写这样的“过程”中的故事。非常非常艰难。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说 “忧患意识”。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这是渗透在我们血液的“东西”。 “对立面”的“好人坏人” 宗福先说,别人经常问的问题,初看起来非常简单,这个人是“好人坏人”,那个人是“坏人好人”?话剧创作,就 是活生生的人在剧场小舞台上演绎和重现人生大舞台上的故事。话剧要在有限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长度里面,使用富有冲击力 的语言,凸现社会矛盾,演绎人物行为,表达冲突以致斗争是展示剧情必要的形式。舞台剧当然有表演的“对立面”。写《于 无声处》,对立面是“四人帮”;现在,我们剧本中的“对立面”是谁?简单的“好坏”两字早已不足于说明如今人物和社会 现象的丰厚内涵。舞台剧里的对立面,大抵是社会某种现象、某个事件矛盾中互相的参照物,或是参照系。只是,那么复杂的 互为参照的社会人物,剧作家该怎么写?被作为参照物的“个体”的人怎么看,作为参照系的“群体”又怎么看? 记者:社会上,在政治层面的诉求,是可以高度一致的:只有改革,方有出路。邓小平就说过: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是,就在这样高度一致的诉求下,各层面具体阶段性的“内心标准”又是各不相同的。其实,从文艺写作的角度讲,这是个 非常基础的常识,“东西”好看就好看在这里。 宗福先:非常基础的常识,但是还有其他的常识在等着写作者。比如,关于资金的常识。比起以往,今天的写作者必 定会多碰到一个人,那就是投资者,或者叫投资方。我们写了个总经理,或者董事长,内心丰富,行为也有故事,但是,投资 者读了本子,觉得要改,还要这样那样地改,否则“不投资”。作为总经理,他有个被参照的感觉,对于参照系的一员,他也 许更想讲话了。人家理由很简单:总经理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还要投资? 记者:按照写作者和读者的一般关系,写东西的人可以不管这样的看法。一本书出版了,作者的人物创造就完成了。 但是,对于剧作家,“东西”要站起来,要活动起来。在写作者、演出方和投资方之间,产生了矛盾,让前者怎么办才好呢? 剧作家的人物不应该是“平面人物”。 宗福先:文学创作者笔下的人物,是独特的“这一个”;但观赏者是现实生活的人,他们要类比,他们要“鉴别”, 他们要联想。引动联想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只是今天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社会冲突也有相应激烈的时候。剧作家写下 的文本,触及社会现实,而引动的联想又非常尖锐。该如何来表现和评判这样的矛盾呢? 同理,写某个级别的干部,人家要问,这个级别的干部是这样的吗?某件事情的运转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要改 。 记者:用书面语来说,作家创作和行政管理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互动是有条件的,也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即使在彼此 都非常理解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此时当下”是否合适立即上演和表现的问题。 也许,普通劳动者、老百姓,最好写了。 宗福先:也不是。我们写了个劳动模范在万般无奈的生存困境之下,偶然“偷东西”。这是个真实故事,我们搬过来 用了。但是,不行,结果改成劳模的老婆偷东西。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遵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感情的需求,因为也想喊出自己真诚的声音,写了《于无声处》。 党和国家、各级组织和领导,给了我众多荣誉和待遇,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我心中一直非常感激。在当代中国经济 改革大潮当中,我和我们的团队,更想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来讴歌改革的无畏勇气,凸现现实的艰难迈进。我体会和认识到 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特点和写作要求,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现实生活的形象和脉搏。 宗福先还是再次说起《谁主沉浮——道拉斯先生道来之前》。这个本子的开头是这样的: 道拉斯先生要来了。他富可敌国,身世显赫。他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他魅力无边,人见人爱。他来干什么?投资东 山,发展经济。为什么要收购我们厂?破产的国企不要钱。那我们工人怎么办? 投资几亿美金,发展高新科技产品,这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啊! 零收购一毛不拔,不解决工人的安置就业问题,这叫什么利国利民? 而剧本结尾时候的话,是这样的: 你乱弹琴!国资委都批复了,你竟然煽动工人抵制破产!道拉斯先生明天就要到东山了,如果投资的事情搞砸了,谁 来负这个责任? 要是……国有资产流失、工人安置无望,道拉斯先生却不来了,或者来了以后出尔反尔,谁来负这个责任? 厂召开了第二次职代会,通过了资产重组的议案。道拉斯先生没有来。因为道拉斯先生认为东山的投资环境太恶劣了 ,来了也是浪费! 在谈话时,宗福先几次说到“心酸”这个词。那是他说到自己最熟悉的工人兄弟时候的常用词。话剧《谁主沉浮》定 稿于2005年5月。有时候要“心酸”的宗福先是这样结尾的: 现在开始走向小康,逐渐富起来......生活中许多真正值得追求、值得珍重、值得守护的东西,是金钱买不来 的,那是我们永远不能背过身去弃之不顾的操守:理想、信念、真诚、信任、善良、爱心......只有这些才能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温暖、带来感动、带来激情、带来尊严!-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