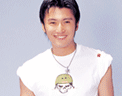国学场现形记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5日10:50 南方周末 | |
|
据说今年2005年是“文化保守年”,甚至可以说是“国学年”,由此也引来种种评论。一百年前清廷下诏废除科举的争议,一百年后,似乎又从昆明湖底翻了上来。敝人的立场,一贯认为民族文化是应该继承的;敝人甚至认为,缺乏外语学习条件的乡村地区,与其让学生不明不白地念英文,还不如从小读古文。古文现在也相当于半门外语了,而调查和研究都表明,学习外语是开发智力的好方式。 有人担心儿童读经会造成封建思想回潮,笔者以为是不必要的顾虑。像电视清宫戏里的“康乾盛世”那样,只读御定的经文,当然会造就皇权的奴才。但在同时学习各类科目的条件下,读点古文,只是多一份比较复杂些的语言材料而已。难道现在的学生念了几句《孟子》,就会真的“男女授受不亲”?本人才不信呢。小学生都在唱“老鼠爱大米”,进了中学不早恋就不错了。 记得小时候听老辈人讲《孟子》,说是古代祭祖宗时,女人煮好“太牢”(祭奠用的牛羊猪三牲)之后,放在碗里,碗再放在大方盘上。女人手托方盘,庄重地走到祭坛边;主祀的男性家长从方盘上端起祭品,置于祖宗灵位之前。祭品交接时,男女手指不接触,一派肃穆气氛。这就是“男女授受不亲”的由来,不知后来怎么会理解成男女在在必须回避。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能对典籍给出经得起多方参证的解说?有位熊姓教授,给学生讲《道德经》,居然解“太牢”为监狱。这个学校甚至抢在人大建立国学院之前,先设置了一个“道德经研究中心”,由熊教授任主任。 或许孔老夫子对此早有预见,他为后人指出了一条钻研典籍的后备途径:“礼失而求诸野”。不少所谓的“今译”,把《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译为“学了之后经常温习”。作者不知道“习”字本义是飞鸟频频拍动翅膀(繁体“習”尚可看出一点本义),这里是“习俗”之“习”,孔夫子还有学了经常用的意思。这一解释有根据吗?有根据的。第一个把《论语》译为英文的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将这句话译作“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即对学习要始终坚持并经常应用。幸好幸好,西方的汉学家先驱,早已把华夏文明的主要典籍译为外文。他们翻译的时候,还有饱学硕儒可咨询,至少保留了文本的传统含义。 至于本来就是外来的文化,如佛教,西方的和尚就更重要了。他们有现代语言学的工具。即使对某些只有汉译本流传下来的佛经,某词何义,从词根、用法比较、近亲语言中的相关单词等方向来追究,他们也有优势。何况梵语本来就属印欧语系。比如《金刚经》有个关键难点:菩萨必不可有的我、人、众生、寿者四相,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很多人读南怀瑾,南某说:“寿者相很严重,我们人都喜欢活得长,你几岁呀?五十八。嘿,我六十了,你比我小两岁。你几岁啊?八十二,你比我大几岁……这都是寿者相!”南怀瑾把印度人当中国人了,他应该去翻翻季羡林先生比较中印文化的书籍。印度人对生老病死的态度要豁达得多,佛祖没必要如此强调。英译本的意思就比较清楚:“众生相”指生生循环、为人为鸟为虫为X时始终都有的存在,类似于灵魂;“寿者相”则是好好活着的肉体。这两相是灵与肉的对照。 参考英译本还能学到汉语知识。《金刚经》里听讲的“须菩提”,英文为 Subhuti,由此可猜测“须”字古音读如“苏”。而某些南方方言确实念“胡须”为“胡苏”(“须菩提”之“须”,繁体不同于“胡鬚”之“鬚”,但从前可通假)。 西天的和尚也会念经。当今四海为家日,我们还真的需要知道别处的和尚是如何念经的。2002年布什访华,在清华演讲后(2月21日),清华校长说,“长期以来,在美国的许多书店里面,销售着一本中国的古典著作,就是《易经》。《易经》里面有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它就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周易》分经、传,清华校训属“易传”文字。本来,在中文语境里,校长那样讲,也还过得去,但顺着“美国书店”下来,就有问题。英文的《I Ching》 书籍,编排与中文线装本有所不同,它们往往只收入“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不录后人加的“传”。如果在场的赖斯博士真的信了清华校长的话,去美国书店查《I Ching》, 十有八九,既找不到“自强不息”也找不到“厚德载物”。 读者或许会说:熊教授,南某人,清华那种以工科为重的大学的校长,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专家,本来就没有多少国学根柢,他们只是强作解人罢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国内的专家们是在研究国学呢,还是在研究国学如何转化为生产力。最近在报上读到,某校哲学系为老板大款们开办了一个年费两万四千元的国学班。你能想像孔老夫子高涨束 ,专收富人吗?我们今天说夫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主要根据之一,不就是老人家的“有教无类”吗? 有位李姓中国哲学博士生为国学班唱赞歌,他相信老板们在学习中感受到了国学“在个体生命实践层面的智慧与知识”。敝同宗的第一个例子,是有老板说:学过一点哲学,“做事情不再浮躁,在生意场上也有了自己的节奏。”这是以庸俗实用的态度对待国学,把国学当作挣钱的助推器。第二个例子是有老板说:通过学习国学,“看问题更全面,自身会有所提升。”这是套话,任何一个有点资历的官员,在他写的学习小结和个人总结里,这类话都是一把一把的。李生的引语里,不要说体现了个体生命的有个性的话,就连带点国学色彩的话都没有啊。 其实,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本正经坐飞机去参加老板班,那是把它当作身份象征了,就像参加一年会费要多少万的 高尔夫俱乐部。或者,像某些大款嫖女人要找大学生一样,借此填补自己不存在的文化自信。熊姓教授和南怀瑾的望文生义固然可笑,但望文生义毕竟还不是操守有亏。而当北大的专家们都在口诵孔夫子却心系孔方兄时,我们想读点古文,想了解先哲前贤的洞见,是不是只有去找海外汉学家的解说了? 如此看来,要把国学读个半通,竟也非懂英文不可。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南方周末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