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别把八十年代炒酸了(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9日17:15 南都周刊 | |||||||||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 定价:4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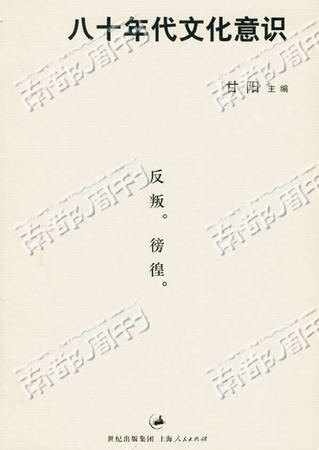 甘阳,学者,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记者 谢海涛 实习生 周长天 6月,甘阳来上海演讲,在上海学界是一件有影响的事情。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应似乎还在,华东师大举办研讨会的会议室里,地板上都坐满了人。研讨会的主题是“全球化文化生产条件下的中国文学研究”,开题演讲便是甘阳的“超越西方文化左派”。这个题目让特地请假前来的学者萧武,事后在博客里写道:这
五十几岁的人,三十七八岁的相貌,二十来岁的举止与活力,这就是甘阳。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围绕雷蒙·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内容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相关性,滔滔不绝,谈话有时东拉西扯,又夹杂着英语单词,似乎很散,但直抵根本的意识非常之强。 记者专访那一天,因为连续赶演讲的场子,甘阳嗓子沙哑。谈到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甘阳如话家常,话语中不无坚持,即强调文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话题转为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时,甘阳提起朋友之间的撕裂,也反省到自己的暴跳如雷,语气之平淡,似乎当初之痛已去,但又不无沧桑感。 采访结束时,记者索要邮箱地址,甘阳说自己总是记错,最后他给了出版社一个朋友的手机,让记者跟她联系。那一瞬,雄辩的甘阳霸气消隐,流露出一丝孩子气。 回忆八十年代隐含着对现在的反省 南都周刊:回忆八十年代,如今似乎是个热点。三联书店出版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引起广泛关注,最近世纪出版集团又再版了你在八十年代末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你觉得人们现在回忆八十年代的原因何在,具体价值何在? 甘阳:这个原因我说不上来,要问你们了。也许是大家都觉得现在有点越来越没有意思,倒是八十年代还有点意思吧。 说到有什么价值,我想回忆八十年代大概多少隐含着对九十年代和现在的某种反省。我个人觉得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是比较单调,市侩气太重,整个社会只有一个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经济改革,是否符合市场效益,用一个标准压掉了所有其他的价值取向。相对而言,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正处于摸索的阶段,思想反而比较活泼,价值取向也比较多元,不同取向之间也更多点宽容,没有现在这么狭隘,这么功利主义。我们今后的社会是否可能更多点文化趣味,更多点人文气,少点市侩气,少点低级趣味,我想这可能是回忆八十年代后面的一种期待。 南都周刊: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三大丛书之一,您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关注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引进,尤其重视德法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的译介,有学者认为, “文化:中国与世界”从人文主义的价值批判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的忧虑。请问,在当时急需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引入批判现代性的东西,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甘阳: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要去引进批判现代性的东西。最初非常单纯,就是想读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书,并不会先去问这书是促进现代化的还是反现代化的。就像陈丹青喜欢画画,就是喜欢画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他不会先问画画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就算不利于现代化,他也还是要画的,阿城喜欢读小说写小说,他也不会去想他这个写小说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我们读哲学的那时也一样,就是喜欢读你自己喜欢的书,这个喜欢最初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你喜欢的就是喜欢,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例如我们进北大外国哲学所,都必须上分析哲学的课,分析哲学的老师也都对我很好,但我就是不喜欢分析哲学,如果有人对我说分析哲学讲逻辑重科学因此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我一定认为他是神经病,哲学不是这么个读法的。 南都周刊:不同的人对于八十年代,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您在与查建英的访谈中,几次谈到你们八十年代的思路是一种“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请问这是你现在回顾的看法,还是八十年代已经这么看问题了? 甘阳: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这书是1989年首先由香港三联出版,这个“前言”说得比我与查建英的访谈更清楚。这里不妨引用1988年“前言”的原话:“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 南都周刊:可不可以谈一下,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我们中国人现在思考现代性和现代化有什么关系? 甘阳:很简单地讲,就是西方人对于现代的看法比我们深刻得多,他们并不认为现代性和现代化一切都好,而是认为现代社会有很多内在问题,而且是问题越来越多的社会,因此要对现代社会本身不断检讨。但我们中国人迄今为止对现代的看法非常肤浅,因为中国人往往倾向于简单地把现代看成就是绝对好的,如果有问题就是现代还不彻底,而不能认识现代社会本身就是有很多问题的社会。例如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高速进入现代社会,大规模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例如贫富急剧扩大的问题,文化日益庸俗化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典型问题。但我们往往不愿意面对这些现代社会的问题,总是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旧体制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这就非常妨碍我们去深化对现代性的认识,实际是错误地以为,一旦现代了,那就所有问题都不存在了。 又如许多人以为我们先搞经济,经济发达了自然就有文化了。根本没那个事!从前香港人说香港是经济发达的文化沙漠,新加坡更是经济发达的文化沙漠,我们今后会不会变成经济发达的文化大沙漠?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差得多,几乎普遍没文化,没有读过什么书,思想感情都贫乏得很,文字就更不用提了,都是无病呻吟惨不忍睹的小资调调。我很奇怪九十年代“小资”怎么成了正面词,“小资”就是小市民,小市民也就是市侩,怎么会大家都以当市侩为荣?但许多人却振振有词地为市侩辩护说,现代就是要庸俗,庸俗才现代,这都是极端肤浅的看法,就是这种肤浅看法的大面积流行使得我们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越来越俗不可耐,不以庸俗为耻,还以庸俗为荣。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现代性的角度去检讨的。 当年文化热并非仅仅反传统和全盘西化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问一下,为什么八十年代会出现“文化热”?当时的文化热似乎并不只是几个文化人的事,而成了整个社会的现象,为什么那时“文化”会成为关键词? 甘阳: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寻找文化的时代,不过实际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文革”刚结束到八十年代初,大家都痛感没有文化。我们知青这一代尤其如此,知青就是没有文化的人,所谓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不配叫知识分子,不过是认识几个字但没有什么文化的青年。我们那时都强烈感觉不但自己没有文化,整个中国都没有文化,这个感觉在阿城和陈丹青的访谈中都谈得特别明显。但正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大家开始“寻找”文化,不甘心这样没有文化下去。但每个人的找法不一样,例如阿城好像很快就找到了他自己的文化之根,中国道家和民俗文化等等,他在八十年代初好像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很罕见,大多数人这个寻找的过程比较漫长。当时大多数人是到西方文化去寻找,因为我们与西方长期隔绝,“文革”结束后开始可以看到西方的书了。所以第二阶段则有点像第二次“五四”,也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现代化,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问题,所以用西方文化作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这些人则更多从阅读海德格尔等日益发现西方本身的问题,因此我们虽然也有强烈反传统的一面,但更多地则集中在力图理解西方现代性本身的问题上。从我个人来说,1985-1986年是提出“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就是反传统”的阶段,但1987-1988年已经不同,我1987年发表的“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着重强调西方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而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已经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明确为“文化保守主义”辩护。 因此八十年代短短几年的“文化热”实际已经一波三折,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八十年代文化热实际并不像许多人通常以为的那样就是一面倒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一是“文化热”中许多人已经转向中国文化传统,作家中的“寻根派”和学界的亲儒家派已经成型,虽然当时不是主流话语;二是阅读西方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有些人眼里看到的西方现代全是好的,都是对的,所以比较简单地用这样的“西方”来全面批判“中国”,但另一种则如我们看到的是海德格尔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这样问题就复杂得多,使我们开始进入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问题。不过这种现代性批判在八十年代是一种“文化立场的批判”,所以我称为“八十年代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 南都周刊:李陀在探讨八十年代文化热时说,当时没有引进后殖民理论和女权主义造成了一个脱节?您认为有道理吗? 甘阳:我不知道李陀是怎么说的,但如果认为八十年代没有引进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之类就是什么脱节,那就是不知所谓,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我认为八十年代的长处恰恰在于,我们当时并不是简单地跟美国走,不是西方什么东西最popular,我们就引进什么。不是美国批判海德格尔,我们也要跟着批判,我们是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不像今天处处要搞国际接轨,我们那时读西方翻译西方著作,和我们想的问题有关系。八十年代中后期海德格尔在中国被翻译出版被阅读的时候,正是美国人开始在政治上批判海德格尔的时候,但我们对美国式批评海德格尔没有兴趣,即使今天我仍然认为不值得重视,那些美国化政治批评海德格尔的都是典型的三流东西,以政治批判来取消海德格尔问题的深刻性,在思想上是拙劣的。 八十年代没有引进后殖民理论,更是完全正确,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没有必要引进。90年代初刘禾在美国问我,后殖民理论对中国是否有意义,我当时就直截了当说没有意义,只有对印度非洲这种西方长期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有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文化,又待在西方的大学里,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现在仍然要强调,我们今天对后殖民这套东西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批判看法,不要随便跟着走,号称搞后殖民那套的大多数是西方校园里的一点小闹闹,和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毫无关系,并不值得我们重视。 作为一个真问题的后殖民问题,其比较深刻的问题原型实际是欧洲19世纪的“犹太人问题”。所谓“犹太人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恰恰是法国大革命从政治上解放了犹太人,第一次给了犹太人公民权后出来的问题,因为这种政治解放的代价是犹太人必须放弃他的族群宗教身份,以“个人”的身份成为现代欧洲国家的公民,也就是要犹太人必须“融入”基督徒主流社会,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第一代现代犹太人接受了这种“文化同化”的命运,热衷于被纳入,被同化,但是卡夫卡著名的“给父亲的信”代表了19世纪后期新一代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反抗“文化同化”的强烈文化自觉,卡夫卡提出的“写作的四个不可能”是对失去自己文化传统和自己母语的最沉痛表达,因为卡夫卡这一代犹太人已经不熟悉犹太传统,不能用犹太语言写作,只能用德语写作,卡夫卡因此提出德国犹太人面临的四个“写作的不可能”:不写作的不可能,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写的与德国人不同的不可能,所有这些加起来最后变成“写作本身的不可能”。卡夫卡以后的整整一两代犹太思想家从本雅明到莱维那斯和德里达,都套在这个写作的可能不可能问题上。但今天美国校园流行的后殖民论述,却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化苦恼,更没有六十年代非洲知识分子如法农的真正痛苦,而是更多变成西方校园里无病呻吟的小资调调,这些东西不值得我们重视。 文化不能按照市场标准来衡量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对资本主义的诗意的文化批判,它的命运历程是怎样的? 甘阳:九十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以后,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很快全面商品化市场化,一个从文化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工具化的立场、视野和问题意识,在中国基本上消失了。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是最后一次试图提出问题,但一下子就被打掉了,大家说,扯人文精神啊,这是什么年头了嘛?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失语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很猛然地,全面地对社会冲击,它用一些简单化的标准把很多东西都取消掉了,文化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为什么人文精神讨论,会有如此一个了结?原因很简单,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来以前,大多数人都预想如果全面市场经济了,那就什么都全面性地好,文化上应该有更多的人读文学啊,应该有更多的人向往高尚的生活,人们不认为市场会带来庸俗化。所以九十年代很长时间不能对市场有任何批评,批评市场就被看成是反改革反现代,这自然就造成了失语。 南都周刊:说到文化失语问题,想起您在7月来上海的演讲中,以“超越西方文化左派”为题,指出晚近三十年来西方文化左派把“文化”看做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大多数人的排斥,所以他们不断地在拆文化这个堡垒,但同时忽视了文化对于市场的批判性,拆了以往意义上的文化,结果恰恰使市场全面占领文化领域。那么具体到中国来说,要解决转型期形成的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现象,文化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甘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媒体上暂时不容易说清楚。这次我是在一个暑期研讨班上谈这个问题,学员相对有专业准备,大家对西学的了解也比较多,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称之为“文化的伪平民主义”,就是认为只要老百姓喜欢的就是好东西。这是错误的。老百姓喜欢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媒体竞相出奇招,来吸引百姓,使得现在的大众文化越来越低俗。比如在香港,最近就出现了最有名两个主持人想出新花样,让香港市民投票选举“你最想非礼的女演员”,自然大家蜂拥投票,最后连政府也不能不出面干预,但也只是罚款,稍微一动,香港的粉丝全都跳起来,他们认为,这个有什么不好?但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同意这种东西没有什么不好?当然非常不好,非常恶心,问题是今天几乎缺乏可以批判这种庸俗的语言和氛围。 其实,文化原本提出了更高的生活方式,超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商品拜物教,从而开展包括个人生活方式的精神上的可能性。但晚近二三十年来,这种要求在西方基本上放掉了,所有的对高级文化的批判和无批判地吹捧大众文化,实际都只是进一步助长了市场主宰文化领域,导致文化领域的日益低下庸俗,因为没有更高的标准,没有正面的价值追求。 (以上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相关专题:南都周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南都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