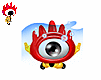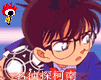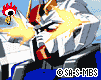| 新民周刊:从华尔街到艾滋村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9日01:44 新民周刊 | |||||||||
 河南艾滋病村,一个女孩这样完成作业 8月15日,上午9:00的阜阳机场空空荡荡。从上海到阜阳的这个航班只有11名乘客。行李车开过来,工作人员直接将一个巨大的拉杆箱交到杜聪手里而没有开动履带,因为似乎没有必要——杜聪是大厅里唯一等行李的人。 两个拉杆箱跟着一个白净、沉默的人向前走。杜聪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没打表,说:“你给30元吧。”杜聪缓慢地温和地说:“你打一下吧,要不,麻烦你拉我们回机场。
杜聪说:“在内地要做成一件事很难,我必须正视、谨慎,同时具备很强的协商能力和谈判能力。” 哈佛毕业生 今年37岁的杜聪出生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全家移民去了美国,他在旧金山读完高中。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现了首例艾滋病,然后进入高发期。纽约和旧金山是高发地,先是一群同性恋者莫名其妙地死亡,然后全城人心惶惶。杜聪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死于艾滋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前,几乎所有的艾滋病人都得死去,这是无奈的事实。 杜聪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1991年在哈佛东亚研究院拿到硕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银行派驻香港,位居联席董事(相当于副总裁)。2年半后,他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杜聪在美国居住的13年,正是这个国家经历艾滋病从初现到高发的年月。 因为银行的融资项目常常涉及到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大型工程,杜聪常有机会来到内地偏远的地方。贵州,他去过8次,还有山东、湖南、湖北等地。在那里,杜聪听说了艾滋病可能在蔓延。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对艾滋病还很无知,中国是否会重复美国的灾难?这让杜聪非常担心。 其实,杜聪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当他还是个香港中学生的时候,每年暑假,都会背上背囊行走中国内地。他去过新疆、走过丝绸之路,像任何一个地方一样,这片土地的光荣与耻辱、文明与野蛮,都铭记在他的记忆里。 当时感触最深的是:长期物质匮乏造成的恐慌清晰地写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譬如坐火车或长途汽车,200个人,只有50个位子,于是大家拖着沉重的行李争先恐后。必须爬窗,必须踩着别人的肩膀过去,因为错过这一班,就没有车了。而当时香港或美国的情形是,人们不会担心,因为错过这一班,还有下一班,社会有能力提供满足需求的交通。这是充裕和匮乏的反差。 他曾在贵阳滞留了2天,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在通宵排队购票时,他看到插队的人,看到“走后门”买到票的人。他认识到,在内地,人际关系是微妙而极其重要的。 1998年,杜聪与几个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诸行动”。刚开始是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的发放工作。顺便交代,杜聪是个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在加拿大和美国,艾滋病高发时,超过半数的感染者是同性恋者;在中国,根据张北川教授的调查,在29个省、市、自治区发现有男性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感染率为5.5%。 性取向,很自然地让杜聪更关注艾滋病。当他面对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评审团,被问及性取向时,是这样回答的:“性取向不应该作为考虑因素,得不得奖要看贡献。” 人生转折点 2002年初与高耀洁的会面是杜聪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河南的情况已经通过一些渠道传递出去,包括杜聪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相信,真有那么严重吗? 那次会面在当时还是有些惊险意味的:高耀洁被警告不要乱说话;当杜聪抵达时,老太太蹒跚着“解放脚”将他带出家门,在另一处谈了好久,包括她失败的经验。杜聪的印象是,高耀洁对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思路清晰,有说服力。杜聪得到一些有价值的、避免走弯路的意见,譬如帮助艾滋病家庭的助学款交给大人不如交给学校,以免被挪作他用。 河南艾滋病村庄好似一个疮疤,让所有看到过的人心绪难平。杜聪第一次走进艾滋村,一天之内一口气跑了几个村庄。在那里,每10个成人中约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一样的缺乏药物,一样的死亡。还有面临绝望、束手无策时的自杀。 “你知道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滋味吗?那就是。”杜聪对我说。 那天下午4点,杜聪和陪他进村的当地人已无法继续探访,5个汉子对着村旁的一块玉米地,哭了。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失眠了。他倚在窗旁,凝望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那是compassion,中文应该译为悲悯。 杜聪决定,他要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一些事情。他辞职了。他当时的年薪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金领中的顶尖级(杜聪不希望透露具体数字)。但,这是他的选择。 从此,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清早,香港,和煦的阳光洒进杜聪家的客厅,他站在家中供奉的白瓷观音像前,点上一炷沉香,合十祈求旅途顺利,然后,拖着他的拉杆箱启程,开始又一次的救助艾滋孤儿之旅。 一次,当他刚刚走进一户人家,母亲便哭着过来,苦苦哀求“救救我的儿子吧”。孩子的爸爸早已因艾滋病走了,地上,有个也患艾滋病的8岁男孩,只剩下一副骨架,他用大得吓人的眼睛盯着杜聪,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杜聪别过头,指着一旁的女孩,对那母亲说:“也许,我没有能力为你的儿子做什么,但我要确保你的女儿能有读书的机会。” 杜聪一定是一个内心敏感而纤细的人。他给我看一张照片:一个很瘦小的男孩,站在一辆板车前面,车上是他骨瘦如柴的父亲,两个人都低着头。那个黄昏,杜聪远远看到泥路上走来这一对父子,儿子用板车推着父亲,只是想让因为艾滋病整天卧床的父亲透透新鲜空气。夕阳打在这对父子身上,笼出一层光晕。及至走近,杜聪按下了快门。 还有一个小男孩,功课挺好,人很文静。父亲得了病,母亲改嫁走了。他站在村口,望着母亲的背景,不出声。那一刻,杜聪突然有了一种恍惚。杜聪告诉我,在他差不多大的年纪,母亲因为别的原因也是这样带着妹妹离开了家,父母从此分开了。在他探访的近百户被艾滋病摧毁的家庭里,没有母亲的孩子往往比没有父亲的状况更糟些。 然而在这些孩子身上,没有抱怨,只有默默承受。他们低着头,用细细的腿脚站立于这个世界,面对这份与生俱来的灾难。他们从没有想过,如果出生在另一个家庭,他们可以有怎样的欢笑。他们就那样站着,低着头,承受着。那些迎风摇曳的玉米秆和窗户上的破塑料纸,教会他们坚忍。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艺术创作有治疗心灵创伤的功效,称为“Art Therapy”。从前年开始,杜聪让一些接受助学的孤儿用画画和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愿望。一个学前班的小女孩画了这样一幅图画——有一天她对病重的妈妈说:“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卖了我,就有钱买药来治你的病了。”她紧接着画了另外一幅——她继续说:“妈妈,不要紧的,等我长大以后我会回来找你的。” 杜聪说,从小孩子们的作品中,还能看到一线希望。有的孩子希望当教师,有的想当记者,还有一个希望成为UFO(不明飞行物)专家。当然,最多的愿望是将来当医生,研究“艾滋病的解药”。没有一个孩子想当歌星或模特儿,杜聪说,也许这些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遥远了。2003年3月,这些图画在香港大会堂展出,展览名为“垂死村落中的梦想”。 救助的哲学 杜聪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训练,让他从一开始就是理性而专业的,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 在进入河南之前,杜聪在另一个机构当义工,在四川、云南已经积累了一些助学经验,加上高耀洁的指点,杜聪想,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标准、一套模式、一个系统,那么一个村子里所有符合条件的孩子都能得到救助,而他们的家人,不需要为得到助学款而扮穷,“他们应该有尊严地活下去”。这个系统从河南的一个村子开始建立。在统一的标准下,全村127个孩子得到了一个学期的学费,到今年,已是第五个学期。这套系统逐渐推广至其他村,至今已有超过1200名孩子在“智行”的支持下继续学业。如果考上高中或大学,“智行”继续负担学费;考不上的,初中毕业后,杜聪想方设法带他们寻找职业培训的机会,譬如最近,他刚带了一批孩子南下广东。他说,如果有好的酒店愿意给他们一些实习机会,以后出去找工作会方便许多。 杜聪曾经带一个河南艾滋村的孤儿到山东。孩子问:“叔叔,为什么我的家乡和这里相差那么大?”“如果连受教育的机会都不给他们,这些孩子永远只能局限在乡间,别无选择。或者,他们长大后可以到大城市打工,但很有可能会学坏。”杜聪说,尽管在许多人眼里,他是拿着一杯水在扑一场大火,但对于每一个被救助的孩子,命运的改变是100%的——起码完成初中课程,具备起码的竞争力,有机会自食其力,摆脱困境。 在阜阳,杜聪被一群省市妇联的主任包围。她们除了用安徽话表达对他的钦佩之情外,也提问:“杜聪,你为什么不再做几年金融,积累更多的资本,再来帮助这些孩子不是更好吗?” “我等不及了。就像在一个人最饿的时候,你给他一碗粥,肯定比在他饱的时候给他一碗肉来得强。”当一些中外媒体将艾滋病的报道重点放在卖血过程和政治层面的质疑,譬如向政府追究责任、要求官员下台的时候,杜聪和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孤儿问题,如果那时不开始,将错过关键时期,这些孩子也许已经交给社会了。 在他看来,试图引起世人关注的传媒的广泛报道原本是好事,但有意无意间也为当地造成不少压力和负面影响,导致当地生产的农作物无法出售(譬如艾滋病西瓜的故事),甚至助长世人对艾滋病人的仇恨与歧视。 救助的哲学远不止于此。如何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关系到善意还是敌意,能不能进村直接帮助孩子的问题。杜聪以他的温和、低调、理解和诚意打动了地方官员。2002年年中,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联系,他被邀请到河南艾滋村了解情况。这在“外来者”中是罕见的。杜聪告诉我,这些年,他遇到过很尽责的官员,能体会他们的压力和无奈。面对一场大火,是先追究放火的人还是先救火?杜聪选择后者。 在每一个艾滋村,都有一个关键人物,杜聪称他们为“握着进村钥匙的人”。这是一些相对富裕的,或在村中具有某种威望的平民百姓。当艾滋病降临的时候,这些人也许有能力去北京看病,他们最先面对媒体记者,面对各种医疗界人士,他们掌握着一些资源。杜聪必须通过他们才能真正了解村子里哪些人需要帮助,尽管这些握着钥匙的人常常也会试图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杜聪以他的平和与他们相处得很好,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公平的可能。 “我要低调地、持久地去帮助那些孩子。”有时候,杜聪不得不保持沉默,他有这个心理准备:“要做成一件事,是不容易的。”但那些丑陋的东西,确乎影响到他,就像亲历了一场车祸,或者目睹了一宗谋杀案,他看到了,却不能说。那些记忆的烙印,常常在深夜里折磨他,让他失眠和做恶梦(他以前不)。杜聪说,两年多来,他好像心理上也有了阴影,他只能刻意地不去想它们,然后,继续每两个月去一次艾滋村。每年70%-80%的时间,他都拖着巨大的拉杆箱,在路上。 每一次回访,他都会看到一些新坟。每看到他所帮助的孩子境况变得更糟,难免真让人灰心。这不是一场地震或洪水,过去就过去了,悲剧在不断地发生。 不是没有想到过放弃。然而,每当杜聪站立于村中坟头前,想起一两个月前曾经紧紧抓住他的那些干枯的、骨架般的手,看看身边的孩子,忽然间就有了一种被托孤的凝重。这些孩子、他们的点滴成长和偶尔一露的笑容,是他在路上的动力。 杜聪身上有一种包容性,似乎与他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有关。在他身上,没有非此即彼的偏执,也没有面对利益有你没我的火气。还有一点,做善事不是为了行善者的自我满足,而是真正能帮到对方什么。这一切,决定了杜聪做事的效率。(文中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杜聪提供)- 撰稿/李宗陶(记者)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