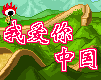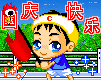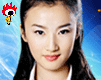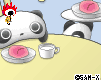2003年09月29日:拆迁黑洞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2日21:21 中国《新闻周刊》 |
|
2003年9月19日晚11时许,北京市长椿街的王先生家里突然闯进了几个蒙面人,在手电筒的强光照射下,一家三口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就被摁倒在地,被布蒙上眼睛堵上嘴,然后五花大绑抬出门外。推土机一阵轰鸣,王家的房子顷刻间被夷为平地。这是又一起与拆迁有关的暴力事件。截至今年8月31日,国家信访局已收到关于拆迁的上访信11641件。 在全国,由拆迁引发的冲突不断出现。 中国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也最急剧的城市改造运动,但一座座家园被除旧迎新的同时,却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拆迁是发生在城市土地上的一场驱赶与占领的游戏,是巨额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而且其中发生的事情未必公平 无法守卫的家园 在危改和拆迁过程中,私房的土地使用权始终没有得到明确承认和补偿,这是造成房产拆迁补偿价格与市场价格产生巨大差异,同时引发拆迁纠纷不断的根本原因 而在这个利益重新划分的过程中,行政权利和商业利益的结合,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拆迁户更容易受到伤害 本刊记者/唐建光 滨江道,天津最著名的商业街,长约1000米。 王春来的家,就在这条商业街的中间位置,离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商厦劝业场不到200米。 8月26日,他坐在家里。窗外正飘着秋雨,雨中传来一阵阵挖掘机的轰鸣声,空气中弥散着一股臭味。 从四楼的窗口望去,满眼是断壁残垣和堆积如小山的垃圾,一座灰色的6层楼房置身其中,如同一个随时将被淹没的孤岛。 三个月里,他一直在这个渐渐形成的垃圾堆中坚守,点着蜡烛熬夜,向旁边的工地上讨水喝,工作之余东奔西走,投诉求告。然而,邻居们的房屋还是一家家被强制拆迁了,王春来和其他最后的留守者们,看起来撑不过一周。 水、电、气、电话、有线电视都被掐断了,连窨井盖和下水管也被拆走。小区的大门、楼道门都不见了,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2号楼的几家、4号楼的王春来家和5楼的一家人还门窗完好,其他都只剩下黑黑的窗洞。 最大规模最急剧的城市改造 这天,天津市和平区法院、拆迁办、公安人员及搬家公司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滨西大楼小区的这个小院——又有三户将被强行搬家。 整个小区的最后11户人家凑到了一起,他们刚刚听说发生在8月22日的南京拆迁户翁彪自焚的事件,不禁发出言辞激烈的感叹。 王春来是今年以来天津市被拆迁的69192户人家中的一家。 在这个具有600年历史的直辖市,大量破旧平房、职工宿舍,以及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建造的多层单元式楼房,被列为改造目标。 仅王春来所在的和平区,上半年就有100万平方米的旧房被拆除,下半年还有超过80万平米的房子被列入了拆迁范围。 在全国,这个数据被放得更大。各大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仅2002年1月至7月,就有1675万平方米旧房被拆除。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最急剧的城市改造,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数以千万计的居民告别旧房搬入新居。 但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城市改造运动中,其中一些人认为自己成了受害者。 国家信访局研究室的专家朱颖说,截至今年8月31日,他们已收到11641件关于拆迁的上访信,近3年来此类内容的上访信每年都要增长五成。截至8月31日,共有5360人亲自跑到国家信访局来投诉拆迁不公。 朱颖说这番话的10天后,9月15日上午8时40分左右,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蓉城镇居民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身上泼汽油后自焚,据称,此举是为了抗议当地政府的拆迁政策。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的第二宗拆迁户自焚事件。 突如其来的“必须搬走” 滨西大楼所在地,位于百年历史的商业街,一度是天津市小业主的聚居地。 60年前,王明水一家就在这里开大饼铺;另一户居民郎建桐的父辈是做图章盒的,后来用一根金条买下了一个院子;李俊茹的父亲则是用开公交车挣回的每月两袋面粉,置下了房产。 1973年以后,当地房管局推倒老院子,盖起了楼房,更多居民搬了进来。王明水们则从私房的主人变成了公房的租客。后来,居民中的一些人在房改时又购买了产权。频繁变动的房屋政策,使得居民与房产的关系变得纷繁复杂,这为后来出现的大量纠纷埋下了伏笔。 尽管6栋或五层或六层的楼房,现在看上去还是挺结实,居民们自豪地说,它曾经扛过了1976年的大地震,但今天它没能逃过被拆毁的命运。 滨西大楼的拆迁,对住户们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遭遇。他们在4月30日突然得知自己必须得搬家—— 一份署名为“麦购休闲广场建设项目现场拆迁办公室”的《致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塞进了居民家的防盗门里,要求300多户1000多名居民必须在5月15日~5月24日期间搬走。 后来居民们还是从报纸上得知详情,这里将投资3.5亿元修建一个麦购休闲广场,新主人叫胡时俊,是一名温州商人。他的公司花了8780万元买了这块面积近6000平方米的地,其中7350万元用于拆迁的综合费用,944.95万元向政府支付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天津市和平区信访办主任闰秉翔后来对记者说,这里的居住价值实际上不高,但商业价值很高。这句话清楚地解释了居民们为什么必须得搬走的原因。 那封公开信还“警告”说,“5月25日以后开始实施断水、断电、断煤气、切断通讯设施。” “我用放大镜看也没看清楚,没有图章,还以为是宣传画。”眼神不好的王大爷当时没把这封信当回事,他说,“不能凭一张纸就让我们搬家吧。” 此时,天津的市民们正沉浸在5月严重的SARS灾难中而无暇他顾。一名来自北京的SARS患者据说传染了175个人,令整个天津一片惊恐。滨西大楼的居民们不相信当此之际他们将会被“赶出”家门。 但到了5月26日零点,整个小区的水电气真的全停了,此时尚有20余家住户没有搬出,而已搬出的房子立即被拆空——住户们说,拆迁公司用“以料抵工”的方式把拆房的活儿包给了民工,因此民工们动作神速。 剩下的住户们压力越来越大,有些压力甚至是没有想像到的。靠摆菜摊维生的中年女人马永珍,22岁的儿子退伍后受聘于某街道综合执法队,7月初儿子回家说,上级领导要求他给家里做工作搬家,否则就下岗。马永珍拒绝后,不久,儿子回家闲着了。 此后的投诉、上访、甚至官司都没能阻止拆迁的进展。 拆了房子买不起房 居民们的抗争,当然并不完全出于对搬迁方式的不满,他们并不讳言“为了多要点钱”,“拆迁所得的补偿——平均大约每建筑平方米3600多元并不合理。” 王春来的房子建筑面积49.15平方米,可得补偿179488元。王说,这不仅不足以在相当的地段买到相当的房子,甚至在天津城区内另觅合适的安身之处都未必能如愿。 但天津和平区政府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样的补偿在天津已经是最高价位。 该区房管局局长可广欣说,和平区新商品房的房价大约在4000元左右,也有3000多元的,因此拆迁户拿到的钱足以另购新宅。 和平区法院院长刘建国也认同这一说法,但他同时承认居民们的具体困难:由于全市大量房屋拆迁,商品房特别是二手房价格上扬较快;而新房很少有100平方米以下的,原住房面积较小的拆迁户要购新房,需要另外添一笔钱。 王明水就为此所困。“房价涨得很猛,我没钱,买不起房子啊!”他拿到的14.7万元补偿金不够买新房,而一家五口人,儿子儿媳都下岗,全靠老两口1200多元退休工资生活。 家住临街一楼的李俊茹则另有苦衷,因为近街方便,她家开了一间衬衣店——在滨西大楼不少住户就是靠地利之便做点小生意。李俊茹说,去年曾有人出30万买外面一间房她都没出手。但到拆迁时,里外两间房总共只能拿到15万补偿。 “一搬家,生意就没地儿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麦购公司)是大个体,我是小个体,你要买这房子我可以不卖你。”但这朴素的生意法则在拆迁中却行不通。拆迁方的人对李俊茹说,这是政府行为,你们不搬也得搬。 拆迁,一个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性质界定的行为,在李俊茹看来是交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兵说,“如果是交易,还有平等的可能性,但这里根本就没有。” 秦兵认为这样的拆迁,实质是一种“征收”行为,“给了适当的补偿,但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如果说是交易,居民们却几乎未见过交易的对方——向他们购房购地(使用权)的麦购公司。能见到的只是和平区人民政府、法院、房管局、拆迁办的文件、人员以及其下属代理本次拆迁的和平区拆迁公司。 “这不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原住北京市新街口四条55号的赵伸,曾在此地拥有一个占地1亩2分的四合院,院子据说有270多年历史了,以前的主人是京城九门提督。 赵的祖父曾在民国时期出任教育部学部理事。50年代,因长安街扩建,赵家在邱祖胡同的老宅被拆迁,其父花了1万多元买下这座院子,大宅子包括44个房间,近600多平方米,其中26.5间、300多平方米为原建,其余为自建。 这座历经风雨的院子,在它最后的50年历史中命运多舛。文革期间,它被收归国有;80年代初赵家失而复得时,已经多出了3家房客;其余归赵氏家族18口人使用。 2001年,北京市西城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打算在这里拆除老旧的院落,建设“桃园二期”危改项目。在赵家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拆迁方给赵家所有房子的评估价是17万元,加上拆迁补偿,总共44万元。 但是赵伸说,他后来请的一家专业评估机构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个院子价值3000万!赵伸举例说,房子的格扇都是皇宫里出来的,共6扇,市价每扇6万。 折迁方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数字,拆迁代理人甚至拒绝与赵家讨论协商补偿价格,也拒绝给他们看相关文件。 “这不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过程。”赵伸 因此拒绝搬迁。 2002年4月27日,众多警察和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封锁了周围的街道。当赵家的孩子们放学回家时,发现家已不在了。所有的家什拉了23车,被运到了京郊大兴区。 赵家18口人不肯搬到大兴,因为孩子们无法在原来的学校上学,大人们也无法如常生活和工作。直到现在,这家人还在北京城“流浪”,租房或借住在别人家。 2003年初,赵家状告西城区房管局。他们“部分”胜诉了,法院认为房屋作价未经过产权人,且补偿安置协议不合理,要求对房屋重新作价并重新制定补偿条件。 但迄今赵未拿到一分钱。“房子已经没了,现在还怎么作价?”赵伸一脸无奈。 私房的土地使用权为什么不被补偿? 贾则戍一家,曾在北京崇文门拥有一个购于光绪23年的宽绰的四合院,光后院就有400多平方米。 1999年5月7日9点,贾则戍收到了崇文区房地局的裁决书,一小时后收到强拆通知——贾拥有产权房两间,每间20平米,开发商付给他拆迁补偿2万元,相当于大约每平方米500元,而宽阔的院子则全然不计。据说这已是当时崇文区的最高补偿价了。 让贾家心理不平的是,这里被开发商的广告称为“钻石地段”,写字间和公寓楼的每平方米售价均在万元以上。如果考虑容积率,则每平方米土地的地值更高。 从500元到10000元,其间的增值是如何实现的?居民们认为,增值主要来自土地使用权的转移。 拆迁户们认为,他们所得到的拆迁补偿,只是房屋的价格,即所谓的“砖头瓦块钱”,而房屋所占有土地的价值,则完全没有被计入补偿。但,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这才是最值钱的部分。 目前北京市拆迁的房屋中,约有1/3属于私房,其中大部分是建国前后私人购买取得的。另一项数据说,建国初进行了确权登记的私产房约有7万多户。在当时,房产都包含了房屋和土地两部分价钱。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不允许对城市土地进行出租、出售和转让等任何交易,城市土地(包括私房占有的土地)的价值因此长期得不到显现。进入90年代以后,国家允许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市场,城市土地价值也逐渐显现出来。但此时在危改和拆迁过程中,私房的土地使用权却没有得到承认和补偿,这也是造成房屋拆迁补偿价格与其市场价格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方可在解析上述问题时,引用了1998年轰动京城的“张婉贞诉东城区房地局案”,80岁的张婉贞在国子监大格巷拥有21间私房,占地500平方米,1942年购房共花了9205块大洋。在1998年的北京市场上,这样一个院子市值约400万元以上。但开发商拆迁时只给3万多块钱的补偿和6套没有产权的安置房。 拆迁时,开发商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则,对私房土地使用权不予补偿,而在售房时却使用了市场经济的规则,售价中显然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格。 这一进一出,“是当前城市房地产开发商暴利的主要来源。”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兵说。 这位律师解剖拆迁和开发过程中的各方利益分配(见下方资料)后认为,在无偿或低价获得了原属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后,政府直接从土地出让中的收益只是小头,大头被开发商拿走了。 政府在拆迁利益之争中扮演什么角色 2001年新的《拆迁条例》出台后,据称对原条例明显不公的地方作了修改。 相对而言,被拆迁人的确能得到更多的补偿——它要求拆迁补偿更多以货币补偿的形式进行,并且“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及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这样,拆迁户可以拿到比“砖头瓦块钱”更多的补偿,很多城市的拆迁补偿清单上有了两笔钱:房屋价格和拆迁补偿,并要求以评估价格为依据。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朱宏亮教授说,这其中考虑了土地的因素。 但是,这个条例对土地使用权予以补偿仍没有明确。秦兵说,这种补偿只是“偷偷摸摸的”,只能说一定程度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有关,但数额很少,法律上也不明晰。 法律上的模糊状态就很难确保拆迁户们得到足额的补偿,比如补偿价格的评估,由于没有科学的规则而存在争议。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的赵伸就拒绝承认拆迁方的评估结果,“不能他们说值多少钱就多少钱吧。” 朱宏亮指出,评估价格的争议是当前拆迁纠纷的一个重要源头。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拆迁房产的评估是由拆迁人委托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由政府指定的。 “有些评估机构经不住利益诱惑,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或与拆迁人串通,做不实评估,评估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较大,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一次会议时承认了这些问题的存在。 事实上,在房地产评估过程中,政府还有更深的介入——评估和补偿的依据也是由政府确定的,包括复杂的基准地价、房屋重置价、装修补偿标准等及纷繁的计算公式。比如在北京,政府就确定了10类地及其基准地价。 “这使得政府对价格的评估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和垄断色彩。政府有什么权力来确定交易价格,凭什么知道我的房子值多少钱呢?”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智晟说。 更为根本的是,当双方对补偿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也是由行政部门裁决。这样政府不仅能“指导”交易价格,甚至能“强迫”房主必须交易。 政府该站到哪一头 作为裁判或中间人的政府,常常遭遇拆迁户的指责或引起行政诉讼,这在中国众多的拆迁纠纷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费安玲说,很多事实表明,裁判并不总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实际上,在拆迁中,政府和开发商有时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更容易形成利益同盟,使行政权力和商业利益结合起来。天津一位希望匿名的银行人士曾多次参与拆迁工作,他向记者解释了开发商为何常常会把拆迁委托给有政府背景的拆迁公司。在他参与的一桩案例中,开发商一次性把900万元拆迁款打入银行账户,给拆迁公司的政策是节约归己,早拆一天给一天的奖励。由此,有政府背景因而更具强制力的这家拆迁公司拼命压低补偿价格,最后用780万搞定了整个拆迁。 经历过多次拆迁的这位人士计算,拆迁公司的利润率在12%以上。 高智晟说,在拆迁立法、执法和行政过程中,“都渗透了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房地产商的利益时常得到袒护。” 朱宏亮教授说,长期以来政府强调小局服从大局,只要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公民就应服从。所以拆迁条例更多强调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和接受,而不是对其支持和保护。“这种观点必须予以纠正。政府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牺牲民众利益,而是应该通过降低开发商的暴利,来降低房价。” 针对目前大量出现的拆迁纠纷,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的蔡定剑博士说,在当今中国,城市拆迁和对农民的土地征用中的一些个案,已经是对公民财产的侵犯最严重的表现。 北京的拆迁户群落及生存状况 在北京城周边的一些远郊区,聚集着一群因家园被拆而迁居于此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失去原有的房屋时,也失去了原来生活的秩序 南苑北里是北京市南四环和南五环之间的一个小区。从这里到崇文区的新世界中心,乘公共汽车要走一个小时。 2000年3月10日,张厚智的父亲张博文从这里出发,去了新世界中心。这幢由港商投资的巍峨建筑的下面,曾经是他们的家—— 一个拥有18个房间的四合院,张厚智的爷爷购于1950年,据说原来是李莲英的外宅。 1998年,张家被强迁到南苑北里后,75岁的老人难舍故里,常常独自回老宅去转转。但那天去后,他就失踪了,直到现在没有下落。 “一看就寒透了心” 南苑北里本来属于大兴区,但近几年被划归了丰台区,成立了和义街道办事处,进入北京市主城区。据称,这是为了管理方便——在此地生活的3000多户居民,都是由崇文区各地拆迁而来的,其中主要来自新世界地块。 8月20日,南苑北里的居民王凤云,拿着一份二审判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前一天去银行取款,发现丈夫每月500多块钱的养老金被法院冻结了。王没有工作,全家就靠提前退休的丈夫的养老金过日子。 不久前,北京开兴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出起诉,要求王凤云家偿付自2000年11月至2003年3月拖欠的1262.16元房租等费用,以及违约金120.52元。王凤云说,当初他们从崇文搬过来时,一直以为这房是置换给自己的,来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只是租户。 据称,此地的3000多户居民中,90%都没交房租。王凤云只是首批被起诉的10多户中的一个。接下来会有更多住户被分批起诉。 而在整个北京,像这样拒交房租的拆迁住户的数字更为庞大。据他们称,拒交的原因,一是不满于原来拥有的住房变成了租房;二是不满于安置条件。 类似的纠纷只是长期积存的众多拆迁后遗症的一部分。当更多人响应政府号召由城内搬到城郊之后,一部分人发现,新日子并不全如原来想象的。 南苑北里修建于1993年,当崇文门的原住民们逐渐搬来时,“一看就寒透了心。” 他们清晰地感到了巨大的落差。四年前,这里还属于一个农场,门口马路狭窄且没有路灯,只有一路公交车进城。院内杂草丛生,由于排水系统不完善,逢下雨就是一片泽国。迄今为止,这里也没有自来水,地下抽的水只能洗衣服,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大桶,到周边讨饮用水吃。 突如其来的迁徙给居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了巨变,原有的邻里关系、生活环境、工作便利都被突然打断。 杨宝东也是崇文大街的老住户,“住了好几辈了”,但4年前搬入新居后,生活一切都变了。8月份,他也刚接到要求付清房租的判决书。 “儿子本来在婚庆公司做摄像,儿媳原来学针炙,跟着医疗队到各个小区做体检。现在住得远了,进一次城得个把小时,赶不上点。两口子只好在家里呆着,有点活才能挣一点。” “孙女当时刚上初一,原来上学五分钟就到,搬来后坐公交车赶不上点,骑车又不放心。只好由奶奶带着上城里亲戚家住,后来孙女也顶不住了,花了4500元转到了附近中学。” “老伴原来是街道居委会主任,回来后心一沉闷,老想不开,三年前得了脑血栓。” “谁拆了我们的房子?” 南苑北里小区,每逢天气好些就满是下棋打牌聊天的人。拆迁户贾则戍说,很多都是丢了工作的青壮年。 张厚智就是其中一个,以前他每月出租房子能挣2000元,在崇文门一带摆个小摊,又能挣4000块钱,日子还算不错。被强迁到此之后,摊也没处摆了。 居住郊区化被认为是城市进程的发展方向。但是,居民们留恋着原住地的生活便利,上学、就医、社会保障等,也不肯把户口迁到郊区。由此造成了众多的“人户分离”现象。这也使和义街道办事处难以统计辖内的拆迁户的失业人员和领受最低保障者的户数,因而使一些经济困难的拆迁户丧失了“低保”的微薄收入。 清华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在北京,随着危改越来越进入城市核心区,回迁率越来越低;同时,开发商提供给居民的外迁安置房普遍离市区越来越远,大批居民被迁往远郊区县。由于安置小区不完善不便利,居民大都不愿搬迁。 报告还证明,对于大量中低收入拆迁户来说,被动迁往远郊区给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造成了极大压力。许多下岗职工和退休工人本来就需要依靠市中心区的商业环境谋生,在城内上班的职工往往花几小时上下班,许多人不能按时到岗,面临失业的危险。 一位拆迁户说:“在市区卖碗凉水就能挣钱,到郊区行吗?” 大规模拆迁形成的强迁户及一部分拆迁户,正形成新的城市贫困阶层。部分强迁户不仅生活陷入贫困,而且作为“钉子户”受到舆论的谴责和社会的歧视。 在北京市丰台区分钟寺一间楼村131号,有6排平房,每排16间,这里居住着由宣武区牛街、天桥等处强迁而来的居民。住在这里的崔进才一家原来在宣武区万明路拥有3间平房,出租给餐馆年租金8万元。崔本人是一名司机,日子还算过得去。 后来此地要建设变电站,崔进才对补偿不服,就被强迁到分钟寺,租金没了,工作没了,崔家只能靠亲戚接济。 这里本属农房,用地下水,农用电,买煤气罐,崔现在一边在院内种点瓜果蔬菜节约开支,一边打着官司。 崔的邻里苏三友的经历更为奇特。2001年,他从日本回到北京时,虽然此前并没有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自己家的二层小楼却已成了一片空地。但是,没有任何人承认拆了这房。 2002年12月,在他家的原址上举行了变电站的开工仪式,苏氏夫妇上前找区领导时,被一群警察架进了警车里,其妻车宪丽被架着四肢抬进了不远处一间小宾馆的101房。至今,夫妻俩就莫明其妙地在此生活了大半年,没人过问,也没人向他们要房租。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变电站现在仍是一片空地,围墙上留着拆迁户留下的一排字:“谁拆了我们的房子?” 有产者的维权困境 大规模的拆迁维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有产者”的财产意识的觉醒,并且寄望于将这种要求诉诸宪法 2002年9月3日,华惠奇一家正在北京崇文区南官园28号的家里吃早点,一群警察冲了进来——这里被划为了“危改加房改”地区,对回迁政策不满的华惠奇拒绝搬迁,由此在断水断电的环境下生活了数月。 华惠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回迁要求他家拿出31万元差价,他们一家人都没工作,全靠吃“低保”,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随后,华惠奇全家人连同家什被强迁到丰台区成寿寺关家坑村196号。这是一个农村大院,住着三四户人,都是被强制拆迁来的。 据华惠奇说,他们被锁在院内,由警察看着,平常不让出门,确有需要也是警车相送。甚至在华的表妹结婚及次年春节吃团圆饭,一家人也是警车相送赴宴。吃团圆饭时,华家坐一桌,警察也坐一桌。 今年4月21日,华惠奇一家被强制搬到太平桥西里23号楼一套房内。警察管得松了一点,只是大事不让出门。 华惠奇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他成了上访专业户,隔三差五就上政府各大重要部门走一趟,或者在阳台上挂上个条幅,每逢此时,太平桥经常堵上一阵车。 漫长而无果的集团诉讼 目前,一些拆迁户也主动走上法庭,希望运用法律手段争取权利,这正在成为一种发展态势。 王玉琴4年前从崇文门被强迁到南苑北里,很快就打起了官司,第一起状告崇文区房地局裁决不当,败诉;第二起状告崇文区政府强迁不当,法院拒绝受理(当时新世界拆迁二号地块的12户拆迁户均提起了行政诉讼,但结果都一样)。 后来,王玉琴看到了“法律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和执行房屋拆迁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其中规定: 因下列拆迁事由引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对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区域性建设决定不服,提起诉讼的; (2)对人民政府因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在裁决确定的拆限内拆迁作出的责令被拆迁人限期拆迁和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迁决定不服提起诉讼的; (3)对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就拆迁人、拆迁范围、搬迁期限等内容作出的拆迁公告不服,提起诉讼的; 王玉琴认为,北京市高院的这一规定超越了其权限,剥夺了《行政诉讼法》赋予他们的诉权。在告状无门之后的1999年,她曾一度成了上访户。 在依然没有效果的情况下,王玉琴所在的崇文门新世界2号地100多户,5号地几十户,1号地100多户,及崇外大街一些居民,分别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大规模的集体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市房地局。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也不断出现拆迁户的集团诉讼。这种维权行为,正由个体行动发展为集体行动。 西城区原金融街的骆淇椿等居民私房主状告西城区房地局,是北京市第一起由拆迁而起的集团诉讼。 由骆淇椿执笔,这些诉讼者起草了一份申请书,要求北京市房地局“停止侵权”。1999年12月,这份申请由贾则戍等5名代表送到该局,其上附有众多居民的签名。次年2月22日,骆淇椿等7人作为诉讼代表,援引《国务院信访条例》关于必须于30日内对申请人予以书面答复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北京市房地局未对申请书予以答复属于“行政不作为”。 此时,在诉状上签名者达到上万人。 在搬到南苑北里的拆迁户贾则戍的家里,不时有来自北京各处的电话相扰,使这个提前退休的老人成为一个大忙人。 “都是来问拆迁的事。”贾则戍说。文化并不高的贾此时已对各种法律关系论述得头头是道,“久病成良医嘛。” 和贾则戍一样,骆淇椿同样简陋的家里也摆了很多法律书籍及与拆迁相关的文件,这位北京一家工厂的职工,只能用业余时间来研究“土地批租”这样的问题,或者撰写一页页的举报信及各种材料。 诉讼仍旧一次一次地被驳回或不予受理,而举报也少有回音。随着一年年过去,即使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拆迁法规最终改变,他们曾经力争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仍是一个未知数。但贾则戍仍然年复一年乐此不疲,他并不太愿意对某家某户的具体拆迁问题过多置喙,他说:“这家的问题,和我家的问题,以及很多人的遭遇是一样的问题。” 法律与行政之墙 天津滨西大楼的居民们同样选择了走法律渠道,他们聘请了京城律师秦兵打官司。 秦兵在调查中发现:4月17日,拆迁方麦购公司即拿到拆迁许可证,而按照国务院《拆迁条例》,获得此证必须先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五项资料。但是,这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4月18日才登报公告出让,5月14日才公告挂牌成功。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在拿到拆迁许可证时,用地方尚未正式取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对此和平区房管局局长可广欣的解释是,拆迁证是根据当地的政策和政府部门的批件作出的。但居民们和律师发现,在向和平区法院申请强制拆迁执行时,申请人(和平区拆迁办)、拆迁代理人(和平区拆迁公司)、拆迁裁决人(和平区房管局)和房屋所有权人(和平区房管局)的法人代表均是可广欣,这一点使法院第一次裁定撤销了该拆迁裁决书。 政府官员如此介入,使得居民们对这宗纯商业项目开发中的行政力量的公允感到疑虑。结果是,和平区法院最终支持了强制拆迁。 秦兵对此深感无奈。接下来他准备走行政诉讼之路,但很难想象会改变结局。 根据现行的《拆迁条例》,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协议的,可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向法院起诉。但拆迁人已对拆迁人提供补偿或安置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并且,对逾期不搬者,政府可责成有关部门,或由拆迁管理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 也就是说,虽然条例规定当事人可以诉诸法律要求公道,但在律师们看来,这条路形同虚设。因为根据这一规定,在多数情况下,拆迁户对补偿不满,不能状告开发商,只能告政府裁决机关。而事实上,此类行政案例胜诉者微乎其微。 “有时候官司赢了,但实际输了,因为房子没了,你再起诉,就没证据了。最关键是结果已无法恢复。”秦兵说。 虽然秦所在的隆安律师事务所有一个专门负责拆迁的律师小组,但他几乎两年没接拆迁官司了。因为此前他代理的拆迁户的官司无一胜诉——即使有个别官司在法律上胜诉,但在现实中仍是输得一败涂地:胜诉之日,他们的家园早已被夷为平地。 “由国家行政权力强制安排民事主体间的合同行为,在全世界也独一无二。”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智晟说。高认为,此举违反了《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这两部法律里明确规定,外在权力不能干预合同的制订。 对《拆迁条例》进行违宪调查? 2003年7月14日,杭州市民刘进成通过北京“114”查号台问明地址,从杭州寄出一封带回执的双挂号信,收信地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信中建议“全国人大对《拆迁条例》作违宪审查。” 刘进成等116名公民在这封信中说,《城市房屋拆管理条例》和杭州市的有关规定对拆迁的强制性规定,“实质就是使得政府有权在居民未签约之下强拆公民住宅,或者强迫居民签约”,“把公民住宅置于任由政府权力处置的地位”,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 刘进成住在杭州市昌化新村,位于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办公大楼之间。去年7月20日,这里开始拆迁,准备新建一个商品房小区。开发商开出的条件是:回迁可以,但回迁价格要两年后才能确定。 “我们发现这是极不公平又很粗暴的方法,房子是我买下来的,我有权利卖,也可以不卖。”由此刘进成成了钉子户。 他和其他的拆迁户多次到浙江省人大等机关“宣传宪法”。此外,“用宪法在法院辩护”,先后帮其他拆迁户打了9起官司。结果是,依然没有挡住拆迁的推进。 7月20日,刘进成收到了落款为“全国人大收信专用章”的回执,回执并没有表明态度。但刘仍然对此感到欣慰,“从浙江到全国,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有一个拆迁户跟我说,原来我们都是‘钉子户’,感到好像理亏一样。现在你把宪法提出来,我发现自己是正大光明的。” 经过一年的“抗争”,刘仍然相信并坚持,通过百姓维权,能够建立好的制度,通过暴力却可能适得其反。 刘进成并不是第一个对现行拆迁条例提出违宪审查的公民。在此之前一个月,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智晟也向全国人大寄送了内容相近的信,提出《拆迁条例》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严重违反《宪法》和《立法法》。 这位律师说,按后者的规定,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只能由基本法律调整;根据《宪法》,基本法律的制定主体只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拆迁条例》显然涉及到对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的调整。 高同样没有收到回音,但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拆迁问题,而且试图运用法律手段改变他们认为不公平的现象。这种行动,正从自发演变为自觉。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费安玲教授发现,拆迁户大规模的维权运动与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兴起的两股浪潮同步。其一是大规模的“房产私有化”,通过房改及购买商品房,城市居民成为房产所有者;其二是由政府和开发商推动的城市大规模建设改造。在后一浪潮利益受损的有产者,成为拆迁维权运动的主角。因为对于这些新兴的“有产者”(即便财产数量尚不多),房产是家庭财产中最有分量的部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钱明星说,拆迁中存在的问题,核心在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够和不尊重,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而漠视公民的私有权。 这位参与了《物权法》起草的专家强调,“应该把房屋作为私有财产保护的重点。” (本刊记者刘志明、孙展对本组文章亦有贡献)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