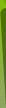托克维尔:革命时代的一个孤独的漫步者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6日08:17 外滩画报 | ||||||||||||
|
王志宏/撰文 陈寅恪先生早年曾自称“为不古不今之学”,他“不欲所为之学关乎今日之事”的缘由在于,今日之事切己太甚,作 为一个历史学家,往往不能压制自己强烈的私人情感,因而至于总是会在研究中间附己意,最终难以取信于历史。
陈先生初出此言时绝没有料到,几十年后,他所写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突破了早年汲汲严守的樊篱 ,更有甚者,他着意撰著了与近代中国历史关系甚大的家史——《寒柳堂记梦》;陈先生没有料到的另一件事是,如果说早年 所为“不古不今之学”造就了他作为历史学家享有的盛名,他晚年的著作就使他进入了思想家的行列,尤其在那一个“万马齐 喑究可哀”、“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时代,相形之下,他凭借这些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著作,陡然成为一个踽踽独行的巨人! 与陈寅恪先生不同的是,对于“今日之事”,托克维尔却一直持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立场,他从来没有把他自己和 历史分开过,既不认为自己可以独立于那曾在的历史,也不惧怕饱含着激情走进自己正在经历的历史。 早年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晚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述都是与他自己,与那个时代的人,不,与所有我们处于 这个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中的人息息相关的事情。它对于那辽远的,“烟波浩渺信难求”而又似乎不能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产 生切肤之痛的过去没有什么兴趣,那样的过去决不可能映入他的眼帘。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历史著作其实都是历史哲学或者说 政治—实践哲学的著作,他所关注的毋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生存样态。他总是能够走到风起云涌、汹涌澎湃的历史伟大事 件背后,去翻查它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各种善好与暴虐的方面,并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回忆录》就并不只是广博见闻、臧否人物之书,也不仅仅是对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 事件——1848年革命——作一个总结。在《回忆录》中,他既是兼有评判意味的观众,又是参与了全部事件的演员,正因 为如此,他有时候放弃了历史学家的职责,他没有全面而完整地搜集材料以使事情原委更加明确,更有曲致,他甚至采取了近 代以来第一人称小说的叙述方式,一切论述以“我”的亲身经历为经,以“我个人”的内心思考为纬,这非但没有使这部回忆 录变得很狭窄,正相反,这恰恰提升了他的思想深度,从而使这段历史的记述超越了作为“纯粹历史”的品格,而跃升为对于 普遍的人类历史和人性的思考。 伟大的个人的心灵史是历史上纷然杂陈的历史事实的内在精神与本质,同样,也是使处于历史当中的人超出历史得以 可能的前提。 革命时代的一个孤独的漫步者 伟大的历史人物遭遇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他的幸运。但是,不幸的是,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都是寂寞的。 托克维尔的寂寞与卢梭的寂寞有些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说,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就是革命时代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录。 与托克维尔的孤独相比,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人群》中所描述的置身于人群之中的诗人的孤独,多了一份清闲 、狂热与自得、迷醉,但却少了对于道义和更高人性的探寻的焦灼;相反,卢梭的孤独多了一份刻意、畏缩与对人群的恐惧, 而少了一份进入到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当中的沉着与坚毅。但是职责与生活当中充塞的各种忙碌都驱赶不了托克维尔的这种孤独 感。 在与那些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士兵、市民与乡亲的交往过程当中,无论是自己一次次侃侃而谈地发表演讲的时候, 还是聆听议员的议论的时候,无论是在和同事聚餐、共商国是的时候,还是深更半夜独自躺在自己的卧室中,无论是在枪林弹 雨、唇枪舌剑中,还是在踽踽独行、长夜一空之时,托克维尔都是孤独的。 一方面,他的孤独是他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有了更为沉痛、剀切的思考;另一方面,他的孤独又并没有使他与时代 、与历史限隔开来,倒是孤独推动他跃入历史的情境,深味处在“我们时代的扑朔迷离的局面呈现的混乱容貌”背后的深刻的 人性内容。 西方古典文明的现代继承人 由于贵族出身带来的各种信念,托克维尔不可能是1848年革命的参与者,但他也绝不是1848年革命的破坏者 。革命之后他由于一个更高的原则而真诚地拥护共和制政府,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一直为维护共和制而鞠躬尽瘁、全力以赴。 他也不是这次革命的旁观者,他自始至终以一个算得上非常重要的角色经历(erleben)了这次革命,经历(Erlebenis) 使他有可能对这次革命有更为深入的思考。 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尚未来临的时候,他在好几次议会演讲中已经有非常真切的预感。尽管他对于革命的真实缘由 ——“不久,将是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大战场将是所有权,而各种主要的政治问题将围绕以多大的深刻程度改变 财产所有权展开争论”——的认识入木三分,深刻无比,但他显然对于因为这个理由而出现一场革命感到非常遗憾。他认为, 有些不负责任的理论家想方设法叫穷人相信,人的贫困不是天意使然,而是法律造成的结果,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 依照穷人自己的意志重新制定法律,才能消除贫穷。这是革命的直接动力。 有不少批评者因此而批评托克维尔,认为他不公正地对待了那些穷苦的阶级成员。这些批评者固然有其并非完全不成 立的理由,但是我们注意到,托克维尔区分开了两个概念: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在他看来,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德行、个 人的自我完成,这些评价标准是人类存在的最高标准。阶级斗争是人从对于财富的欲望以及对于自己可怜的现状的痛恨中升起 来的野蛮的烈火,而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完成确保人的自由这个神圣的任务。 这种自古希腊以来就赋予个人的人性完成的观念在托克维尔身上可谓是根深蒂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托克维尔是西方古典文明的现代继承人。 时间并没有使我们更聪明 带着西方人古老的人性梦想,托克维尔观察了几次革命的过程。越是深味革命的本质,越是接触革命事件中更多的细 节,他就越是失望。他沉痛地写道,他本来以为这次革命是1789年革命的继续,但他最终发现,它们是同一场革命。 时间并没有使我们更聪明。革命固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但这也促成了一些使人惊奇而恐惧的即兴发挥。国王的逃遁, 议会里的吵吵嚷嚷、议而不决、各据山头、党同伐异,革命者的义愤填膺、不能自制,只有充满仇恨的激情,而毫无有活力的 激情,诸如此类。一切那么生动活泼,又是那么依稀相识。这一切都是法国人惯会表演的“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所产生的后 果,政府和革命者双方都像文人那般对政治进行判断,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政治家。 托克维尔的矛头不仅指向别人,他也常常调转矛头指向自己,对自己做了大量深刻而尖锐的反思。当然,托克维尔也 并不全是失望、震愕。在很多人身上,包括博蒙夫人、奥尔良公爵夫人、拉莫西里埃将军、乔治·桑、士兵以及从全法国赶来 支援巴黎的人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革命活力与人性的善良。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仅针对其他人或者他自己,事实上,他已经在反 思法国人的民族精神,而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常常最赫然醒目而又巨细无遗地表现在革命这样的事件中。 托克维尔反复申说:“我并不想写1848年革命的历史,只是努力追述我在这一革命当中的行动与想法,以及我对 这一革命的印象。”个人处境和视域的有限性使他的视野很狭窄,妨碍他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种 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托克维尔能够在某些方面深入思考下去,而且是在某些最为重要的方面。 政治家的德行 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是以政治家的身份登场的,在那些岁月中与他朝夕相对的是政治家。那些政治家,包括国王 、梯也尔、路易·勃朗、布朗基、路易·波拿巴、迪福尔,在他回忆录中无不有栩栩如生的记载,但托克维尔的目的不是简单 地颂扬与讽刺他们,而是直指政治家这一职业的神圣性要求。 自马基雅弗利以来,政治家的个人德行问题被弃置一边,从此,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问题,而 在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那儿政治学恰恰是伦理学的一门应用科学。 韦伯较早地反思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政治家的个人德行问题。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无一不把这个问题当作政 治学的主要问题——甚至当作核心问题——来讨论。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已夺韦伯之先声,以大量的篇幅和随意点染的 方式指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政治家的德行不是指制造理论的能力,蛊惑、鼓舞民众的能力,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能力, 甚至也不是息事宁人的能力,而是对人性的洞悉,对自由的爱好,对人的尊严的崇敬,对于真正的政治目标与政治责任的把握 。政治家的德性不仅仅在革命期间展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培育一种公民精神,使政治的激情不至于为其他激 情所取代。 在两次革命之间,“像法国人在政治激情方面要有理论家为他们的非理性行为找理由一样,各俱乐部也不断地在内部 忙于召开民众集会,以制造可以配合他们今后的暴力行动的原则”。这种所谓的政治是对真正的政治的亵渎与抛弃。托克维尔 甚至因此而痛斥布朗基、索布里等为疯子。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说:“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 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也许1848年革命远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价值,所 以托克维尔等到革命全部结束之后才动手写作以反思其全部过程。但是,托克维尔的反思所得出的很多结论或者开启出来的思 考方向并不比修昔底德稍逊风骚。 他们都看到了一点:在人类或者民族内部发生过的各种暴行,过去就发生过,而且,只要人类的本性没有发生根本的 改变,它将来就还会继续反复发生;只要人类存在,人的天性就会一次又一次战胜正义和法律的脆弱约束,让我们陷入对人类 本性深深的悲观之中。同时,也在考验我们作为个人在面对人性的卑劣时,是准备去修缮、完善,还是听任与放纵?! 尼采说,他把修昔底德看得比柏拉图更高,因为前者并不歧视人或者事物当中一切独特的东西,相信他们每一个都能 够给人无限的感觉和无偏见的快乐,而他的目的就在于发现这些独特而引人入胜的东西。我们同样可以把这样的赞美放在托克 维尔的《回忆录》上。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 、《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 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 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 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 长思想胜于行动”。 《托克维尔回忆录》是一本关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回忆录,对其间许多人物比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 破仑、阿道夫·梯也尔、路易·勃朗等 的评述十分尖锐,用语几近刻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该书在作者死后34年1893 年 才首次出版。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外滩画报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