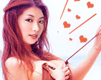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天堂电影院”的百年变迁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1日14:22 新世纪周刊 | ||||||||||||
|
-本刊记者/龙曦无论是在极尽奢华的大光明电影院,还是在打谷场的星空下,甚至是逼仄、空气污浊的录像厅里, 对于陶醉于电影中的人来说,它们都是“天堂电影院”。然而,时光流逝,观影方式也在变换,不知人们在公交车上观看手机 电影时,能否再找到电影所带来的感动与震撼。 6月24日,记者来到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大观楼电影院。半个
在大观楼影院的电影海报下,各色杂货小铺依然热闹。“大观楼美容美发厅”的价目牌立在电影院门口,而旁边的电 影厅已经被一扇卷闸门封住,让人只能站在门外遥想这个百年电影院的前世今生。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观楼影院停业的前几天,国内首部手机电影《聚焦这一刻》拍摄完成,将通过手机及网络下载在 全国公映。 从1896年,中国人第一次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茶楼里看到了“西洋影戏”,到汽车影院、4D影院及手机 电影的诞生,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变迁的又何止电影本身。 摩登时代电影“王宫” “现代的电影院,本是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张爱玲在小说《多少恨》中这 样描述。 19世纪末,一批“专业影戏院”从戏园、茶馆里脱身为独立的门户。到了1930年,中国已有233家影院共1 4万个座位。尤其上海,不但拥有占全国总数1/4的影院,而且欧美几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这里找到了代理人和发行商 ,首轮影院的影片差不多能与欧美同步上映。 “大约两三天就有新片上映,多得几乎看不过来。”79岁的上海“老克郎”朱廷嘉回忆说。而最让他难忘的,还有 当时首轮电影院里的优雅氛围。“入场有穿连衫裙的白俄女郎领座,领座的男士也是黑色西服,黑帽子,还戴着白手套,领座 员都非常安静。” 领座员掀开红色的天鹅绒帷幕,穿着英国毛料西装的男士,与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玻璃丝长筒袜的女人,以高傲的 姿态鱼贯而入。“西服、衬衣还得每天换,而且如果没去首轮影院,就会被女朋友看不起。”在朱廷嘉的描述中,电影院无异 于高级社交场所。摩登男女们管服务小郎叫Boy,即使10岁的卖爆米花的小郎都彬彬有礼。 而当时的上海大光明影院不但有三眼巨大的喷泉,铺着地毯的台阶,在默片时代,它甚至有一个由欧美乐师组成的乐 队。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为了让空气中都充满奢华的味道,还有工作人员会拿着喷筒在影院里喷香水。 严肃点,看电影呢 朱廷嘉说,那就是优雅。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细节,还有那种氛围,是今日的电影院所无法复制的。追星在当时也是很 时尚的事。朱廷嘉记得有一次在影院门口等了很久,只为了看一个印度女明星。据说好莱坞的明星偶尔也会出现在电影院中, 让观众惊喜异常。 为了模仿《乱世佳人》中的克拉克·盖博和《魂断兰桥》中的罗伯特·泰勒,大学男生有很多留起了小胡子、大鬓角 和鸡心头。朱廷嘉说:“还有种菲律宾Stye也非常流行,将后面头发留很长,两边拱起,就像鸭屁股一样。”朱廷嘉笑着 说,“女同学则流行模仿费雯丽,腰束得很细,把胸挤出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院都能如首轮、二轮影院一样华丽,普通市民、穷人也会穿着拖鞋去便宜的四流影院。“不 过,后来四流电影院也不允许穿拖鞋进入了。”朱廷嘉说,因为那时候,看电影是很认真、严肃的事情。 露天的大众狂欢 在上海“孤岛”时期,人们仍然按以往的节奏从容地生活着。即使“炸弹好像从头顶飞过,但照样看戏、跳舞。”然 而谈到解放后的电影,朱廷嘉则相当“郁闷”。 “当时的影片只记得两个,《南征北战》和《黑山狙击战》。”为了花几毛钱就能在有空调的电影院里睡个午觉,朱 廷嘉把《南征北战》足足“看”了22遍。自那以后,把几个革命影片当作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精神食粮的时代开始了。 尤其在乡村里,一些孩子追随着电影放映员的足迹跑了一村又一村,把同样的片子看了一遍又一遍。与上海的大光明 、国泰不同的是,这些“电影院”不但没空调没引座员,甚至连座位都没有。以星空为屋顶,以草木芬芳为香氛——这就是露 天电影院,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真正的“天堂电影院”。 “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次放露天电影的经历。当时人们情绪沸腾,欢呼跳跃,高喊毛主席万岁。”1950年国庆, 在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万人大会上,电影放映队的到来让人们欣喜若狂。当时,全国第一期电影放映员训练 班的学员石开基以实习生的身份,放映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他说简直无法形容那万人欢腾的热烈程度和自己激动、自 豪的心情。 露天电影的条件非常简陋,在电力不足的城市郊区和没通电的农村,放映员们还得自己发电,有时候电压不足影片就 会中断。不过,这丝毫不会影响观众的情绪。有人这样形容露天电影的“上座率”:蹲、坐、站、爬树,并在银幕后加座。 由于影片匮乏,很多片子是放了又放,以至于观众对台词都非常熟悉了。常常是电影里说了上句台词,观众马上附和 下句,交流气氛热烈异常。而当银幕上出现反面角色时,有的观众会向银幕丢石子、吐口水,乱成一团。 “露天电影一般都有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看。有的人可能都根本看不到银幕,但看露天电影图的就是那个热闹劲儿。 ”石开基说。 老影迷杨胜利则向记者回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有一次忽然下起了大雨。那是11月,天气冷得很,大家全身 湿透了抖抖嗦嗦的,但都舍不得走。家住得近的喊小孩拿了雨伞斗篷来,我可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也只有干淋着,硬挺了1 0多分钟。” 9岁的杨胜利回去病了一星期,不过他说自己并不后悔。那是他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看他最喜欢的《地道战》。 特殊时期的内部看法儿 文革时期,电影几成绝响。而一批“有敌情的和艺术的参考价值”的外国影片,如《生死恋》、《冷酷的心》、《红 菱艳》等,却被当作“政治任务”译制完成,成为一小部分人“参考、讨论”的“内部”片。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一个情节表现了当时内部片的观看画面。一群军区大院的孩子们混进了放映内部片的会议 室,如痴如醉地看着大胆的画面,但很快被大人们发现并赶了出去。文革时,看“内部电影”就和解放前进上海大光明一样, 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 作家阿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从乡下返回城里的情形。“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 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什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 ,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 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 当时的很多内部电影都是“过路片”。一些外国电影的版权卖给了香港或者别的国家,拷贝经本地停下来转移的时候 ,赶快从使馆拿来,半路沾点光,看完了就马上送回去。“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一票难求’?那时想走点‘后 门儿’,送电影票就行,这关系票比现在的名烟洋酒还有魅力。” 46岁的王忠因为有亲戚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所以偶尔能弄到关系票,他说,“如果小伙子能常常弄到内部片的 票子,就很讨姑娘的欢心。给姑娘送票时还要假装口气很平淡,那意思是这不算什么大事儿,其实心里别提多得意。” 文革时期,一些军区大院的小礼堂承担了电影院之职,而文革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多单位礼堂、会议室,都“ 鱼目混珠”变成了“电影院”。王忠说,由于有些单位电压不足,放电影就没法儿开空调,大热天的,有时候一大堆人挤着几 小时看下来,就像蒸了个“桑拿”,“不过就是蒸得馊了。” “泡”在录像厅 文革之后,“饿坏了”的中国观众终于迎来了“大餐”时代。“那时候观众既能看到新拍的影片,也能看到五六十年 代的电影,甚至解放前的《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都能看到。”知名编剧、影评人程青松说。排大队买票看电影 的场面出现在各个城市,甚至小城镇的电影院门前。 到了90年代初,录像厅突然遍地开花。程青松当时在做放映员,他所在的电影院也开了个录像厅。“录像厅票价便 宜,只有电影票的一半。而且录像厅放映的港台影片,大都是走私盗版过来,在电影院没法放。” 港台影片,尤其是香港武打片、黑帮片在当时确实很“抓人”,很快让录像厅拥有了一批“铁杆儿追随者”。无数7 0年代出生的人,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空气污浊、环境嘈杂的录像厅。 “我对电影的迷恋就是从泡录像厅的少年时代开始的。”李蒙(化名)如是说。“父母在外做生意,也没人管我。有 时候逃课从早看到晚,看得昏天黑地。”李蒙在录像厅里爱上了电影,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仍然抛不掉电影情结,进入北 京电影学院进修,现在已成为一名摄像。 与李蒙不同的是,很多人在录像厅里完成的不是电影启蒙,而是“性启蒙”。录像厅出现不久,一些香艳的片名便充 满了门口的小黑板。直至前几年,一些城市的火车站录像厅仍然“理直气壮”地叫卖着“三级片”。 “作为录像厅泡出来的一代影迷来说,三级片在记忆中必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可是录像厅里最火爆的片种之一。 记得当初通宵到后半夜时,一些睡眼惺忪,甚至已鼾然入睡的哥儿们突然精神抖擞起来,正襟危坐,因为李丽珍出场了……” 有人在文章里津津有味地追想当年。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常常以“黄色录像”的称谓来代替“三级片”,这与录像厅播放影片的良莠不齐是不无关 系的,而经常出入录像厅的少年则被视为不良分子。 2000年,河南焦作一个叫“天堂”的录像厅里,74名反锁于内看黄色录像的观众被大火烧死。此后两年,录像 厅作为城镇“死角”被渐渐清理,而昆明、珠海等城市则索性实行了一次性“死亡”。录像厅的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私人观影时代 电视电影、影碟、网络电影……随着电视、VCD、DVD、网络的迅速普及,看电影不再是一大群人扎着堆儿同哭 同笑,而变成了在自己私密小空间里的自娱自乐。 有着“大银幕情结”的程青松虽然收藏了4千多张DVD,但他并不认同看碟与看电影是一回事。不过,时下很多的 年轻人都以“碟客”身份为时尚,迷恋看原声,聊花絮,而喜欢“免费午餐”的人,则疯狂从网络上BT下载着各种影片。 “两个人去电影院里看电影,至少要花40元钱,还不如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里放的电影,我前一阵子还看了《乱世佳 人》。”“老克郎”朱廷嘉仍然对参加part跳舞情有独衷,但电影院,却已经是几年不去了。他说,小青年谈恋爱才去那 儿。 和“朱老克朗”的想法一样,月收入6000元的白领吴小新也很少进电影院“谈恋爱”。“太贵了,不值,好片也 不多,只有特别有视听震撼感觉的大片才去电影院看看。”吴小新说,“我现在碟都不太买了,反正很多片子只看一遍吗。网 上多的是DVD版本,画面也很清晰。” 程青松认为,看电影一定要大银幕,只有这样才能感受电影的视听效果。然而,现代的时尚个性载体,已让电影“银 幕”小到不能再小,如手机电影。而被程青松称之为“世俗的宗教活动”的观影感受,也变成了一道能随时随地享用的时尚“ 快餐”。 电影期待温暖 也许,汽车电影院仍能找到些许露天电影的影子,但在老影迷杨胜利的心中,却没有了那种温暖。“小时候看露天电 影,都是人挤着人,热热乎乎的,一不小心可能就碰到后面女人的胸,或者闻到旁边大爷口中的蒜味儿。”而在屏幕超大的汽 车电影院里,和杨胜利的雪佛兰开拓者排排坐的是一辆辆漂亮而冰冷的汽车。 “看到激动处我会按喇叭‘鼓掌’,不过应者寥寥。”杨胜利苦笑着说,影片结束后,“汽车们”一溜烟儿走了,他 很怀恋那种大家一起翻山越岭回家,一路热烈讨论电影剧情的日子。而程青松则执著地相信,电影院迟早有一天会真正复苏。 2003年3月,三峡正式蓄水之前,程青松回到曾工作过的重庆市云阳县电影公司。当年电影院大厅的椅子都已经 被拔掉,隔成了很多间小房子,住着三峡移民。而在电影院的窗口,程青松却意外地找到了1986年他用美术颜料在上边写 的三个字:“售票处”。 17年光阴,颜色已经褪尽,唯有字迹依稀…… 相关专题:新世纪周刊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世纪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