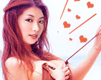凤仪萍 守护生命的记录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1日14:22 新世纪周刊 | ||||||||
|
-本刊记者/旺达摄影/阿灿1942年11月27日,东条英机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做出“关于华人劳工遣入日本内 地的规定”之后,大约四万名中国人被强制劫运到了日本,14岁的少年凤永刚就是其中一员。60年后,回首那段在人间地 狱里度过的日子,凤老依旧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愤。 1945年,在北海道那间四面漏风的工棚里,一本写有300名中国劳工姓名和住址的小
因超强度的劳作以及寒冷饥饿的摧残,不久那位工友就病死了。凤永刚翻出小册子在“费铎”这个名字的后面,为客 死他乡的同胞做了最后的注释:“2.4病”(2月4日,病死)。 因为要下到漆黑的煤矿去劳作,凤永刚的每一天都在生死之间挣扎。他将“生死簿”藏在“榻榻米”的木板下,嘱托 身边的工友:“这里面有一个生死记录本,万一我死在煤矿里,你们一定要带回去。” 然而“生死簿”坚定了凤永刚活下去的信念,他终于活着爬出了那个比地狱还要黑暗的煤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记 录着那些曾经鲜活过的生命的“生死簿”,在被凤永刚苦苦守候了60多年之后,如今正静静地躺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大 厅里,向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平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真实而深刻的疼痛 凤仪萍,男性泌尿领域内蜚声全球的医学专家。在广州这个忙碌而纷杂的城市,当记者坐在公园的一角听凤永刚讲述 所亲历过的那些苦难时,没有人注意到眼泪正无声地渗入凤仪萍眼角的皱纹。 当年的凤永刚,现在的凤仪萍,他们原本就是同一个人。 阳光直直地照射在那份沉重的名单(复印件,原件已送至博物馆)上。凤仪萍颤抖的手指指向每一个名字,向记者描 述他们的相貌以及少得可怜的个人资料,当年同他一起被掳至日本的300人中有92个再也没有回来。 “早上4点多就被赶进煤井,晚上12点才出来,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太阳。如果从井里出来一脚踩进雪地里,就知 道那天的天气不好,刮风、下雪了;要是踩上去滑溜溜的,就知道白天的天气一定很好,出了太阳……” “即使病死了、被打死了,日本人都不管,我们把死者送到火葬场火化后,匆匆埋了就要赶回去干活,不知道他们的 坟墓还能不能找得到!多想有一天再去看看他们,告诉他们,现在我们的祖国很强盛,再也不会遭人欺负……” “晚上跟你一起从煤井爬上来的工友,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他吊死了……劝不回来,人已绝望了,他要死,无论 你怎么开导都拽不回来……”凤仪萍的诉说来自并不遥远的上世纪40年代,尽管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日军的罪恶行径,但 当近距离面对凤仪萍的时候,心中的疼痛显得真实而深刻。 战争中的童年 1930年,凤仪萍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木材商家庭,母亲生下他时已经40多岁了,加之他又是家里最小的男孩, 自然倍受宠爱。 7岁那年,父亲见他实在淘气,便安排他跟着一个上了五年级的姐姐去学校。不久,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侵 略者也加紧了对上海周边地区的轰炸。那段时间,年幼的凤仪萍感到最恐惧的事情,莫过于看见画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 。不得已,父亲找人做了一艘大木船,带着家人去逃难。 木船到了上海外滩的英租界,印度巡捕却拒绝了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家庭提出的靠岸请求,当木船再次漂回浦东老家 的时候,房子已被日本飞机炸平了。房子虽没有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在家人的努力下凤仪萍在老家读完了小学。 1944年,凤仪萍刚满14岁,在上海教书的哥哥将他带回了上海,参加复旦大学教授开办的暑期补习班。从一位 老师口中,凤仪萍了解到重庆后方的一些情况,他想到父亲的木材公司已快被烧光了,再加上日本人和伪军隔三差五就来勒索 钱财,如果真能到重庆去也是一件好事。 他打算先到同学那里打探一下情况,带上“良民证”和路费出发之前,凤仪萍只是简短地告诉父亲:“我到上海去几 天。”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400多天。 掳往日本 当时,日本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扫荡),从浦东到上海沿途就设了三道关卡。凤仪萍刚过浦东关卡,身上 的路费和“良民证”就被搜身的伪军抢走了,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赶路。从浦东到外滩海关大楼下面的码头,这一路都很顺利 。经过南京路拐上四川路,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凤仪萍心里也放松了许多。 四川路的南端是英租界,北端是凤仪萍的唯一路线,在那里,日本人设立了新的检查站。“站成一排!都把‘良民证 ’拿出来!”面对日本兵粗暴的命令,凤仪萍只得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站到队伍中。结果,他跟几个拿不出“良民证”的同胞一 起被轰上一辆卡车,等差不多装满人的时候,汽车启动了,一块苫布把车上的人盖得严严实实。 人们被赶下车时,已置身上海虹口的日军集中营,早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人被关进了这里。突如其来的意外和惊吓把大 家都搞懵了,在黑漆漆的空间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过了很久之后,角落里的凤仪萍听见一个人的声音,他说:“大家别 害怕,不要紧的,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当时当地,这句话多少给人们带来一些安慰。 在集中营一待就是半个多月,在漫长的等待中,每个人都忍受着精神上巨大的煎熬。终于在一天深夜,门口传来日本 兵的吆喝声:“起来!都起来!” 此时已从门口开进了十几辆大卡车,凤仪萍跟在人群中登上了其中的一辆。汽车在吴淞口的码头停下来,人们被赶进 一艘货轮的底舱里。“轮船的两头都是拿着刺刀的日本鬼子,有人想跳黄浦江都来不及。通往底舱的门很小,我们就在日本兵 的监督下一个一个往里面走……” 货舱里只装了一半的铁矿砂,另一半的空间,显然是为“乘客”留出来的。此时,人们心中压抑了许久的惶恐终于爆 发了出来,再也顾不上许多,开始互相交谈起来。围绕“我们究竟被送到哪里”“这是干什么呀”的话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猜 想。 有人说:“是不是因为日本鬼子在前线伤兵太多需要大量的血浆,拉我们去抽血?”马上有人提出相反意见:“抽血 在哪里不能抽呢,上海也可以。”人群里有两个以前当过海员的,缓缓地说到:“看样子不像去抽血。” 随着轮船的启动,货舱里有了短暂的寂静,之后是更加绝望的猜测。只有14岁的凤仪萍听着“大人们”的讨论,心 里害怕极了。第二天清晨,两个同胞从船底的悬梯爬了上去,纵身跳进了滔滔黄浦江,闻声赶来的日本兵对着江面一阵扫射过 后,那两个身影便永远地留在了江底。 怀着极度的不安在海上飘荡了20多天,终于在一个傍晚看到一个港口。“那是日本的门司海港,大家一下子明白过 来了,做梦也没想到被抓到日本来。” “因为在船上待了20多天,我们身上全是铁锈的味道,也有虱子和臭虫,下船之后就被赶到两个装满来苏水的大水 泥池子里面,脱光了衣服在里面泡了三四个小时。上来之后,大家抱头痛哭,哭爹、哭娘、哭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到达日本的那天夜里,饥饿、劳顿和恐惧折磨着这群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人间地狱 日本下关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地方,1894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就在这里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和 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50年之后的1944年,凤仪萍和其他同胞在这里登上了开往北海道的小火车。 “上火车之前我们见到了从北海道赶来的两个日本‘监督’,一个叫小田岛,一个叫佐藤,小田岛曾经在日本侵略东 北的时候当过军曹(相当于班长的职务),这两个人是来管理我们的……”在两个日本人的“监督”之下,小火车途经青森、 横渡津清海峡到达北海道的函馆、辗转夕张来到了栗山町(镇)的角田煤矿。 凤仪萍回忆道:“小田岛的脾气很坏,打人很厉害。我们不能反抗更不能回绝,否则就会招来一顿毒打。当时感觉最 痛苦的就是离开了祖国和亲人,如果我们的祖国和民族都很强大,我们就不会受这样的罪……”他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颤 抖的声音传递出这个古稀老人隐藏在内心深处巨大的委屈。 工头把近300名中国劳工分成六个小队,每天给的粮食不到半两。大多数情况下,劳工们依靠草和树皮果腹。凤仪 萍指着公园里常见的那种长着圆形叶子的低矮灌木,告诉记者:“这种树是最好吃的,所有的树里面就属这一种最好吃。” 每天早上四点,劳工们准时到厨房去领一个“便当”,然后到第一个管理处领取柳条做的安全帽和矿灯,之后劳工们 下到井下,来到第二个管理处领取风钻、煤铲等工具,最后来到四米长、一米高、宽度在两米左右的采煤段,开始一天的劳作 。 至于在地下的劳作场景,凤仪萍是这样描述的:“通常是先打炮眼,前面一个人跪在那里,后边的人拿着风钻抵在前 面人的肩膀上,哒哒哒开始钻,那些煤粉直接冲到嘴巴、眼睛、鼻子里甚至呛到肺里去,打到一尺左右,把炸药放进去,日本 工头在很远的地方合拢一个开关,我们赶快躲到隔壁的采煤段去才不会被砸死…… 爆炸声刚过,烟雾还没散尽、煤块也没有完全掉下来,工头已经开始往下赶我们了。稍微慢一点,工头就会手拿前面 绑着榔头的棍子敲打你……有人被煤块砸死在下面,也有人在放炮的时候就被炸死了,这就是我们在地下的劳作。” 无望的逃跑 生病的劳工在经过日本工头的确认后,可以到最后一排的工棚里休息,但每天只给两碗稀得和水没什么区别的东西吃 ,多数人都被饿死。 凤仪萍也曾因为顶撞工头中村,被他一刀砍在手指上成为病号,凤仪萍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多亏了工友们。当时那本“ 生死簿”已交到了凤仪萍的手中,作为劳工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工友们把“活着带出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为了 不让凤仪萍饿死,劳工们每人每天从自己的干饭里舀出一小勺留给他吃。 在凤仪萍的周围,除了有人不堪折磨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苦难之外,也有人选择了逃跑。曾经有五个工友成功从煤矿 里逃了出去,气急败坏的工头将劳工们集中在一起大发雷霆:“你们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北海道!四面都是海,你们等 着瞧,不出一个礼拜我们就把他们抓回来!” 工头把逃跑劳工抓回来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雪,他们被剥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中村和佐藤用木棍和鞭子一直抽打到 几个劳工奄奄一息才停手,任凭他们赤身裸体躺在雪地上直到冻死,其他劳工在工棚里又一次痛哭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的灾 难呐!” 重归祖国 就这样,劳工们在没日没夜的劳作中,400多天过去了。 1945年的7、8月间,人们开始发现工头们的叫骂声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在井下的时间也短了许多,每天早上 8点下到煤井,在傍晚5点钟就结束劳动,甚至还见到了没有完全落下的夕阳。劳工们开始向着祖国的方向祈祷,希望早日结 束非人的生活。 9月15日这天,劳工们得到“今天不用下井”的通知。上午9时,两个美国兵驾驶着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来, 忽然见到这么多衣衫褴褛的劳工,感到十分诧异。其中一个用英语问到:“你们从哪来?”“我们从中国的上海来。”懂英语 的人回答道。 两个美国人流露出更加不可思议的表情:“战争已结束了,日本以失败告终,你们为什么还在为他们干活!”听闻这 个消息,劳工们从工棚里跑了出来,相互拥抱着又一次号啕大哭。 1945年10月,满载着3000多中国劳工的日轮“明优丸”号驶进了长江口,劳工们站在甲板上纷纷把从日本 戴回的帽子丢进大海。 由于没有御寒的衣物,凤仪萍坐在返回家乡的小火车上仍旧穿着日本军服。乘客们对他举起拳头:“日本小鬼子怎么 还不滚回去!”凤仪萍流着眼泪,向周围的人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回到家中,他才得知母亲已病了一年多。看到皮肤溃烂、瘦骨嶙峋的小儿子,母亲不住地嗔怪:“你怎么搞的,一年 多也不回家!”凤仪萍试图向母亲讲述自己的遭遇,但她已经听不明白,一个月后就去世了。 交出生命的证据 从日本回来后,在侄子的建议下,凤仪萍重新回到了中学。北海道的那段经历,几乎每晚都在惊扰着凤仪萍,他不敢 让别的同学知道,也很少与人交谈,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读书上。 工友托付给他的“生死簿”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那些冤死的工友们,凤仪萍的内心充满感 伤。他说之所以选择学医,跟自己当年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当年跟工友们分别时,他们大都20多岁,只有我还是个半 大孩子有学习的机会,工友们叮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让祖国强大起来……” 本来,凤仪萍的愿望是等自己“天年”后,再将“生死簿”捐献给国家。但当淞沪抗战纪念馆的领导找到他时,凤仪 萍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这本‘生死簿’如果放到博物馆,就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军国主义 的暴行;另一个方面,这个小册子我已保存了60年,把它拿走就像从我身体里掏出一个器官一样,实在很难割舍……” “最后,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对他们说‘我可以交出去,但是能不能再让我保留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躺在 床上把它放在心口的地方,一夜都没有睡着……” 相关专题:新世纪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世纪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