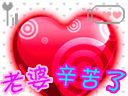北京城中村加速消失带来的阵痛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17:23 《法律与生活》杂志 | |||||||||
|
2006年,北京市“城中村”整治的规划数字为80个——“城中村”的消失正在加速。 “城中村”的消失是艰难而不可逆转的,但采访让我们知道,“城中村”的重建更加艰难,要重建环境、治安、文化、和被推土机掘伤的亲情。 东村人的幸福生活
本刊记者/吕娟 李云虹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东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会新认为,用这句话来形容东村人这些年生活的变迁,再恰当不过。 2006年1月12日上午十点多,原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黄土东村41岁村民张富国(化名)两手拎着刚从附近菜市场买的两大兜菜,哼着小曲,慢悠悠地朝家的方向溜达着,时不时地遇见几个街坊,停下来笑吟吟地寒暄调侃几句。 自东村拆迁失地后,张富国一直没有工作,而这样悠闲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一年多。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东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会新认为,用这句话来形容东村人这些年生活的变迁,再恰当不过。 阵痛 东村家园,原回龙观镇黄土东村,位于北京地铁十三号线回龙观站以南一公里处,东、北紧邻回龙观经济适用房文化社区。在北京城市紧锣密鼓地向郊区扩充、市内房价急速飙升的进程中,这里的低价、交通便利无疑成为低收入北京市民以及进京打拼的外地青年居住生活的首选。 在这样的环境中,东村家园用不一样的楼体颜色,封闭的社区院落,独立的物业管理含蓄而轻松地宣示着,这里是一片与众不同的乐土。 62岁的东村村民刘志芩的乐,像盛秋的菊花一样,张扬地“开”在脸上。 40年前刘志芩从娘家北流村镇嫁到黄土东村时,这个村子仅几十户人家。贫穷,闭塞,鸡犬相闻的生活让从小对跳舞唱歌说快板痴迷的她必须立即收敛起所有喜好,勤勤恳恳地过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当然包括生儿育女。 “汗珠子掉八瓣,见不到一分钱”,那时,所有黄土东村的壮劳力辛苦一天的价值是一毛七分八,对于村里的大部分农民来说,尽管守着皇城根,但仅往返北京城参观的车票就高昂得让他们不敢奢望,刘志芩跟同村人一样,羡慕城市里的人,却觉得遥不可及。 辛苦到2002年,刘志芩的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终于长大成人,并各自成家生子。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郊县逐渐地变为市区,地铁轻轨沿着城市开发的脚步一路向北延伸,黄土东村迅速地湮没在一片片高高矮矮的楼房当中。尽管早些年村里的田地已被国家征用,“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但城市扩张也同时卷来大批的外地打工者,在原有的宅基地上尽可能加盖几间平房出租给外地人,几乎成了每户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刘志芩家的小四合院有五间大北房,挤了祖孙一家九口人,同时还要出租几间赚点租金维持生活,拮据可想而知。2002年,当市政府拆迁的通知正式下到黄土东村时,刘志芩急得直掉眼泪。地没了,赖以生存的房子又要没了,换来个城市居民户口,却连像城市人一样供养楼房的技能都没有,刘志芩想不出将来的生活还能恶劣到什么程度。找村委会干部吵、闹,虽然对方拿出各种补偿政策反复解释让她吃定心丸,并一再强调两年后即可回迁,刘志芩仍旧觉得,一旦离开这块土地,未来的生活就是未知数。 搬迁的日子到了,刘志芩和老伴决定回她娘家暂住,子女留在村子附近租房。破旧的家当一狠心扔了,又转眼心疼地找了回来,跟随自己大半辈子的缝纫机才能卖5块钱,刘志芩没有舍得,老两口扛着缝纫机含着热泪离开黄土东村。那时,刘志芩专门为搬迁编了一段快板,现在,词忘了,但那种“心中就像打翻五味瓶”的滋味,她仍记忆犹新。 刘志芩65岁的老伴祖辈生活在黄土东村,虽然他干了一辈子的铁路工人,但对农村这块土地的依恋却有增无减。比起老伴,他更心疼的是,拆迁将使这个明朝时期就存在,有了600多年历史的小村庄从此彻底消失,若干年以后,随着东村老人的一一离去,东村富涵的古老传说将永久地被林立的高楼尘封于地下,无人传承。 花儿样幸福 2004年11月15日,黄土东村的改建竣工。曾经像一块疮疤般嵌在周围崭新的楼群中的小村奇迹般消失了,破旧的平房、随处搭建的违章建筑、零乱狭窄的小路被整齐气派的十栋七层住宅楼以及楼间规则点缀的草坪、室外健身区取代,小区正门一块醒目的石碑上刻着红漆大字——东村家园。 刘志芩觉得,她前半辈子体验过的惊喜都没有回迁那一刻的多。各种形状、功用的健身设施,杵在健身区一角供居民健身散步时享受的大屏幕液晶电视,各单元门前的残疾人车道、可视性密码单元门以及铺着瓷砖地面的楼道令她无法置信,这里是她曾经居住过几十年的东村。 但更令她不敢置信的是即将属于自己的房屋。 按照补偿政策,刘志芩一家九口人,不论男女长幼,每人回迁补偿的面积是70平方米,11岁的长孙因为是独生子额外补偿2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一家人将拥有9套共650平方米属于自己的房子。同时,东村当时拆迁的现金补偿额为2700元~2800元/平方米,回购房的价格为1200元~1800元/平方米,一消减,一家人轻轻松松攥着了几十万元的存款。 房子不愁了,连装修的钱也省了,作为村里的福利,每套房子由村里统一进行装修,瓷砖地面,白墙,整体橱柜,光洁的卫浴设施,整个房子“搬张床进去就能住”。而更超出刘志芩想像范围的是,屋内统一配备可视对讲,主卧安装应急按钮,预防突发事件,阳台窗口装有红外线防盗警报,直接连接24小时监控的物业。 对于刘志芩来说,幸福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子飞进她的心里,压在心底几十年的生活重担转瞬间消失了。一家人经过合计,9口人按户各住一套房,其余的五套出租。老两口从此的起居生活就像度假,有事就回自家住,没事三个孩子家轮番转,生活的重心变得简单而轻松:一边含饴弄孙,一边琢磨怎样能让晚年的生活过得“快乐潇洒”。 刘志芩很自然地捡起了自己曾经的喜好。大队办公楼一层400多平方米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她的舞台,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她是在这里度过。清晨太极,上午秧歌,午睡后快板、合唱、评书,晚上再来趟交谊舞,稍有点事儿耽误了,伙伴们催促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刘志芩觉得自己似乎比年轻时还忙碌,但这种忙碌让她的眼笑得像弯月。 刘志芩的老伴张万达喜欢别人叫他“老青年”,因为他觉得自己两次死里逃生,如今却活得这样潇洒,就像获得了新生,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1995年和2003年,张万达两次因突发脑溢血报了病危,但又奇迹般活了下来。更令家人感觉惊喜的是,自从住进了新楼房,他因生病落下的行动不便竟慢慢地好了起来,现在,他自动参加了村里的老年乐队,并在刚刚过去的阳历新年,与老伴和其他村民共同组织了一台3小时的晚会,正如他说的,“发愁的事没了,身体自然就轻便了”。 65岁的张金林三十年前的梦想是,穿没有补丁的鞋,拥有一块城里人戴的手表,过年的时候可以不用四处借钱。 但现在的生活远远超出了他的梦想。住进了120平米的楼房,看上了40多寸的等离子电视,每月坐收几千元的房租,买了车,当然也戴上了梦寐以求的名牌手表。 比起物质生活的变化,更让张金林感怀的是村民们精神需求的提高。体弱的老人舍得花钱雇保姆照顾,村民的家务活都是请保洁工来干,家家户户虽然都有车了,但是却不像以前那样渴望进城了,“污染严重,交通紧张,住的都是鸽子笼,不如这里的生活原生态”。 张金林认为自己接受新鲜事物享受生活的步伐甚至更快一些,他懂得了什么叫养生,花上万元购买按摩椅,健身器,组建了村里的老年乐队,最近又筹划着买架钢琴,要不是儿女劝住,65岁高龄的他甚至想学会开车后自驾车外出旅游。 当然,张金林也感到了生活质量的翻天覆地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前邻里串门,推门就进屋,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但现在一门就是十几户,又记单元又记房号,若干次跑错后,走家串户慢慢地减少了。以前,谁家儿女结婚送一对枕巾就算贵重,但现在,每年的人情礼就得一两万,“虽然心疼,但都是邻里,必不可少”。 村干部难念的经 四年前,35岁的杨会新被村委会请回来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时,急得牙床整整肿了一个月。 杨会新早先在回龙观一个国有房地产公司工作。照村里老人的话说,这个他们看着长大的穷孩子是少有的几个走出东村出息的小子。杨会新在公司的待遇不差,部门负责人,几千元的月薪,丰厚的年底分红,工作相对轻闲。他至今都觉得离开公司是个遗憾,但他也知道,自己没法拒绝那些被自己叫做叔叔伯伯的老村干部的邀请。 杨会新不愿回村的理由很简单:他太清楚农村的工作方式,公司企业有完备的章程,谁违反规定,按章程处理,但在低头抬头都是熟人、长辈的农村,想不计人情大刀阔斧地办事几乎不可能,“扣谁钱,他们全家上你家理论,不行就搬出最老资格的长辈坐镇,直到你没法为止”。而更令他备感压力的是,2002年正是东村“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处理不好,“在村民的眼里就一辈子不得翻身了”。 回村后,杨会新才发现,新的村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不足40岁,他明白了前任党支部书记所说的“继往开来”的含意。 杨会新说那时工作的底限是不让村民骂:村民不愿搬,就要反复地向没念过几年书的他们解释北京市拆迁补偿办法,直到替他们把账算清楚为止;大部分村民念旧情,希望回迁,他们就要一遍遍地与开发商谈判,直到他们点头同意为止;一些老人认为村东头的正午庙是黄土东村的精气所在,同时也是古迹,万万不能拆,他们就要想法最终让开发商妥协,专门留出那片场地;年纪大的村民希望能通电梯,他们软磨硬泡让开发商突破经济适用房的楼层限制,硬是多要了一层;之后,从建房、装修到分房,每一个程序都会组织村民代表到其他社区甚至广州等地参观取经,然后召开村民代表会进行讨论,包括地砖铺什么颜色,炉具用什么款式,门窗用什么牌子,分房以什么为标准…… 东村分房采用的方式是抓阄,按照标准,杨会新一家三口可分得三套房,有了电梯,谁都希望自家的楼层能高点,但杨会新接连抽的都是一二层,这令他挺懊恼:“事实就是,干部在这里,没有一点特权。” 农村没了,村委会也改牌成了居委会。除了医疗保险,村里的老人并不是很看重他们曾艳羡不已的居民户口,而年轻人大多是为了谋得一份工作。根据拆迁协议,一部分年轻村民进入了小区的物业公司,每月拿着七八百元的工资,一部分选择自己创业,而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过着像张富国一样悠闲的生活,“每月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房租收入足够他们衣食无忧,他们觉得没必要再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杨会新解释说:“另外,他们也无力承受在城市打工所要面对的激烈竞争和外面对文化素质、工作技能的要求。”但令杨会新颇为头疼的是,一些曾选择待业在家的年轻人最近又陆陆续续地开始闹着让村里给安排工作,因为“年轻轻在家闲着的日子太难熬了”。 守着日渐升值的地段,东村人享受着他们迟来的幸福生活。谈起幸福生活得来的原因,有人说是政策好,有人称赞是“年轻的领导班子开创了东村新的历史”,有人觉得是那座保留下来的正午庙护佑了东村的喜乐平安,但这样的反思大多只在瞬间,更多的时候,他们在乐此不疲地挖掘生活中更多的幸福。 这样的挖掘过程形成了东村独特的现象:年轻人因幸福驻足,老人因幸福忙碌。 蒋家坟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本刊记者/吕娟 李云虹 2006年1月19日上午10点多,临近春节,零下13度的严寒显然没有逼退北京市丰台区郑常庄乡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的人群。一簇簇的人从车站边一个不断传出吆喝、叫卖声的小巷走出,缩着脖子,捂着耳朵,紧锁着眉头低声咒骂着突袭的冷空气,将至的新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的脸上增添多少喜气与清爽。 巷内的蒋家坟村是我们这天采访的重点。一条一里多长的中心街道“有商户355家,其中90多家无营业执照,违法棚、亭、阁299处”,这是我们之前从网络上查找到的关于它的信息。2006年北京市计划重点整治城八区五十多个城中村,蒋家坟并不在其中,但是北京市社科院一份调研报告却指出,这里是北京市丰台区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角落”,聚集着16000多人的外地打工者,超过当地居民与村民总和的5倍,一位通过考大学离开该村的年轻人嫌恶地形容自己的家乡是深藏在北京城里的一块难以治愈的“癞疮”。 被遗忘的食租者 尽管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真实的蒋家坟仍旧出乎我们的意料。 通往蒋家坟的主街道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街道,最窄的地方仅一米多宽,一辆三轮车能造成这里通行的滞塞。街道两边拥挤着数不清的小商铺,五金、百货、小餐馆、美发店,更多的是蹬着三轮叫卖的游商。为了招揽生意,店主们大多将货物架搬到路边,时不时对着来往的人群慵懒地吆喝几嗓子。走过的行人肆无忌惮地朝路边吐口浓痰,恰好落在摆满热腾腾蒸笼的包子铺前,老板不以为忤地瞄了一眼,继续她的叫卖。 空气中充斥着呛鼻的味道,几名路过公厕的男女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匆匆跑过,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公厕旁几米处的烤肉摊前,几个操着外地口音的青年举着手中的烤串大快朵颐。 行至一里左右,一块立在巷口拐角处的锈迹斑驳的铁皮牌子告诉我们,蒋家坟到了。 对于初来乍到者,蒋家坟更像一个破败的迷宫。狭窄的胡同无规律地向不同方向曲折延伸着,看似到了一个死口,却又魔术般从一侧长出条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幼臂”。破旧的四合院“争先恐后”地向路界扩张,简陋违章的小门脸挣扎着从墙体间挤出。路面上污迹斑斑,随处可见的菜叶、垃圾甚至粪便,污水肆无忌惮地从两边房屋的下水管中流向路面,在低洼的地方蓄成肮脏的水坑,又立刻结上一层薄冰。 虽是半上午,胡同里来往行走的人却很多,操着天南地北的方言。画着浓妆,穿着短裙的年轻女孩,抹着厚重发蜡,西装革履行色匆匆的南方男人,巷角补鞋的鞋匠,穿着棉睡衣光脚趿着拖鞋在胡同里闲逛的妇女,还有坐在门前小凳上,用漠然而浑浊的双眼巡视来往人群的老人。 沿路打听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是当地村民,一个一手端着盆洗头水,一手撸着滴水的头发的女人正从院内走出,慢条斯理地询问我们是不是找房东,随后不等我们回答,重重地叩了几下院旁的铁皮门。半晌,一个中年妇女打开门,用惺忪的睡眼打量我们,问想租什么样的房,得知是记者,她摆摆手,二话不说关上了房门。 一个好心的外地人告诉我们,当地的村民更喜欢别人叫他们房东,因为他们大多以出租房屋为生,相比房客,他们更愿意在这个季节呆在家里。 走进杨大妈的小院时,她刚送走一个看房客。院子的过道两边各加盖了四间出租房,院子搭了顶,变成正屋,却没有暖气。知道我们是记者,她两手往袖口里一揣,深陷的颊窝牵出嘲讽的冷笑,鼻子里挤出一声哼,“你能帮我们说实话吗?”随后转身撩起门帘进了里屋,但并没有阻止我们跟入。 虽是白天,屋里却漆黑一片,“停电了”,杨大妈说,“这是常事。” 虽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但杨大妈的话语却因愤懑而零乱,几番交流,我们终于拼凑出她的故事。 杨大妈四十年前嫁到蒋家坟,那时全村以种蔬菜大棚为业,够吃够喝。1992年蒋家坟农地被开发商占用,全村人失了地,没了收入。按照政策,她和74岁的老伴转了居民户口,每月拿340元的退休费,患尿毒症的老伴每年光医药费就得七八万,而转居后的医疗保险才能报销30%,生活入不敷出,全村人开始逐渐在自家院里院外加盖几间房出租给外地人,赚取租金成了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开发商要拆迁的风声时不时地传出,届时只给每家按面积每平米补偿三千多元,不得回迁。年轻人面临两种选择,要不领5万元的遣散费,要不接受安置在开发商公司做保洁等工作,每月几百元工资,但这样的工作也没维持几年,现在80%的村民都赋闲在家。 “要我们活就活,要我们死就死”,杨大妈斜倚在墙边,恨恨地反复重复这句话。“你们替我们反映反映,真拆了,我们住哪儿去?在这儿破平房里,捡点柴火烧锅菜粥窝头还能活,楼房却是买得起住不起,哪来的钱养它呢?” 赤脚律师 据杨大妈说,村里部分人转成居民后,形成现在的农居混杂,村东头是居委会,村西头是大队,两套班子,双重管理。 蒋家坟的居委会是间路边的平房。正伸手在炉边烤火的工作人员张爱英(化名)听说我们是记者,立刻站起身要带我们“去看蒋家坟真实的情况”,脸上的表情似乎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 张爱英走路很快,一路带着我们穿过堆满垃圾、污水横流的几条小巷,边走边比划“这儿,这儿,还有那儿,以前干净着呢,种地回来街上胡同里整整齐齐,早晚有人打扫,现在你看,这还是正常的生活吗?” 张爱英带我们来到她家,一个临时搭建的小阁楼,在破木板搭成的楼梯拐角,她停下来,指着楼下堆满垃圾的荒地,“这以前都是菜地,开发商占了以后,常年荒着不开发,要不租给废品收购站,全村光这样的废品站有十多个,都是在居住区,从早到晚叮呤哐啷,白天黑夜地烧着电线、胶皮、塑料,空气污染严重极了。”随后她指着楼下来往的行人,“外地人比本地人还多,收废品捡破烂的,收不着就偷,抢,看你家炖肉他连锅端,现在谁家不丢个东西那叫不正常。” 走进屋内,张爱英指着沙发上坐着的一个中年妇女,“你们采访她吧,因为拆房,她都喝敌敌畏了。” 这个女人叫周夏菊(化名),41岁,魏家村人,张爱英的中学同学。魏家村与蒋家坟两村紧挨,过去同属一个大队管理。2002年10月25日,开发商在魏家村贴出拆迁的公告,每平米补偿3150元。到目前,全村只剩周夏菊和其他5户没有搬,因为“开发商拆迁手续不合法”,周夏菊解释说,这几年她一直跟开发商对抗,“他们雇人到我家砸门、泼粪、扔大爆竹,想逼走我,可我走了就没有活路,他们不准魏家村人回迁,要回来就按每平米8500块钱买,谁买得起?” 周夏菊说虽没搬,但自家现在已没法住人,三天两头停水,电压最高时只有150伏,“电器基本都烧坏了”,无奈,只能在老同学家暂住。 谈话间,一个戴着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进入,张爱英介绍说,这是他的丈夫李维德(化名)。 李维德还有一个身份,被拆迁农户的诉讼代理人,“我没考过律师本,可我敢替老百姓说话”,他走进里屋,从布帘里探出头,“他们都叫我赤脚律师”,随后,他抱出一摞一尺多厚的材料。 “这都是我拿命换来的”,李维德指着材料,“谁拿着它明天就能成富翁。” 他摊开材料,“看到没有,从拆迁批文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全是造假。” 李维德说这些材料是开发商的“罪证”。他曾去过北京市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查档,根据规划局的档案显示,蒋家坟与魏家村所在的青塔除了1999年因市政道路建设被国家征用24.27亩的农地外,至今都没有再被列入市政规划。按照法律,因公共建设征用基本农田超过35公顷的,必须由国务院批准,而蒋家坟与魏家村53公顷的粮田与宅基地却被开发商轻易地占用开发商业楼盘。“你看”,他指着手中的资料,“他们把我们的农地宅基地改成了‘其他’,更荒谬的是明明拆的是西区的魏村,提供的却是东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甚至连这个证都是假的,”李维德指着落款,“连章都没有盖。” 虽然握着这些证据,李维德代理的这起行政官司一审却打输了,二审的判决等了一年多仍没有音信。“我没输在‘理’上,而是输在‘世’上”,他的语调转为激愤,“明明知道是蚂蚁扳大树,我就是要抱打不平”,他再次拿起那些材料,“我没什么文化,可现在所有北京市拆迁方面的证件,拿出来我就能看出是真是假,老百姓都认我。”随后他神秘地一笑,“你知道开发商给我起了个什么外号吗——拆迁的搅屎棍!”他抬高声音,语气里透出得意。 李维德说他为代理魏家村拆迁的官司付出了很大代价,“开发商派人砸了我家的八间房,所以现在才搬到这个小阁楼。”两年前的一天,一群人冲到李维德家寻衅,“幸亏我们有这个”,李维德从抽屉里掏出一把灭火气枪,“六米之内能把人喷倒,但不伤人”,“这里家家户户都备着这个。”即便如此,李维德仍受了伤,他撩起衣服,让我们看他的伤口,露出了腰间缠的一条红色的腰带。 “我们卢沟桥公社以前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李维德感慨,“地理位置相当好,那时人都挤破头来这儿,谁想到现在变成这样呢?” “这些你们都能报吗?”他笑着反问记者,带着一丝挑衅,但随后又坐在椅子上,一段难得的沉默后,他抬起头,“尽量给我们反映反映吧”,他的语气转为低落,“现在这里的人生活水平大不如以前了,大家都害怕,魏家村的今天就是蒋家坟的明天啊。” 相关专题:法律与生活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法律与生活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