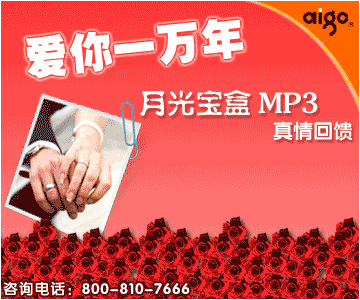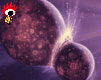| 巴黎喷泉:溢自我心深处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12日14:09 新民周刊 | |||||||||
|
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喷泉的鲜活 那是一个傍晚,我从拉丁区雷勒街的艺术电影院“丑角影院”看完电影走出来。
天气很好,太阳已经被甩到一丛丛米黄色楼房的后面。天将黑未黑,它的色彩正从淡蓝向瓦蓝过渡,这个过渡的中间 过程是非常让人迷醉的。所有的东西都显出清楚的轮廓,但细看又都已开始朦胧。一弯细细的新月斜挂在天的一角,淡淡的, 就像水笔轻轻地勾了一下。 生命中能站在这样的天空下的时间并不多,因为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拖你下到它那浑浊的水中,那是个永无止境的诱惑 。何况在时间范围内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有的美丽都只是某个中间过程。每到这种时日交变的时辰,甘斯布的那句唱词就会 在我耳边响起:“我过来跟你说,我走了。你想起旧日时光,你哭了。” 我没有朝回家的方向走,而是过了马路顺着老鸽舍街,向圣叙尔皮斯广场走去。没有走多远,就听到了水声。这是现 代都市唯一还能向路人提供的美妙声音。圣叙尔皮斯广场上“布道者泉”的水声,穿越人声和车声,招魂一样地拉我过去。作 家圣·埃克絮佩里让他的小说主人公小王子说过一句话:“如果我有53分钟的时间可以支配,我就静静地走向一个喷泉。” “布道者泉”单从雕塑讲,并非最美的,它是19世纪雕塑家维斯康蒂的作品,且有“抄袭”巴黎另一泉“无辜者泉 ”之处。而“无辜者泉”是16世纪让·古荣的作品。相比来讲,以水仙女作饰的“无辜者泉”要比以雄狮作饰的“布道者泉 ”来得优雅。但后者另有一种气势,到掌灯时分就显出来了。 雕塑中只有喷泉雕塑,不管历经多少时代,永远都给人鲜活的感觉。这是流动与凝固的绝妙配合。 其实,有时并不需要这样的雕塑和水力,泉本身便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记得在戛纳,离开海滨大道的浮华,走到老城 区。顺老街向上走,穿过小餐馆、旅游商品店,就遇到了拐角处的一眼喷泉。一棵树,一条依墙而设的石凳,一个没有多余装 饰的石槽承接着细细的水柱。我总喜欢去坐一坐,哪怕是在正午当头的阳光下,这里也有一种仿佛隔世的清凉。我望着一圈圈 变大的水纹,耳边会荡起那句法语歌词“我望着那永远达不到沙丘的海浪”。 好多年前,我从蓬皮杜文化中心出来,向市政府广场走,经过圣·麦瑞教堂时,发现了伊格尔·司塔文斯基广场上的 那个喷泉。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一座现代雕塑的魅力。在几乎覆盖整个小广场的水池里,从红唇到乐符,所有奇形怪状的东西都在 动,将这一切不和谐和谐到一起的是水!这是20世纪80年代让·丹格利和尼基·德·圣法尔的作品。 这里与上述的“无辜者泉”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但两个泉之间却隔了五百多年的历史。没必要大发对时间的感慨,走 一走这五分钟的路程,听一听几乎是同样的水声,便知道一年、一个世纪和永远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后来我每次走过伊 格尔·司塔文斯基喷泉,都会想到奥匈帝国皇后希茜的一句话:“疯狂比生活本身更真实。” 约会之角 就在大王宫后面,还有一眼听名字就令人遐想的喷泉:“诗人的梦想”。无论什么时候走到那里都是安静的,与几十 米之遥的香榭丽舍大街宛若两个世界。这泉是献给写过《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的作家缪塞的。缪塞留下过两句有关喷泉的诗: “为什么看到那泉上颤抖着的和风之吻,我无法无动于衷?” 我称这里是“约会之角”,喷泉雕塑背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水塘,完全掩在绿阴里,时常是没有一个人。只有水从石块 上滚下来,敲击另一片水的声音。这时候,所有的语言都在死去。我会突发奇想:下一个约会是谁?是死亡吗? 诗人里尔克说:“人们来到这里为了活下去或者不如说为了死去。” 卢森堡公园里的“梅迪奇喷泉”好像就是为了吻合这句诗而建的。 喷泉本身是17世纪亨利四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让人建造的,19世纪中叶又进行了改造,增加了一个长约5 0米的长方形水池,以及水池尽头的那座雕塑。 这是一座给人奇特感觉的喷泉,四周长满百年以上的悬铃木,将阳光完全遮住,水发出幽暗的绿色。从池子尽头向喷 泉方向看去,水像镜子一样煞平,好像随时在逃避你的眼光。只有池中的落叶让你从虚幻中回到现实。雕塑是奥古斯特·奥丹 的作品,希腊悲剧中的三个人物:独眼巨人波利菲姆正试图谋害夺走他恋人的牧羊人阿西斯,而阿西斯全然不知地正拥吻着引 起妒火的情人加拉苔。 由白色大理石雕塑的两个恋人,让时间之足停了下来,生与死在这四目对视中仿佛没有距离。诗人普雷维尔写过: “喷泉之水唱出的歌,早就比我说得更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也从来没有忘记你。” 城雕里的政治 在巴黎或者外省的小城,这种可以静静地坐下去,任由时间之水流淌的地方,并不止这一些。 我以为巴黎的灵性就在它大大小小的两百多处喷泉。这是它无以数计的城雕作品中,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部分。我把 巴黎的城雕分为两大类:喷泉和非喷泉类。两者都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就是几个世纪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积累与淘汰。前者 完成了一个从实用到美学的过渡;后者则在20世纪之前几乎清一色是权力——宗教的和政治的——征服的象征。相比之下, 我偏爱前者是不足为奇的。 1900年之前的非喷泉类雕塑,很少是没有政治寓意的。不是国王骑在高头大马上,就是共和女神硕壮的铜身或石 身,再就是所有的战争胜利者。还有无所不在的国魂的泛泛代表圣女贞德的塑像。凯旋门和胜利柱更是极权的体现,拿破仑时 代建得最多。 到了19世纪后半叶,又被另一种好大喜功取代。这一时期的欧洲竞相举办世博会,以显示其“强大”、“富有”。 城市建筑追求高大奢华,大量的城雕随着城市扩建和改建像春笋般竖立在大大小小的广场上。从拿破仑时代的后古典主义雕塑 ,到罗丹的写实,以处于两者之间创作“自由女神像”的巴多尔蒂最具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这个时期的城雕追求“高、大、美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巴黎城雕是19世纪这一百年里创作的。 这一历史时期的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炫耀”。显示“强大”、“富裕”,要比市民阶层实际能得到的福祉重要得 多。一个城市也有新贵暴富的心理。 巴黎城的美化早在17世纪便被正式提出,从那时起巴黎开始了从中世纪古城向大都市的发展。城市雕塑的最初出现 ,为国王歌功颂德的成分远远大于美化城市。1792年大革命期间,国王们的塑像,全部被砸掉。到王朝复辟时,又被一一 重建。但仅仅是重建而已,新国王们已变得聪明了,没有再为自己塑像。 但后来的城雕却并没有脱离共和派与王朝派斗争这条线。到了巴黎公社时期,文化保护观念已经出现,所以公社社员 在摧毁旺多姆广场拿破仑建的胜利柱时,没有将拆下来的浮雕和塑像送进熔化炉,而是送进了博物馆。1871年共和体制彻 底确立后,没有再砸国王的塑像,而是大塑共和女神的塑像。这场斗争白热化的表现便是巴黎城两个最显眼的建筑。1871 年后为了重塑教会的权力,在巴黎北边的山丘上建了圣心教堂,因为地势高,这个教堂在巴黎到处都能望见。共和派也不示弱 ,利用世博会设计了巴黎铁塔,更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城市雕塑的政治斗争才基本平息下来。最后一次摧毁城 雕作品发生在二战期间,比如如今立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的丹东塑像,二战时被送进了熔炼炉,二战后又重塑了一座。不过在这 以后,左右派的斗争也并未结束,左派上台为左派人物塑像,右派上台必反其道而行之。 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再度繁荣的六七十年代,城市的暴富心理比一个世纪前已淡了很多,都市基本没有被卷 入摩天大楼的“竞高热”中。而是更注重人性的伸张,讲究实际和舒适,这一时期的城雕已以其文化特征取代了政治特征。人 的生存质量超出了城市所要对外显示的东西。 20世纪后半叶,巴黎出现了现代城雕,但在城中心,选择非常谨慎。永久固定的雕塑地段和形式的选择慎之又慎。 多数现代雕塑是临时性的。现代雕塑的审美是非常个人化的,一旦固定下来,就有强迫所有人接受这种审美之嫌。如果是固定 的,19世纪“高、大、美”这样的概念已经被抛弃,除去纪念意义,也就是继续为名人塑像外,让每一件雕塑融入环境,取 其巧,是新的理念。 旧雕塑已经作为历史留下来,它们曾经具有的政治含义,业已淡去,就好像是被时间冲刷掉一样。剩下的只是形式的 美与不美。没有多少人说得上国家广场上那个体态丰美的女人是共和理想的体现;当费尔·罗什罗广场那巨大的铜狮子是人民 反抗侵略的象征;旺多姆广场上1871年后又重建的胜利柱是拿破仑侵略战争的纪念碑;波邦宫广场上那个正经危坐的女人 是司法的代表。 溢自我心深处 城市雕塑从权力的喉舌过渡到个人的情感,经历了一个多么漫长、甚或充满血腥的演变过程。 要说我心目中理想的现代城雕,其实很简单,就是那种给我意外惊喜的设计,并不张扬,没有什么“主义”要伸张, 耐看足矣。把它们放在某个街心三角地或公园的一隅,便让人觉得应该在那里,只能在那里。 我在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附近的一个十字街口,第一次看到那个名为“穿墙过壁的人”的雕塑,着实为之叫绝。雕塑 所在的位置是名为马赛尔·艾梅的街心小广场。作家艾梅的故居就在广场边,雕塑是根据他的一篇同名短篇小说设计的,19 89年完成。小说主人公迪蒂耶尔在最后一次穿墙时,特异功能失灵,被永远凝固在墙壁上。这是个住在蒙马特高地窝囊到连 老婆也没有娶上的小人物,某天突然发现自己有穿墙过壁的功能,生命观为之大变,从此不再唯唯诺诺。可惜奇迹只能是奇迹 ,当你加以利用时,它便消失了。 这个雕塑与整个十字街口的建筑融为一体。它不是多余的,就怕是多余的。 那天我站在这个小广场上,想到那个诅咒世界的哲学家西奥朗有句话放到这里很合适:“只要我们继续想象我们的故 事,我们便会继续存在下去。” 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自己时常会在去卢森堡公园的途中,在那个街角停一停。那是拉丁 区瓦万街和布雷亚街交汇形成的一块三角地,几棵树下,一个老式挂钟,一盏旧式街灯,一个漆成绿色的铁制小喷泉。这种小 喷泉在巴黎随处可见,比落地邮筒略高一些,一柱细水从顶盖上垂落下来,供行人饮用。19世纪英国慈善家理查·华莱士捐 款为他喜爱的巴黎建了一百多个这样的小喷泉。 我喜欢这种绿色身体的小喷泉,因为它们总在人不经意的时候出现,丝毫不强迫你的视觉。我在三角地的长椅上坐一 坐,轻轻的水声会一点点穿透城市的噪音,流过来,流过来……片刻间,时间从我的生命中脱开去,就像并行的两条铁轨。 阿拉贡说:“我要求每人都有将焦虑的面庞俯向喷泉之镜的权利。” 我也在这个时候,更理解了泰戈尔的那句诗:“喷泉溢自我心深处……”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