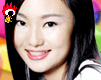杀青时 我狠狠地抽了一支烟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0日10:39 时代人物周报 | ||||||||
|
本报记者韩雨亭 陆川,现年32岁,一个彻头彻尾的电影理想主义者。剧组的权威与核心,不仅负责电影的艺术生产,还要照顾与调 动剧组成员的生活、情绪等问题。每一天剧组出发,他都会准时在车上放一盘许巍的带子,其中的一首《完美生活》经过他的 强力推荐后,几乎成为了《可可西里》的“剧组之歌”。
陆川很少批评演员,对于表现不好的,他通常用沉默和失望的眼神来表示不满。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个操蛋的人, 对于自己的工作伙伴,如果我察觉他们没有能力去做事,或者工作态度不好,我就会特别愤怒,觉得他们是废物,甚至连朋友 都没得做。” 电影收工后刚回北京的一个月里,陆川的手都不能握紧东西,有时候写文章老抓不住笔。同时,他开始觉得自己在这 个大都市里找不着北了,有点恐慌。每次去书店,他都感到很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并非来自对知识的恐慌与压迫感,而是开始 质疑那些写书的人。陆川说:“我去可可西里,不是一个城市人去荒漠猎奇,而是觉得自己像盐巴一样掉到水中,立即与那个 环境融为一体,那种感觉远比都市舒服。” 时代人物周报:当你真正走到现实环境中去拍摄《可可西里》时,是不是与开始的构思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甚至是 冲突呢? 陆川:的确有很大的改变与冲突,原来的《可可西里》无论从故事结构还是情节上,都显得更甜一些。也就是说,更 加注重于歌颂好人好事,在构思上甚至都有点像孔繁森。但后来,当我们这群人走入可可西里去捕捉这些线索时,却发现它无 论在现实情景还是逻辑推理上,都与我所构思的有很大出入,甚至发生了很多方面的冲突,这都是我始料未及的。现实比我们 预料和想象的更加深刻,更加无情,也更加惨烈。 时代人物周报:在电影正式投入拍摄之前,你去过几次可可西里? 陆川:两次。 时代人物周报:这两次是启发了你进一步深入的欲望?还是因为与你预料的不一样,而感到失望? 陆川:失望倒没有,但是我认为拍电影本来就是一件“苦差”。比如可可西里那些在我脑海中的传奇和概念性的东西 ,都在现实中被击碎了。但是既然电影马上就要开拍,我所能做的是进一步删除、改进与完善它。到了可可西里之后,我一直 在问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那里的人们与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些答案到现在我都未能找到。 当拍摄更深入了,而我们也必须面对可可西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时,我没有一刻停止过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比如,我为 什么要这样过?为什么要选择导演这个职业?我想那未必仅仅凭热爱吧。绝对有另一只手在推动着你,去干每一件事与做每一 个决定。在一种莫名的力量面前,如果我非说我是因为太热爱导演这一行当而走到今天的,那绝对是没有经过现实考验的一句 话。 时代人物周报:听起来的确有点玄乎,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与你此次可可西里之行有很大的关系?或者更细 一点说,与出车祸和人命有很大关系? 陆川:对,有很大的关系。但就电影的风格来说,可能内涵比这些事情更为复杂。当我去了可可西里之后,发现现实 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我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但《可可西里》本身没有过多的复杂推理,它的线索很单 一,其实就是旅行,而在旅程中,不断有人倒下。 时代人物周报:其实,《可可西里》剧组也与这部电影一样,经历了同样严峻的考验。 陆川:对,剧组一共走了3000多公里,换了四个主要的拍摄场地。其中最艰苦的是在“五道梁”,当地人俗称“ 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它与青藏铁路很近,一般只有巡山队员与修路工人出没,所以特别宁静。我都觉得,我们的到来 破坏了那里的安详与可怜的植被。但是,那里的环境太过于恶劣了,就连经常去那里的司机都感到头痛欲裂,更别说我们这些 内地去的。剧组一共在那里住了20天,我一共瘦了20斤。上山的时候,大家的脸都肿得发胖;下来的时候,又都瘦得像只 猴子,一摸都是骨头。 时代人物周报:的确,挺难得的一次经历。电影收工后,你的情绪怎样? 陆川:拍完那天,大家都如释重负。有的拿枪玩射击,有的装子弹。但我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可能比较麻木了,我 狠狠地抽了一支烟。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时代人物周报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