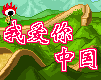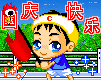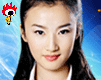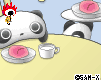洛蒂的北京之行(下篇)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2日20:01 新民周刊 |
 罗什福尔城洛蒂故居门口,从外面看是很平常的民居  皮埃尔·洛蒂当年在他的土耳其宫的留影 东方旧梦 我的旅行终于在下午到了目的地,西南夏朗特河边的罗什福尔。顺着这条河再往西走一点,就是大西洋。洛蒂当年从天津到北京走了好几天,在我则是几倍的距离几分之一的时间,现代化已经让人失去了耐心。这个昔日相当繁荣的军港,已归于平静,再没有什么东西来激荡这个外省的小城生活,它像许多外省小城一样让人感到平静之下的衰落,以及极度 文明之下的生命力之贫乏。全都是这样,没有了野蛮人的大悲大喜,也就少了活力。洛蒂走进北京城的时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抵达前半小时,他走在一片荒漠中,开始怀疑这个传说中的城市是否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同伴跟他说:“北京城不会让你一点点望到,而是一把抓住你。”当有人叫道:“北京!”他写道:“在几秒钟内,一堵黑色、巨大的城墙,以我从未见过的高度,出现在眼前……北京的城墙高高地压在我们头上,像一个巴比伦的庞然大物,在秋日一个下雪的早晨幽暗的光线下,显得黑森森的……城郊没有一个路人,空空如也。墙边地下也没有一根草,土地呈现一条条细沟,灰尘累累,就像一片灰烬,伴着东一处西一处的破衣、碎骨,还有一颗人头,显得阴森可怖。”这一天是1900年10月18日,一个星期四。想想我们这些一百年后的人再也无缘看到那个“巴比伦的庞然大物”,华北平原上的一道奇景在一场革命后的狂热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这在历史长河中永远没有声音的叹息:没有人珍惜已经到手的东西。 几乎是整整104年后,我看到了罗什福尔城边那一块旧城墙拆剩下的石头,城市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从标志着旧城入口的那尊一战英雄纪念碑,走到市中心广场,只要几分钟的时间。我明白洛蒂在北京城门前的感觉了,这的确是两个世界。市中心广场上照例是喷泉、咖啡座,在这个阴雨的8月,并没有多少游客。巴黎任何一个小广场都可以移植到这里。安宁,甚至有些暮气。一切都是根据人的需要不多不少地配建的,与什么都大得令人压抑的北京城比,这里是个“迷你”世界。马路基本保持了一百年前的宽窄,没有一扇临街的大门、没有一条马路,像今天北京城里的机关大门和大马路那样宽大到反人性的地步。城市的色彩调到最单调的几种,红、蓝瓦顶,一色白的墙面。没有极度奢华与贫穷的反差,除了教堂没有炫耀财富或想象的建筑。没有晾晒出的色彩斑斓的衣服,没有厨房飘出的饭菜香,私生活被牢牢封在四墙之内,这是西方与东方的界线之一,是它在与东方接触后,为自己订的一条规则。一句最简单的话,就把两个世界截然分开了:“东方人生活在街上!”洛蒂初进北京一路看到的都是死尸废墟,10月19日那天他去天坛,走着走着看到了另一番景象,他写道:“这个我们至今以为只是一座巨大公墓的北京城,意想不到地呈现出镀金流彩,以及千形万状竖向天空的怪兽。喧闹的声音突然袭过来,有乐声有人声。这样的生活,这种纷乱嘈杂,整个这种中国式的浮华,在我们都是难以想象和不可捉摸的!在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沿着这个科尔贝广场右手的一条街,也算是本城一条大街,但也就和北京的胡同一样宽窄,走不多远,141号就是洛蒂的故居了。街名原先叫圣皮埃尔,洛蒂出名后,改为皮埃尔·洛蒂街。 在141号门口,你完全想象不到你会在里面发现什么。小城全都是略带罗马建筑风格的二、三层小楼,141号也不例外。很一般的楼门,与普通住家没什么两样。1901年4月26日,洛蒂二进京时,做了一次去清陵的旅行,这一天,他在傍晚走近涞州县(译音,估计是今天的涞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远远看去,这个处在一片平原之中的古老城市,以它带雉堞的高高城墙,几乎可以说是雄伟的;走近了看,它肯定又是衰老破败,就像整个中国。”这是所有带着神秘梦想而来的西方人在深入中国后的反应。但愿我下面看到的不是这样一种反差。 里面远比我想象的热闹,不预约根本参观不上。想想扔在旧书摊上的这本《在北京最后的日子》,看看排队看故居的人,看来“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这话应验了,果真是抵抗遗忘的又一招。幸亏遇上故居博物馆一位热情的公关小姐,才解决了没有预约的麻烦。并且因为是中国人,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小小特权,看到了那间已不对外开放并且也大半消失的中国厅。 据说洛蒂这个人是一个矛盾体,呆在家里便只想远游,走到外面又只想着回家。于是他用了几乎半生来调和这一矛盾,具体的做法便是把祖居和后来买下的隔壁的房子,一点点改造成凝固的旅游匣子。这个庞大的工程从1877年开始,陆陆续续到1903年完工。中国厅便是最后完成的一个东方梦,显然是为他的北京之行而作。该年5月11日,他为中国厅的揭幕办了一个盛大的中国节,请了一百多人,来宾全都扮成中国清代的绅士淑女。据当时的描写,这个厅金碧辉煌,完全模仿中国宫殿内部装饰的风格。1900年10月24日,住进团城镜澜亭的洛蒂,在鸦片的迷醉下,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深地理解中国艺术,似乎真的就是在这个晚上,它向我们昭示了它的魅力。”那么这个中国厅是不是就是那个夜晚那种魅力的一种延伸,或者说一种试图的延伸? 我跟着导游绕到后花园一个僻静小庭院,小庭院入口的石门后面,是一扇影壁似的中式石牌楼,上写“龙马精神”几个中文字。从刚才小城中心广场这么一路走过来,绝想不到在这个民居深处会有这样一件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东西,忽然就明白了洛蒂的人格特点:永远的异乡人。小小的庭院已经荒落,这里永久的过客是鸽子。隔壁主楼里的人声完全被高墙阻断,让我们依稀还能捡拾几把洛蒂的东方旧梦。 中国厅那扇几乎锈住的门终于打开了。出现在眼前的只是当年中国厅的一角,大半部分被幕布隔在了另一边,那是已经不存在的一边。长久没有人进来了,有一种雨季淡淡的霉味。从粗大的红色厅柱,到金龙雕顶,从房间尽头那尊坐佛,到入口处珍藏的几双女式绣花鞋,你大略能感到当年那次异国情调的延伸走了多远。我在几双绣花鞋里辨认,究竟哪一双是他书里所说的从慈禧凤床下找到的红色绣花鞋。没人能回答我,这也许又是洛蒂式的模糊现实与梦想的一招,他一生都在从事着这个职业。 这间带点霉味的小半个中国厅,简直就像清朝的遗梦,被那股征服的狂潮,甩到这么远的一个角落里。我由此想到任何一种征服,都同时是一种被征服,角度不同,方法不同而已。那天洛蒂在天坛登高远眺,望着西面一望无际的灰色原野上的骆驼队,发过这样一番感慨:“这个与我们不同的种族,有着顽强和超人的耐心,让我们惊恐万状的时间的步伐,对他们是不存在的……这四到五亿颗大脑的所思所想沿着与我们完全相反的轨道,而我们永远都破解不了……” 出来时下起了小雨,站在主楼边的一个小阳台上等待去参观剩下的“阿里巴巴宫”时,想到洛蒂去清陵的路上在涞州县夜宿县官家里写的那段话:“我真不知身在何处,感到与我那个世界彻底分开了,中间是广袤的空间、时间和岁月;我好像觉得就要在一个比我们至少落后千年的人类社会中,沉入梦乡。”进城时看到的挂在城门口的人头,不可能让他还有别的什么想法。而第二天在易州(译音,估计就是今天的易县)县官招待他的酒宴上,菜上个不停,一道又一道(只这一点,东西方的界河便是难以逾越的)。一个当地的饱学之士在饭桌上问他:“中华帝国占据着地球的顶端,而欧洲艰难地斜挂在它的侧边,对不对?”没有比在法国外省小城洛蒂故居的阳台上,测到当年两个世界的距离,更奇妙的了。那互相投出的目光,擦边而过,不知落向了哪里。 半个小时以后,走出“阿里巴巴宫”,为一个人可以如此占尽各种文明的风光而震慑。这的确是这位旅行作家的最后杰作。在小小的有限空间内,居然集中了中世纪古堡、土耳其宫殿、清真寺等多种文明的结晶。现在就要看,再过一百年,是文字还是这房子更能经受时间的冲刷。据说,洛蒂死前对儿子说,要把这些全部毁掉,儿子没有听。这是洛蒂意识到这房子日后会冲淡人们对他文字的记忆?还是他为水手作家传奇人生设的又一迷障?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他生前怎么改造,“阿里巴巴宫”最终也没有成为梦乡,而只是一个港口,他在1892年的日记中记道:“我昨天早上刚回来,午夜,呆在罗什福尔这幢老房子里,坟墓一般的寂静……真想马上走掉,整幢房子都让我感觉阴郁和忧伤……”他不断要走向东方寻找野蛮人的声音、气味和色彩。洛蒂的矛盾心态很能涵盖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那种处在征服与被征服间的心理失衡。 征服者的忧虑 告别罗什福尔,奔向本次行程的终点,洛蒂最后埋身的奥雷龙岛。罗什福尔西南十几公里处的一个小岛,都不用乘船,有跨海大桥。刚才的“阿里巴巴宫”是洛蒂搞的一怪,下面的葬身地,是洛蒂搞的另一怪。作家墓地在法国往往是生命的最后一景。所以公布地点又谢绝参观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洛蒂算是首例。他为此葬在他姨妈家的花园里。 我在傍晚来到奥雷龙岛的圣皮埃尔镇,天已经放晴,只有海边才有的那种特别明亮的斜阳,打在也叫洛蒂街的半边墙上。19号是一扇漆得碧绿的乡居木门,在残旧的小街和湛蓝的天空配映下,很有点特别。街对面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家招牌挂得很高的“洛蒂比萨店”,小地方住过一个名人往往都要百分之百地加以利用,因此什么样的“洛蒂”招牌都有。正是7点多钟,玩了一天海的人陆陆续续在返家,街上远远谈不上安静。洛蒂大概绝想不到,身后80年的社会进步,不但孤岛与大陆有一桥相连,而且小岛也已成为夏季旅游热点。19号门口有一块相当醒目的石牌,上写皮埃尔·洛蒂安息在花园的常春藤和月桂树下。门铃上方还有一块小牌子,告诉想来按门铃的人:根据洛蒂遗愿,墓地谢绝参观。 我事先知道,也就算不上白来。这位生前使出浑身解数引人注目的人,身后却用一道围墙将好奇者拦在了外面。在书中,他一直在感叹北京的各种各样围墙,“难以穿越”这个词始终挂在嘴边。看来,他在生命的终点,实践了这个东方的传统。1901年4月28日这天,洛蒂站在清陵墓前,写道:“等到联军撤出中国,这个对欧洲人开放过一阵的陵园,又会变得难以穿越,时间又会持续多久,很难说,也许到下一次入侵,那时候这个古老的黄种巨人就该彻底坍塌了……除非他从他的千年梦中醒过来……最终拿起武器,我们真不敢去想他的报复……天哪,等到中国群起而做最后反抗的那一天……手头又有我们的现代化毁灭性武器,那将是一支多么可怕的军队!何况我们的部分联军的确在这里不谨慎地撒下了太多仇恨的种子和报复的渴望……”站在这扇绿色的木门前,真想把他唤醒,轻轻告诉他:“洛蒂,这个噩梦还要再做一百年吗?我不是来报复的。” 沿着圣皮埃尔镇的细街,向大西洋走去,是看落日的时间。5月4日是洛蒂在北京最后的日子,团城的晚会结束后,他踩着宫殿发出清脆声响的石板往住处走,在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庄严的寂静中,忧愁袭上身来。“这个晚会好像以不可挽回的方式,为北京的沉落添上了最后一笔,或者不如说是一个世界的沉落……它的神秘被揭开,它的魔力被打破……这是地球上未知与神奇最后的避难所之一,古老人类最后的剧场……”10年之后,清朝被推翻。西方的征服使多少文明从原先的轨道上脱开,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滑过去。这些文明从此像困兽一样,东奔西突,寻找出路。偌大的世界从此不再可能各人按各人的节奏,广袤的疆域被收网一样地缩小,直到100年后思想几乎被完全同化的地球村的实现。在人类文明那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喧闹的峡谷间,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争斗并没有停息,我即使躲到这个小岛上,还能听到那征服的脚步,在历史空谷间回荡。 站在岛尖上,望着落日掉入水中,那么快,顷刻间,天上水面便只剩下没有一起带走的红霞。由洛蒂的叹息,我想到朋友D的一次经历。我们那时在西藏旅行,与一帮人去玩枪。在打空瓶和打野免之间,我选择了前者,他选择了后者。他说一开始很兴奋,瞄准那些完全不知死到临头的野兔,让他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等到他熟悉了枪的机制,终于一枪把一只兔子打倒时,他忽然有一种厌恶,他意识到这一枪的后果。谁给了我这样的权力?只因为我有一把枪吗?我比他强大? 洛蒂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夜晚,显然已意识到这一枪的后果。征服者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同时也成了谋杀旧梦的刽子手。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