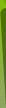拿破仑与大卫(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6日13:39 新民周刊 | ||||||||
|
独裁者独自一人是独裁不起来的,如果没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每一个人对自身利益的那些小小的选择,构成了这个制度形式的基础。 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圣克卢公园的废墟
拿破仑被英国人打败后,除了老百姓没抛弃他,所有他致力维护利益的王公贵族、资产阶级和教会,全都抛弃了他。但聪明的他,靠一部《圣埃莱娜岛回忆录》,把失去的名声、魅力一样样全都追回。这恐怕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本“平反书”。 但他住过的两处最出名的官邸,在战火中被毁灭,却不似人的感情那样追得回来了。这两处地方,一个是杜勒里宫,一个是巴黎西郊圣克卢宫。烧毁时间都是在1871年,前者由巴黎公社放火烧掉,后者是在与普鲁士军队作战时被大炮炸毁。 但圣克卢还是很值得一游。它已经变成一座有森林草地的公园,关键是它地处高地,可以将巴黎城尽收眼底。 这个地方意义不同寻常,还因为拿破仑政变上台是在这里,后来称帝也是在这里搞的鬼。他喜欢住在这个离宫。大革命开始后这十年里,不管是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还是只想将革命进行到适合自己程度的人,都怕再跟“富贵”沾边,因为这两个字似乎已跟旧制度沾在一起。把国王从杜勒里宫赶出去后,没有哪个以革命起家的政客敢住进去。就是西哀耶斯这些督政官,实则代表着有产阶级,也只敢在卢森堡宫办公,据说宫里除了几件办公家具,一件奢侈品也不敢有。当初靠打倒特权阶级、呼吁平等起家,把人家打倒自己立刻登堂入室去享受同样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拿破仑可不管这些,他住进了杜勒里宫,也不怕人说那可是你们推翻的“暴君”的宫殿。他进去视察准备派人整修时,看见墙上还挂着革命党人的小红帽,便对身边人说:“别让我再看见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而离宫他选了圣克卢宫。这是死在断头台上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最中意的别墅。她大革命前从奥尔良公爵手里买下这座城堡,找名匠精心装修,直到1788年革命爆发前几个月才装饰完,却已经无福消受。 我知道圣克卢宫已经烧掉,但以为橘园还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就是在橘园进行的。西哀耶斯和拿破仑于雾月十五日制定了推翻共和三年宪法的政变计划。由拿破仑把军队方面的人控制在手里,西哀耶斯则已策反了元老院最有势力的三个议员。政变的主要目的是推翻督政府,重新制定宪法。实际上就是又一次激烈的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不再通过群众革命这样一种方式。推翻一个宪法再立一个宪法,形同一场革命,要想它不流血,政变是唯一的办法。18日(1799年11月9日)早晨,元老院开会,三名西哀耶斯安排好的议员,危言耸听,说雅各宾党人正从各地赶往巴黎,准备夺权。在几个“暗钉”的搅动下,元老院果真同意了谋反者的要求:将立法两院迁到圣克卢,由拿破仑负责迁移。这一步是把两院与巴黎可能生变的各种力量隔开,便于操作。元老院的命令和拿破仑的布告散发到巴黎街头。布告里拿破仑有几句话,已经颇有主子的口吻:“你们把我给你们留下的如此光辉灿烂的法兰西变成了什么样子?我给你们留下的是和平,我回来看到的却是战争;我给你们留下的是胜利,我看到的却是失败;我给你们留下的是意大利的亿万财富,而我到处看到的却是横征暴敛和民穷财尽……”大革命以来,还没人敢如此露骨地摆出这种唯我独尊的架势。眼明的共和党人马上警觉起来。 西哀耶斯在几天前与拿破仑密商时,也已经惊觉拿破仑的霸气。西哀耶斯跟他谈改变宪法的计划,拿破仑打断他的话:“这些我都知道……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需要的是把两院迁出巴黎的当天就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我同意由三人组成临时政府:你、罗歇-迪科和我……”西哀耶斯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幻灭。几天以后拿破仑又说:“我给他们时间自己想明白了,我完全可以不要他们就能做我同意和他们一起做的事。”西哀耶斯想取拿破仑这把“剑”自用,却不想实则成了对方的谋权刀柄。但机器上了发条,已经停不下来。只能走下去看了。 19日,两院代表来到圣克卢宫。五百人院的会议在橘园举行。元老院的钉子实际已经拔掉,就剩下五百人院了。拿破仑想用对付元老院的办法让五百人院就范。行不通。他就亲自出马,以为议员是他带的兵,可以随他调遣。结果橘园里面炸了锅,人家大骂他:“独裁者!”他仓皇跑出来,不小心把自己脸划破,却对外面士兵说议员里有人要害他。最后,眼看再不动手,政变要流产,他下令士兵冲进橘园,强行解散立法议会。 第二天,有些地区就以两院的名义贴出了告示:“雾月十八、十九这两个不朽之日,挽救了行将和必然分裂的共和国。” 大卫在听到雾月政变的消息后说:“我早就想过,我们的德行没有好到足以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雾月十八日政变就这样把革命留下的最后一个人民代表机关拔除了。自1789年以来,不是没有人想以自己的意志扭转什么,但没有人像拿破仑这么彻底,也没有人像拿破仑这样适逢其时。革命已经疲软到所有人都经不起强力的拉扯,很容易就把辛辛苦苦撑持下来的理想丢掉了。像雾月十八日这样的事,要在1792、1793年,民众早已暴动。但革命十年的结果是,穷人照样是穷人,财产不到一定数目连投票权都没有。我看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制度让老实人长久统治狡猾的人。雾月十八日政变,正是人民想要一个强权保证他们最基本生活的时候,他们已把以前的事忘掉或者不愿再记起了。要到下一个周期才会再翻过来。每一件事都有它自己的时间。 我进圣克卢公园大门时,看门人还跟我说橘园尚在。但我在里面转下来的结果,只找到橘园旧址的牌子,橘园已经没有了。很奇怪的一种感觉,花园、喷泉、石阶、房基甚至露台都在,就是宫殿与橘园没有了。1789年革命后,王后装饰一新的宫殿自己还没住上,已经向老百姓开放了,群众跑来看到里面的优雅豪华,无不开始仇恨特权阶级。不过没有特权阶级,也就没有了奢华,我们就连眼福都享不到了。 马车一路驶向圣母院 共和八年雾月20日(1799年11月11日)凌晨5点,一辆马车离开圣克卢宫,驶进尚在睡梦中的巴黎。车上坐着雾月政变的两个主角:拿破仑和西哀耶斯。这辆孤独的马车让我想到5年后浩浩荡荡穿过圣奥诺雷街驶向圣母院的车队长龙。西哀耶斯已经不在那条长龙里了。 那天凌晨在卢森堡宫分手的拿破仑和西哀耶斯,不出一个月就已经分道扬镳。先是三位执政中迪科马上审时度势,向天平倾斜的那头靠去。他对拿破仑说:“将军,谁主持执政府没有必要再投票了,这个权力应该归你。”一下子就把西哀耶斯扔下了,西哀耶斯如不同意就站到了对立面。从这以后,迪科凡事按拿破仑的心愿走。他对西哀耶斯说:“我们的统治已经结束。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能力掌这个舵。事情很明显,这个国家要一个将军来指挥。” 西哀耶斯背后,有文学名人斯塔埃尔夫人沙龙里一批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支持,从跟拿破仑合作成功的第二天起,他就开始了抵抗。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总是事后聪明,永远生不逢时。他对那些迅速向权力重心处倾斜的人说:“先生们,你们有一个主子了,波拿巴什么都想做,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能做。”他集毕生政治智慧拟定的宪法草案,并不合拿破仑的心愿。与另一执政官分权而治,始终处在行动和被监督之间,这些构成西哀耶斯政治体系的东西,可不是为拿破仑裁剪的衣服。拿破仑这样的人,需要特别量身制作。立法者与拿破仑争到后来,拿破仑便威胁说他要打内战,那时候“会有鲜血没膝”。我好像耳边响起了“不成就上井冈山”。西哀耶斯扔过去一句话:“你是要做国王了。”拿破仑很不高兴:“我不是个国王,我不愿人家用国王来侮辱我……我是从人民中走出来的一个士兵,全靠自己走上来。能把我和路易十六比吗?”日后的历史将证明,国王都还够不上他的野心。 1800年2月通过的新宪法,最显著的特点是诉诸全民投票。当时流行一句话:“新宪法里有什么?”谜底:“有拿破仑。”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全民投票只会顺从他的意愿。民主,民主,有时很蠢。1944年,即便东边有苏联的大炮,西边有美军的飞机,要是再投票,希特勒当选一点都不会比1933年票少。西哀耶斯彻底认输了,他对拿破仑说他别无他求,只想退休。 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官后,把73家报纸,一刀砍掉60家。1803年砍剩8家,1811年只留4家。两院他也并没有不让存在,只是人数和构成都如他所需。他在1802年之前,的确为稳定这个动荡了十年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权威。在议会制吵来吵去做不了的事,他一声令下都做成了。最主要的是,他给有产阶级提供了可靠的保护。他取消了旨在限制富人发财的累进税,把有产阶级最怕的雅各宾党人流放到下辈子也难返回的太平洋小岛。那个奢华的巴黎慢慢又复苏了。商人、银行家最高兴:“这才是一次舞台布景彻底换掉的变革。共和国只是个幌子,实权都在将军手里。”拿破仑自己的评价是:“我恢复了私有财产和宗教信仰。”我看他是一时间把“阶级斗争”的火焰扑灭了。在他治下,法国社会几年就找回了似曾有过的歌舞升平。一时之间,似乎人人满意。下层百姓有不断的对外军事胜利可以欢呼和自慰;资产阶级更不必说,正忙着发大财;就是保王党也从他身上看到英国那个蒙克将军的影子。蒙克将军也是以反王权起家,但后来打进伦敦,解散议会,把查理二世接回来,复辟了王政。如果拿破仑的统治在1802年即结束,历史将只留下他的功德。但真正的野心家是不会自动停住脚步的。“从卓越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这是拿破仑自己说的。 我挑了一天沿八匹大马的皇家马车走过的加冕之路,由杜勒里花园向圣母院走。在里沃利街没有辟出前,圣奥诺雷街是主干道。如今跟旁邻的里沃利街比,它实在是不算宽。可见当年八千人的车队那长龙般的尾巴可以甩多远。圣奥诺雷街昔日的繁荣已经被里沃利街抢尽。但寻旧的人选这条街而避开里沃利是上策。 拿破仑的车队从圣奥诺雷街拐上新桥便直奔圣母院。这是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我在桥上歇脚时,望着亨利四世高头大马的塑像,想到这铜像是波旁王朝复辟后,熔化了两座拿破仑的铜像,重塑的。原版的亨利四世像在大革命中被群众捣毁了。前不久维修时,在铜像里发现一些差不多藏了快两百年的文章和书,全是共和思想的内容。有人推测是雕塑家对王朝复辟不满,才埋下这一伏笔。好有意思,铜像不会说话,但有好多故事。让我们接着讲下去。 从共和到帝制,这一步跨出去,远比当年从帝制到共和要容易。每想及此,我便不得不承认,自身责任感不强的民族,只看见眼前利益。所以他们往往只有两种角色可演:被虐待的孩子或被宠坏的孩子。 越权行为是一步步来的,好动感情的民族,很容易就把权力与感情混淆,并且很容易就把希望寄托在那个最善于煽动他们感情的人身上。事情的起源就是一种感情,实际是一种被操纵的感情。从1802年5月起,就有人提出要向第一执政官证明全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如何证明?还有什么比让他再统治下去更好的礼物?于是,元老院投票通过将拿破仑的权力再延长十年。可拿破仑想要终身权力,这个礼显然太轻了。所以他觉得很不得面子,拒绝了。但拒绝的理由当然是故作谦虚。 我发觉,碰到权欲超强的人,他身边人往往不是去制止他,而是拼命迎合他,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使得历史上的独裁者有太多机会走到底。这些人很快想出了一个高招,既把元老院的决定绕开了,又可满足拿破仑的欲望。拿破仑说:“我要求人民来决定。”你看,碰到这种人,人民迟早都是人质。而向人民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再干十年行不行,而是“拿破仑·波拿巴是否做终身执政?”元老院哑口无言。 投票结果可想而知,同意票占绝大多数。于是,拿破仑被宣布为终身执政。 我已经走到巴黎圣母院前。在那个寒冷的冬日,为了拿破仑的加冕礼,整个巴黎都张灯结彩。为一两个人的心事搞得全城大动,现在看简直荒唐,但身处其中的人,觉得理所当然,这才可怕。眼前刚刚整修完的圣母院,像迟暮美人新涂了脂粉,让人颇有了几分年龄加魅力共同对付青春的底气。加冕礼那天,圣母院的外墙完全被罩起来,因为大革命中提倡“崇高人类”信仰时,圣母院外墙上的雕像被砸个七零八落。革命的疯狂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为这次盛典圣母院周围的民房全被下令拆除。权力可以让人将自己的欲望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看来现在圣母院前这个摆放漂亮圣诞树的广场还是多亏拿破仑了。广场上也有一个塑像,比亨利四世的那座还要高大,非得把头仰得很高才好观赏。这就是拿破仑孜孜以效的榜样——查理曼大帝。 拿破仑还有最后一步就走过来了。 到了1804年,由于对英战争,以及抓出了几个谋反将军,有人提出:“广阔的帝国四年来全靠波拿巴的坚实领导才得以休养生息”,所以必须确保领袖身后这个政权的存在。 这只是借了一个机会,通向权力顶峰一直就在拿破仑的野心里的。 在权力面前,拍马屁者的传染性远大于批评者,于是一呼百应。元老院起草了一封肉麻的信给拿破仑:“伟人,完成您的巨作,让其永垂不朽,就像您的光荣。您把我们从过去的混乱中拯救出来,您让我们享受到今天的幸福,再为我们保证未来吧。”马屁走遍世界都是一样的,真遗憾!为了“革命”,给终身执政官一顶皇冠的时候到了。整个元老院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这才叫“全国一心”。元老院走在前面,别的人也不甘落后,谁都想分到“伟大杰作”的一份。法案评议委员会秘书长是个“改邪归正”的雅各宾党人,居然号召同行说:“对于全国政权的领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比皇帝这个头衔更配得上我们伟大的国家。”“改邪归正”后再踩准鼓点的人绝少,惯性常常又把他们甩到了另一头。不要忘了,法案评议委员会是三权分立的另一足。可见政权制度随便你怎么立,人都是可以另搞一套。关键在人。 拿破仑呢?还在装模作样:如果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他准备接受,但要全民投票。 于是在确立终身执政官两年后,再次试探民意。当然是顺利通过。人民把推翻旧制度时的不理性,又一分不减地用在建立新制度上——或者说建立一个根本就是“旧”的新制度。没有一个结果不是由人的欲望产生的。独裁者独自一人是独裁不起来的,如果没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每一个人对自身利益的那些小小的选择,构成了这个制度形式的基础。所以从历史上看,有些民族往往是推翻了一个独裁者,再选出另外一个独裁者,而且常常更独裁。每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意识到自身的利益与他人利益那个适当的界限,意识到每一个选择的后果,才是走向个人独立的第一步。没有独立个体的社会,每个人不能自我负责的社会,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永远不可能是一种理智的关系。 20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在卢浮宫络绎不绝地观赏大卫的《拿破仑一世加冕礼》。曾如此崇拜革命的大艺术家,最后以其才华,将独裁者被送上皇帝宝座这一幕永远地留在了人间。而艺术家本人则至死没有回法国,后来王室碍于他的名气,倒是愿意特许他回来。但这一次也许依傍权势的苦头吃够了,他拂了路易十八的好意。他说:“我是由一条法律放逐的,只能由一条法律才能再回来。”他与拿破仑的路早于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便永远分开了,但油画艺术将他们永世拴在了一起。■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