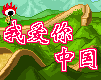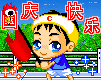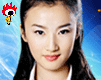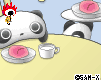高耀洁河南艾滋病已无空白点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1日19:26 中国《新闻周刊》 |
|
因为非法采血,河南成为中国的艾滋病大省。75岁的高耀洁为同胞面临死神威胁奔走呼号数年。这是她成为本年度 全球唯一一个世界卫生大会JonathanManm健康奖获得者。 颁奖在即,高耀洁却突然接到通知:不能去领奖。 高耀洁知道:有人不希望世界知道河南艾滋病已经进入高发期的惨烈现实。她说,我 还要孤军奋战下去。艾滋、艾滋、艾滋。高耀洁的家,如同一个“防艾”展览馆。 角落里,堆满了她自编自印的艾滋病宣传单,上面的标题很敏感,什么“避孕套能阻止艾滋病病毒吗?”什么“游泳 能传染艾滋病吗?”书柜中,陈列着她编写的《性病、艾滋病预防》等书籍,她说这书已经送出了几千册。 墙上,是她走入河南艾滋重灾区——比如新蔡县和上蔡县,与艾滋病孤儿的合影。她满脸的皱纹与孩子们稚嫩而忧郁 的面孔,勾勒出一副让人心痛的画面。而“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副挂在她家客厅正中的对联,则是高耀洁目前生活 的最真实写照。 一缕微弱的晨光打在高耀洁的脸上。听说记者来采访,她清早5点就起床了。她说她有很多话要找人倾诉。 这位75岁的河南老太,致力艾滋病民间防治宣传已有5年。她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编写发“防 艾”材料数十万份,为此个人出资10多万元。而她与她的老伴,却生活在冬天连暖气都用不上的简易楼里。家中桌椅家具上 的漆已然脱落,只能从斑驳的痕迹中,辨别出当年的红色。 为表彰她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突出贡献,世界卫生大会将2001年度“JonathanManm健康奖”授予高 耀洁。“健康奖”每年评选一次,在全球范围内仅有一个名额。5月29日—6月1日,这次颁奖大会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4月8日,高耀洁通过网络获悉这一喜讯。当天,122个祝贺电话打进了她清贫的家。 “谁说我不想去领奖?” 新闻周刊:获悉得奖之后,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高耀洁:我只有一种预感,可能去不了美国领奖。 新闻周刊:为什么? 高耀洁:上面的阻力大。我的领导,上到河南卫生厅,下到我退休前所在的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一直不赞成 我对河南艾滋病的防治和宣传。 新闻周刊:领奖真的遇到了很大阻力? 高耀洁:对。5月8日上午,河南中医学院一位党委副书记找到我,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高老师,我看这个奖还是 不要去领了。小布什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一直不稳定,加上前几天的撞机事件,局势更紧张。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的反华倾向 比较严重,我们怕您被他们利用了。”听到这话,我很恼火,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和中美关系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我知道,这种 事情我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就说:“既然领导这么决定,那不去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到省妇联去领稿费——稿费是我用于补贴艾滋病投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妇联的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告诉 我:“去与不去,不是个人的事情,你必须和省里打招呼。” 几天之后,河南省一位副省长对此表了态:“我们共产党最讲人权。我认为:高教授去领奖,利大于弊。” 新闻周刊:事情出现了转机? 高耀洁:根本没有。虽然省领导支持我出国领奖,可办手续的时候,又受到了单位的阻挠。出国证明需要一个我的档 案所在地——第一附属医院的公章,但到了5月15日,这个章还没盖下来。 5月16日晚,河南中医学院统战部部长和我们医院院长一起来到我家。他们催促我表态:“高老师,您就说您不想 去领奖。”我说:“这个态我不能表!谁说我不愿意去领奖?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不想给河南丢面子。如果我一去领奖, 全世界就都会知道河南的艾滋病情况很严重了,某些人会为此担责任,他们平坦的仕途就会受到阻碍。” 他们一再劝说,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去,那我就不去;但让我自己说不去,绝对不行。” 新闻周刊:如果这次领奖之路没有成行的话,会有什么损失? 高耀洁:如果能去,可以获得国外的一些资金支持,钱对于河南的艾滋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新闻周刊:那您估计您还能出国吗? 高耀洁:现在不好说。他们告诉我再等几天。但我最后的期限是5月24日晚。因为美国驻华使馆通知我:5月25 日上午10点必须到使馆科技处领签证。如果我赶不上5月24日由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这件事也就不成了。 阻力!阻力!阻力! 新闻周刊:真没想到,去领一次奖都那么不容易,那您在5年的工作中受到的阻力恐怕难以想象。 高耀洁: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几年来10多万付出去了,没花政府一分钱。我图什 么?可就算这样,一些领导却说我是瞎折腾,我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多了。 1999年,我被评为国家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没能去北京领奖,内部消息告诉我 ,是怕我到北京见了中央领导谈河南的艾滋病情况。而单位也没有落实我的奖励措施。 1999年12月1日中午,郑州电视台请我现场做了“防艾常识”讲座。当天下午,某位领导一共找了我四次。她 说得很好听:“这是为了爱护你,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厅(指河南省卫生厅)里说了,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人。”而 在当时,我兜里有张纸条,上面有12个艾滋病人的姓名和地址。 2000年8月,《新闻周刊》到我这里采访,并对河南的艾滋病状况进行了调查。报道反响很大。某领导看到周刊 后怒道:“高耀洁擅自向记者提供有关艾滋病疫情的资料,影响河南形象!以后不准她再接受记者采访。”11月15日,这 位领导再次警告我:“今后不能再见任何记者,不能再谈艾滋病。” 2000年11月19日,河南卫生厅一位处长到我家来办事,进门就跟我说:“你见了卫生厅的人,千万不要说我 来过。”我和他谈起艾滋病的严重性,他连连摇手:“不敢说,不敢说……” 还有人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已经被监控了”;我的一些朋友不敢再同我接触,因为领导的“特别关照”了他们.. .... 新闻周刊:刚才听您所说的压力,大多来自官方。为什么他们会对您如此反感? 高耀洁:因为怕我的宣传断了他们的升官之路。这在我和性病游医斗争时已经有了征兆。1998年,我揭开了河南 街头性病游医的老底之后,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有关领导就受到了时任省长的马忠臣的严厉批评。相比之下,艾滋病的危害肯定 要比性病游医厉害得多,会死很多人的!所以一旦真实情况传播出去,有关人员还能不负责任吗? 不过现在,有些人又开始拉拢我。他们可能意识到,我跟新闻媒体接触的比较多,强行压制造成的坏影响更大。他们 对我说,你可以搞宣传,搞调查,我们还可以对你进行支持,但调查结果不能向外公布。就在今年5月中旬,一位领导还来过 我家,请我去泰国考察。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有考察的钱,还不如给艾滋病孤儿买几个馒头!” 新闻周刊:除了来自官方的阻力之外,您在工作中还遇到什么困难? 高耀洁:社会对艾滋病人不理解。人们认为:这病是“脏病”。所以,在我募集“防艾”资金的时候非常困难。我是 妇科大夫,现在还给一些人出诊。治好了人家的病,他们会来感谢我。一次,一位很有钱的电厂厂长来到我家,说:“高大夫 ,冬天来了,我送您一件皮衣吧!”我说:“你还是给艾滋病孤儿捐上几百块钱吧!”他当场拒绝,以后也再不提这事儿。从 今年三月到现在,我一共才募集了2000元钱,杯水车薪呀! 其实,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大都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卖血。不久前,我获取了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夫妻 一方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另一方两三年后抽血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仍然为阴性,且人员健康状况良好。由此说明,在 我接触的艾滋病人中,性传播的方式还是很少见的。如果这个研究结果确实成立,能为不少艾滋病人正名。 河南地界:艾滋病没有空白点 新闻周刊:与过去相比,2001年河南艾滋病整体情况有何变化? 高耀洁:2000年和2001年,应该是河南艾滋病的高发时期。因为由于输血传播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病毒潜 伏期是5年左右,而河南地下采血盛行于1995-1996年。今年3月——4月,我到魏氏县水坡乡水黄村调查,当地人 告诉我,从去年中秋到今年3月,一个村因艾滋病死了47人。今年3月15日——4月7日,仅仅23天,又死了3人,平 均每周一个。艾滋病人死了,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座新坟,还有他们的孩子。有些人家父母双亡,一批艾滋病孤儿无依无靠,惨 不忍睹。 新闻周刊:目前河南艾滋病高发区是哪里? 高耀洁:上蔡县是很著名的,大约有上千篇报道,但新蔡县更严重。除此之外,还有周口、南阳、信阳、开封、商丘 、漯河、许昌、平顶山……包括黄河以北的鹤壁。总之,河南地界,恐怕已经没有艾滋病空白点了。 我说这些,决不是信口雌黄。我这里有各个地方的艾滋病人的来信,一共3000多封,我接到的咨询电话则是信的 10倍。 新闻周刊:目前河南省的艾滋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总数有多少? 高耀洁:不好估计。但仅在上蔡一个县,就不下10000人。这是县里自己承认的。 新闻周刊:目前河南的卖血现象是否得到了控制? 高耀洁:有很大程度的控制,但没有完全杜绝。不久前我去杞县调查,一位姓徐的男子就是被抽血活活抽死的,3天 抽了18000cc。他的儿子今年才两岁,我拿着徐的照片问孩子:这是谁?“叔叔、伯伯,”孩子就是认不出爸爸。当孩 子的母亲在一边痛哭时,那里的血头却说:“现在抓的紧了,要不然我还干。” 何时不再孤军奋战 新闻周刊:去年《新闻周刊》对您进行专访时,曾以《高耀洁:与艾滋病孤军奋战》为题发表文章,来形容您“防艾 ”的势单力薄。近一年过去了,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观? 高耀洁:很遗憾,基本上没有。目前,与我志向相同并有所联系的人,只有湖北武汉的桂希恩教授。但我们距离太远 ,很难互相支持。 另外,还有一些人想和我合作,但目的不纯。有人想通过我骗钱,说咱们联合推销药物吧,这药可以根治艾滋病;还 有人想捞名誉,建议一起搞个什么办公室,专门接待记者采访,进行宣传。这让我怎么接受? 新闻周刊:但您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想没想过借助集体的力量? 高耀洁:我个人尚且受到这么大的阻力,怎么搞团体?如果真成立了什么协会,一定有人会以“反党”的名义给我扣 帽子。说不定,还会引来牢狱之灾。我都70多岁的人了,再也经不住折腾了。 我目前的状况很不好,小女儿因为受我频频出头的牵连,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工作,已经和丈夫远走加拿大。她生我 的气,至今没有和我联系。我的大女儿现在病得很重,可我根本抽不出时间去照顾她,只能把她托付给她姨。现在,我的老伴 也有病。 新闻周刊:既然如此,是什么力量支持您去面对这项事业? 高耀洁:你看到墙上的对联了没有——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尽管目前我经济上,在精神都很困顿,但这不会让 我停步。我出身很苦,又一直和社会底层人士接触,看不得别人受罪。何况,救死扶伤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尽管在语气中流露着坚强与倔强,但说这番话的时候,高耀洁还是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她没来得及拭去眼泪,电 话铃再次响起。 电话来自一个病人家属。这位家属是河南省某权力机构的一位官员,高耀洁委托他打听自己出国领奖的事情能否成行 。来电的语气很沉重:“高老师,‘上面’可能不让您去了”。 未能领奖将成为高耀洁的遗憾。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何况,今年她已经75岁了。但这位坚强的老太太只 叹了一口气,擦干眼泪,就去整理她的资料了。她说:“我要把这些资料印出12万份,发给那些为艾滋病所困的人。” 本刊记者/吴晨光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