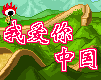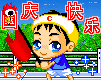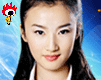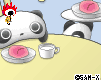经常和朋友们呼啸成群地凑在一起喝酒,他们见到我的开场白一般都是这个问题:“现在在哪儿高就?”我通常也是
顺口就说出一个曾经呆过的地方的名字,脸不变色心不跳。听者不会再继续打探,我也不会再提起。于是双方相安无事,推杯
换盏。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
听说有的人在网上有几十个ID,网虫们戏称之为“马甲”。那些老鸟大虾们在网上熟
练地用这些ID玩着角色转换
的游戏,乐此不疲。一会儿装成一个学者,一会儿装成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或者干脆扮成妙龄MM与人打情骂俏。把个好端
端的INTERNET弄得像个假面舞会。每当夜色阑珊,意犹未尽,下网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想:莫非我在实际生活中也
成了这样的一只老鸟,那些被我干过的工作,或者说曾经练过的摊儿,也成了我随时可以更换的马甲?想到这儿,不由地出了
一身冷汗,在心里暗骂自己。
当初刚从大学校门里出来的时候特有理想,还想过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呢。可是这些崇高而美好的东西都已经离我要
多远有多远了。现在的我正朝着一个地地道道寄生虫的方向迅速地滑去,虽然还有些不甘心,偶尔还回头张望一下那曾经被我
向往过的峰顶,但是必须承认,我从这种“自由落体”的堕落中体会到了一种接近于纯粹的快乐。
稍微有一些物理常识的人都会懂得:任何一种形式的下落都会产生一种力,而这种力量的承受者必定受到一定程度的
损害,损害的程度取决于下落的速度和承受物的柔韧程度。在我迅速地堕落成一个害虫的过程中,老板可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了。我前前后后换过不下10个老板,或者说领导者。他们对于自己“被炒”的命运接受起来也不太一样。有反应比较激烈的
,也有淡然处之的,破财消灾的。在我茁壮成长为一个寄生虫的道路上,可以说既是这些老板们成全了我,也是他们毁了我。
怎么理解都可以。
据说在日本,部门经理以员工抽屉里面东西的多少来衡量他对企业的忠诚,东西越多越忠诚。如果我在这样的公司工
作,肯定第一个遭到辞退。因为我会连卫生纸和水杯这样的必需品都不带,纸用卫生间的,杯子用一次性的,随时准备溜号。
可是当初我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恨不得把家都快搬去了。以至于辞掉工作之后分成三次才把东西全部运回来。
那是一个销售计算机终端的公司,我在市场部干的活儿跟自己的外语专业挨不上边,有种使不上劲的感觉,再加上我
实在受不了那些客户的土鳖状,与我当初对事业的憧憬相去甚远,于是断然离去。当时的老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绅士,不但没
有因为我贸然辞职而责怪惩罚我,甚至还给了我一笔不少的钱,使我在第一次辞职的惶恐中还能有物质的安慰。记得我当时确
实是伤心地哭了,可是看见那一大笔钱就又破涕为笑了。
一个人的第一次经历是很重要的,它几乎定下了以后所有类似经历的调子,就好像女人的第一夜。
我之所以在“炒老板”这件事上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绝对和我第一次辞职的经验太美好有关。它主宰了我几年来的命
运。很难说这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诅咒。说它是一种祝福,是因为它让我在以后与老板的周旋中无往不胜。说它是一种诅咒,
是因为它永远地改变了我对一份工作的神圣看法。
对于经历过那件事的我来说,工作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一个需要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人的一根稻草。一切都
与理想无关,与事业无关。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饭碗而已,吃得不痛快,不舒服,砸了它换一碗又有什么不好呢?就好像女人和
一个男人做爱,如果是为了爱情她是要专一的,她是要只献身给他一个人的。而如果仅仅是为了钱,她是绝对没有理由在一棵
树上吊死的。如果所有动作只不过是在卖身,谁给的钱不是钱呢?
我在工作问题上水性杨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根本就没爱过这些工作,尽管其中的一些很让别人羡慕。那什么样
的工作才是我爱的呢?我到底想干什么呢?我是真没想明白。而且还特怕别人貌似关心地问我,因为我这人太敏感。在人家看
那只是风中的一粒沙,可是这粒沙它吹到我眼睛里,那就不是沙了,那是板儿砖。
就让我这样寄生下去吧。既然大家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就让我多蹦几下儿,把这些鸡毛扬起来做个假雪景吧。反正
大家都在演戏,也就甭笑话谁穿帮了。丢人也是丢的大家的人,现眼也是现的大家的眼,一个也跑不了。我连墓志铭都想好了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不要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要因为生活
庸俗而羞愧。临死的时候,我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自由和独立而
斗争。”
文/丢丢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