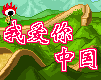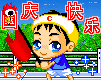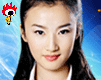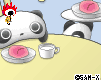2003年12月01日:春节晚会导演赵安受贿案调查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2日21:26 中国《新闻周刊》 | ||||||||||||
|
春节晚会导演 赵安受贿案调查 在赵安“受贿案”广受关注却又信息明显缺乏的情况下,一位电视节目制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颇有价值的判断,他说:赵安更像是一个符号,在公众的思考路径里,他代表着
在传统社会向市场机制的转型中,传媒手中掌握的“软权力”,同样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同样会被“购买”。这种“购买”与“被购买”直接导致了传媒的堕落——商媒勾结或者商媒共谋。 中国的传媒特别是具有垄断色彩的媒体中的“权力阶层”,似乎还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 受贿案真相 人们真正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赵安”这样一个具体的个人和他究竟“犯了多大的事”,更是他手中掌握的特殊权力的寻租空间 本刊记者/金凌云 特约撰稿/ 艾先立 于飞 一年来,有关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文艺节目中心副主任兼文艺部主任赵安,和知名演艺人士张俊以的受贿、行贿案不断被演绎出若干版本:有消息说警方在赵安家里光现金就起获了1000多万元;还有消息说张俊以是因为逃税和制作非法广告才东窗事发。 事实是,赵安因涉嫌犯受贿罪,在2002年9月26日,接受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讯问,后取保候审;同年10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检察机关批准,10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北京市某看守所。 张俊以的情况类似,只是批捕的时间稍晚,因涉嫌犯行贿罪诽谤罪,于2002年10月1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11月2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北京市某看守所。 目前赵安“受贿案”的最新进展是:2003年10月29日上午9点,法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庭审后宣告休庭。 扣押款物清单与量刑焦点 警方对赵安案件的调查结论是——44岁(1959年9月30日出生)的赵安,在1994年至2000年期间,先后利用担任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部副主任、主任,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春兰杯”颁奖晚会总导演,2000年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等职务的便利,多次为词作者——33岁(1970年3月16日出生)的张俊以谋取利益,使张俊以创作的作品得以在上述晚会及赵安主管的各类文艺晚会上演出,并使宣传张俊以的专题片得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为此,赵安向张俊以索取贿赂人民币6万元,并先后两次收受张俊以给予的贿赂人民币5万元及价值人民币50万元的音像设备……(见下页扣押款物清单) 这是赵安被起诉的全部内容。 如果罪名成立,对赵安的量刑轻重,关键将集中在赵安受贿时的身份认定上,即他是否算是国家工作人员。据相关律师介绍,“受贿罪”又可分为“商业受贿罪”和“受贿罪”两种,前者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只要符合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取钱财的,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相对“商业受贿罪”,“受贿罪”的量刑更重,最严重的甚至可以判处死刑,需要强调的是——它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律师称,由于不能确定赵安的主体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无法对赵安的量刑做出准确预测。但这名律师的估计也许过于乐观,检方在起诉书中,对赵安的身份是这样描述的——“本院认为,被告人赵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第款第(一)项之规定,已构成受贿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更为复杂的张俊以案 从起诉书中可以看出,张俊以的案情要比赵安复杂得多。 张俊以除了被起诉行贿罪以外,还面临一项诽谤罪的指控。 起诉书写明,除张俊以外,被起诉的还有另外一人:被告人杨雪泥(曾用名杨雪芬),女,25岁(197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安吉县人,无业,因涉嫌犯诽谤罪,于2002年10月2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11月2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据了解,张俊以和杨雪泥被指控于2001年10月至11月期间,捏造、印制了多份以污秽语言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的匿名信件,这些信件多达100封,从浙江杭州分别邮寄,后被公安机关截获。 另外,还有200余封匿名信件在北京、天津、河北省廊坊市被邮寄散发。 行贿罪一般处以5年到10年的徒刑,严重者可判无期徒刑,而诽谤罪量刑一般不超过3年。 赵安与张俊以的“亲密接触” 赵安,浙江人。1984年,学舞蹈出身的赵安,从某歌舞团调入中央电视台任导演,这一年他25岁。此后他一路平步青云,直至身居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文艺部主任等职。文艺部主管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他本人也曾7次执导该晚会,并4次出任总导演,分别是第七、第十、第十三、十八届春节晚会总导演,时间为1989年、1992年、1995年、2000年。 “很大程度上,是体制造就了赵安”,一位圈内人士如此评价,“中国人好大喜功,场面越大越喜欢。赵安就擅用‘人海战术’,其实劳民伤财,也导致了他自身的膨胀。” 张俊以,1970年出生在松辽平原的小镇郑家屯。原来是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的一名记者,后来在采访中认识一些明星,开始借钱组织走穴。尝到甜头后,他毅然离开家乡前往北京闯荡。张既不会唱也不会演,他的看家本事是——写歌词。 关于赵安与张俊以的相识,听起来像一个传奇故事: 1995年冬天,张得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正在排练,就连开了几个夜车,将自己几年来最满意的诗歌作品送去。好不容易,张被一位在吉林“走穴”演出时结识的龙套演员带进春节剧组的驻地梅地亚宾馆。在一间不起眼的房间前,张撞开门找到导演组。当时的春节晚会总导演正是赵安。 在被赵安否决十几首新诗旧诗后,张绝望地说:“莫非连一首歌词挤上去的可能都没有了吗?”此时,赵安提起有首《贺年卡》的歌词较差,张就冒出一句,“什么歌我不能写?”并当场发挥,做了一首《贺年卡》歌词,被赵安当即首肯。 据知情人介绍,张俊以把这首歌词改了不下十稿,最后在第三天夜里写成并获得赵安等人的最终认可。也就是从这时起,张的歌词得到了上央视春节晚会的机会。 这个故事虽未得到当事双方的证实,却已广为流传。 这只是张俊以通过中央电视台发迹的开始,从此以后,从1997年到2002年,张俊以创造了每年都有歌词进入春节晚会,而且全都被明星演唱的纪录。到2000年春节晚会时,张俊以的势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我和你》、《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西部狂想》都入选,其中《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有蒋雯丽、吴若甫、傅笛声、任静、孙浩和周艳泓6人一起演唱,一首4分钟长的歌曲由6人演唱,每个都是当红明星,由此可见张俊以当时受追捧的程度。 2000年也是张俊以最忙碌的一年,那年下半年他一直忙于中央电视台那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晚会《奥林匹克星》。这台晚会由张俊以和赵安担任总体设计,晚会上,更是以张俊以写的歌作为主打,《欢迎你到中国来》、《同心同庆》……等多首标明由张俊以写词的歌曲在晚会上一一唱响。 时至2002年春节晚会,“词坛怪杰”张俊以仍有两首歌词入围:由吕继宏、张燕演唱的《左邻右舍》,还有浮克作曲的《美丽新世界》(演唱者是美籍台湾偶像歌手王力宏),由港台歌星演唱内地原创作品,这也开了春节晚会的先例。 至少是部分地借由强势媒体——特别是收视率高达96%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传播效应,张俊以平步青云。案发时,他担任北京生命之星广告有限公司董事、经营药品的北京生命之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等职。 张近几年来在公益事业上的大笔投入可以折射出他的雄厚财力,1998年,张俊以为抗洪救灾捐款700万;1999年设立“张俊以儿童文学基金奖”捐300万;2000年设立“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俊以基金”又捐600万;2001年为“张俊以救助孤儿爱心基金”再捐360万…… 关于张俊以和赵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认识赵安之前,张俊以苦于自己在公众面前没有让人记忆深刻的形象。看到赵安的大胡子后,他留起长发并烫成波浪,再加上永远微笑的面孔。从此,一个“大胡子”,一个“长卷毛”,成了文艺圈的一对醒目人物。而这一切,都结束于去年的秋天,赵安和张俊以均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赵安案”暴露 媒体权力卖场 电视系统改革已经迈出很大步伐,但在内部管理体制上仍然没有实现科学化。对于整个电视业来说,目前迫切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和市场运营的规则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 本刊记者/金凌云 刘志明 文/于飞 刘滢 10月29日,记者终于找到钱列阳。钱列阳是赵安的代理律师,但他显然不愿让公众知道自己的这重“身份”。钱不愿解释为什么要“保密”,却反过来问记者:“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赵安的辩护律师?” 就在当天上午,沉寂近一年的原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赵安“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钱列阳出庭为赵安进行辩护。 核心数字——61万元 钱列阳说,“不要谈论本案。”随后,他解释说,赵安案与此前同样由他担任辩护律师的刘晓庆案“大不一样”。 持续多日的采访中,不少被访者尽管声称“知道一些内情”,却仍然对谈论赵安和张俊以退避三舍。而10月29日的庭审,有关方面的处理也颇为谨慎——之前没有公开的消息发布,之后虽有媒体对此报道,却也语焉不详,没有庭审的实际过程及详细内容。 目前所知的惟一细节是,赵安在法庭上表现得“口才极好,滔滔不绝”。钱列阳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赵安)的精神状态不错”。 本刊辗转得到一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赵安的《刑事起诉书》。这份起诉书只有短短500余字,起诉理由围绕着一个核心数字——61万元。这是控方认定的赵安收受张俊以贿赂的数额,而此前经由媒体传出的“执法人员从赵安家中搜出千万元巨款”的消息,起诉书并未提及。 据知情者转述,钱列阳为赵安进行的辩护主要围绕“是否构成受贿”,即“赵安有没有利用职权为张俊以谋取利益”? 这个疑问,又须以另一个问题为前提:中央电视台究竟应不应该在节目中使用张俊以的作品和播出“宣传张俊以的专题片”?也就是说,如果给张俊以打分,他提供给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那些作品有没有达到央视文艺节目中的“合格线”?如果没有,那其中便有赵安的权力在起作用。 赵安的权柄有多重? 对普通公众而言,对电视节目选用标准问题的“技术性”思考,显然并无实际意义。人们真正关心的,仍然是媒体这样一个机构中的“权力”运用以及控制方式。 赵安曾担任四届春节晚会的总导演。作为收视率极高的春节晚会,运作方式究竟是怎样的? 春节晚会剧组是临时成立的,分为歌舞类节目组和语言类节目组,有权力在晚会里安排节目的,首先是这两个组的导演。他们选择各自的节目,再层层审批,先要过总导演一关,总导演以上是台文艺部,文艺部以上是台领导,最后节目还要通过广电总局等方面的审查。据统计,总导演之上对晚会有说话权的人共17名左右。 每到春节晚会前夕,每个节目组的导演都有一个大大的类似作战地图一样的东西,来分辨节目层次,比如定下的节目就插个红旗,可能要换的节目就是一个黄旗,随时要换的就是绿旗。 春节晚会的节目,大致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必须要上的,这种节目演员人气旺;第二种,是节目较好,但入主春节晚会的稳定性没有保证;还有一种,就是安排进入大联唱之类的节目,业内人士往往视之为安排所谓“条子演员”的一个大筐。 由于像春节晚会这样的大型演出价值极高,因此,像赵安这样的总导演自然举足轻重。一名圈内人士评价说:“赵安是总导演,演员想上晚会,就觉得一定要去找赵安。这样就把关系搞乱了。”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介绍说,电视媒体中的“权力层”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按职能划分,比如部门主任;另一种则是按内容划分,比如制片人。前者属于频道运营序列,后者属于内容制作序列。 依照这样的划分方式,作为总导演的赵安的“角色”显然具有双重性:在人所共知的春节晚会等大型演出项目中,赵安的总导演“角色”相当于一名“节目采购经理”,他向节目提供者(比如演员)“采购”节目;而在日常的频道经营中,赵安又是一名程序安排者,他有权决定或至少有权参与决定节目的播出与否,以及播出的时段。正是这双重“角色”的兼具,使赵安手中的“权力”变得沉重。 价值千金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表 赵安的权柄分量,自然也与央视春节晚会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关。这个一年一次的、集中了全国十几亿人的眼球、收视率高达96%(据央视调查公司数据)的夜晚,让无数演员生发出一夜成名的梦想。 原本在美国百老汇默默无闻的费翔,因为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台湾歌手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创造了中国歌坛的纪录——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销售了2000万盒,在内地开了63场个人演唱会。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文艺圈里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明白——只要能在春节晚会露一小脸,这一年就会穴单不断,财源滚滚。 但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时间最长只有4个多小时,能上节目的演员有限。因此,近几年观众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春节晚会上的合唱特别多。2001年的春节晚会,合唱节目飙升到21个,一首《西部放歌》,节目单上就写有13个人的名字。赵安在有一年春节晚会后曾经给出这样一个数字:歌曲45首,其中只有21首是完整唱完的,还有4个歌舞组合,每个组合中至少有5个左右的联唱,所有歌舞演员一共有700多人。 春节晚会每年能给中央电视台进多少账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一年比一年行情看涨却是个事实。据独家承办2003年春节晚会广告的公司透露,今年晚会的广告比上年每秒涨了10万元,达到每秒30万元。除广告时间,年年让观众不胜其烦的主持人念贺电,也大多收了企业的钱。据了解,在2002年的春节晚会,前一年广告投放额超过150万元的企业,可以得到春节晚会现场的一个座席。而在2003年,这个价格涨到了200万元。 电视媒体的权力“卖场” 因为媒体存在这样那样的“权力”,在媒体之外便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卖场”。在许多熟悉此间运作的电视圈内人看来,这早已不是新鲜事。 电视节目制作人阿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解释媒体“权力”的作用。在一家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组中,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一段时间内接连收到从外地寄来的支票,而她却困惑于并不认识寄出支票的人。几经查问,方知支票并不是寄给自己的——她与该栏目组的制片人姓名完全相同。这名工作人员于是感慨:如果我是那名制片人就好了! 阿忆在电视界工作十年,曾格外观察其中的权力运作。他说:“在几乎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权力的运用很容易形成所谓的‘灰色经济’。” 90年代初期,刚进入电视台工作的时候,阿忆参加过一个剧组。其时,为工作方便,剧组入住了一家宾馆。当他发现剧组只有七八个人却租用了宾馆整整两层楼时,“大吃一惊”,于是去问同事们为什么,却被同事取笑“少见多怪”。现在,在电视界工作多年的阿忆终于明白,这只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招数”。简单地解释是,制片人手中掌握着数额可观的预算,而此举的用意不过是将预算的一部分先行“花出”,而后再收入囊中。同样的“道理”,适用于购置道具以及给那些实习生或临时工开工资。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分析这种现象说,媒体的“权力阶层”手里有很多没有明确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模糊性”,使他们手中可以调度的人财物等资源很多。电视系统改革已经迈出很大步伐,但在内部管理体制上仍然没有实现科学化。在宋建武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制约。 “当然,要把所有权力都严格监督起来,也不大可能。所以,制约要靠商业上的规律。”宋举例说,在国外电视界,频道运营和内容制作是两个可以相互约束的关系,节目经理认为制片人的节目不行,便可以弃用其节目产品。而在国内,部门主任(相当于节目经理)和制片人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或者是同事关系,其间的约束力并不强。 “对于整个电视业来说,目前迫切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和市场运营的规则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现在市场分工非常细腻,大到一个电视台,小到一个栏目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它究竟是内容产品的制造商?还是频道运营商?要把功能划分清楚,然后根据功能重新进行部门划分,在部门划分的过程中,又把不同职位的角色确定。把责权利描述清楚。”宋建武说。 “就媒体缺乏监督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问题,其他媒体也一样。媒体监督已经成了媒体界一个共同的问题。”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院副院长黄升民表示。
央视大力反腐 央视拥有的,虽然不是对社会直接进行管理的硬权力,却是具有一定垄断意味因此也具有某种稀缺性的软权力。 人们关注央视,因为人们寄望央视 本刊记者/ 丁尘馨 言咏 根据中央电视台日前的决定,戏曲音乐部主任孟欣离开了工作6年的岗位,带着自己一手创建的《同一首歌》栏目被调往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任职。 和孟欣同时被调整岗位的,还有央视20多个部门的处级负责人,如此大规模的官员轮换,在央视尚属首次。 据了解,中央电视台这次处级干部大换班其实早在半年前就已逐步开始,央视原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主管电视剧的副主任冯骥均被调到国际电视总公司。而不久后,冯骥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拘捕。 这次岗位大轮换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央视是为了防止更多的部门主任滑入职务腐败的泥坑,而大手笔地进行内部反腐动作。 “领导轮换”与禁止有偿新闻 据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央视就尝试科一级的干部交流,但当时的范围很小,只有三四个人。 针对的是长期从事某一岗位,而这一岗位又比较敏感的领导位置,比如与经济方面接触较多的岗位。SARS前下了调任单,SARS后调换结束。 而此次处级领导大轮换主要调整的是节目部门。除了戏曲音乐部、新闻部门外,还有社教、管理等专题类节目的部门。 尽管央视相关部门一再强调这次岗位轮换的出发点是从业务角度考虑,和内部肃贪没有必然联系,但如此大范围领导岗位的调整,客观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廉政意义。 和央视处级干部大轮换同样被关注的,还有其10月出台的《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声明》,央视同时还公开了举报电话。 据称,这个声明出台的背景与前一段发生的“繁峙事件”有关。2002年山西省繁峙县“6·22”金矿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因收受“黑金”掩盖事实真相,成为今年传媒界最大的丑闻。 财务改革与栏目管理公开 本刊还了解到,从去年年底起央视的财务部门开始进行成本核算,主要是核算哪些节目花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花得是否合理。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一项比较大的措施。 还有一项措施是:栏目管理公开。该措施被称作“阳光工程”。 目前,中央电视台最基本的管理单元是栏目,全台共有300多个栏目。以前人财物的管理和运作权都集中在栏目自己手中。从去年开始,央视从各频道选了12个栏目进行改革试点——所有的财务开销都需向纪检组、台领导公开;栏目对人员的录用和解约,也需要详细说明理由;财务制度在细节上也更为严格,比如一个剧组以前买方便面、点心等食品作为加班之用,只需要一张发票就可以报销,现在则需要明细小票。 这项改革今年可能在整个中央电视台全面展开。 同时,央视还将进行制片人改革,他们将制定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确定制片人的岗位,并对制片人的责权利明确规定。据了解,今年年底,央视将有10名制片人通过竞聘获得职位,这较以前的制片人任命制有了很大变化。 当然,这些措施也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仍有待改进。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堵一些漏洞,但“只是让想干坏事的人操作起来更加困难一些,并不是说他们就完全做不了了”。 针对央视前所未有的换岗创举,有业界人士担心,如果只是调换岗位,是否可能出现前“腐”后继的问题? 今年9月,央视《开心辞典》栏目制作了一期廉政特辑节目,就规章制度和与廉政有关的内容考查工作人员,并组织集体观看,这说明央视进一步重视思想教育。 但是,任何一个资源丰富的部门、一个公众瞩目的部门,腐败易发环节可能更多一些。而央视拥有的虽然不是对社会直接进行管理的硬权力,却是具有一定垄断意味因此也就具有某种稀缺性的软权力,因此反腐形势仍将严峻。 赵安案只是一个普通的受贿案。公众之所以关注赵安,一是他的知名度引起社会的连锁反应;二是赵安等人问题的曝光,也暴露了机制方面的缺陷。 对官员的监督是不是严格,官员行为如何规范,都是央视需要思考的问题。 人们在关注央视,人们也寄望央视。
2002~2003年传媒腐败实例
2002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告处处长陶建因截留报业集团巨额资金、偷逃税及多次收受他人贿赂而被拘捕,同时,广州日报社原总编辑何向芹因涉嫌从广州日报集团的房地产、装修和广告业务中收取回扣被双规。 2002年6月3日,广州市原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广州日报》原社长黎元江因严重经济违纪被双规,其得力助手《广州日报》社社长助理、社办主任梁燕梅同时被双规。 2002年6月下旬,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副社长凌近铿、集团印刷中心总经理兼社长助理何兆仪被双规,他们二人分别掌管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财务和印刷材料采购工作,被怀疑参与了黎元江和何向芹的贪污活动。 2002年8月,28岁的《中国财经报》社原广告部副主任李晋虹因贪污349万余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2年11月8日,辽宁省沈阳日报报业集团原总裁、总编辑傅贵余因犯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2003年9月,中央电视台原文艺中心副主任、影视部主任冯骥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拘捕。 2003年9月,11名记者,包括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过程中,受贿7.46万元人民币,已转交山西省检察机关立案侦察。 资料来源:据公开报道 资讯整理:陈利华
警惕特权利益侵略传媒
今天,国内媒体腐败屡成大案要案,其严重程度恐怕只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多个外国政府贿赂的法国部分报纸可比。一个走向现代化、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如果缺乏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公共与专业伦理,那是不可想象的 文/展江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在传媒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这就为其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 但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又变成了某些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 尤其是报业集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使得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 但是与20世纪新传媒——电影、广播和电视——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新媒体在英、德、法等许多国家,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本来,传媒最初是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干涉,而现在,这种格局被彻底颠覆了。而且传媒传播的效率越高,就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 结果,哈贝马斯借用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丑闻、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于是,文化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倒退了,部分公众重新陷入愚昧状态而不知。 令人尴尬的是,在中国传媒领域,这些问题已经出现。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当年我们有人嘲笑张季鸾为《大公报》定的报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可是今天有媒体见赵公元帅(指财神)就拜,甚至以“舆论监督”为敲诈手段,以致于媒体腐败屡成大案要案,其腐败程度恐怕只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多个外国政府贿赂的法国部分报纸可比。 已有政治学者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这一问题的后果是,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兹举每日新闻事业中的几种现象为例: (1)各种商业和私利集团利用传媒,以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的形式频频制造“媒介事件”,私人和私利团体成为新闻主角,他们的利益俨然成了公众利益; (2)媒体的商界朋友成了新的媒体英雄,而一旦这样的“英雄”失势或案发,媒体则往往三缄其口; (3)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人为乐事,对真正的监督对象——不法权势集团——却曲意逢迎; (4)在本地新闻表现歌舞升平的同时,媒体主管并不是不知道“负面报道”的用处,只是更经常地利用别人的“全是坏消息”报道模式从事“进口转外销”,仿佛天灾人祸只发生在异域和外地; (5) 由于国内报道领域的窄化,在市场机制下出现的通俗报纸过早出现了过度同质化。 如果说,我们的媒体都在如此维护“主旋律”和“收视率”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大众传播方式,是否会诱导民众变成不讲游戏规则的经济动物,是否会加速公德和社会良知的失落,以致于出现马克思所说的精神斋期呢?——但愿这只是几个不合时宜的读书人的杞人忧天。 一个走向现代化、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如果缺乏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公共与专业伦理,那是不可想象的。而欲规避这种危险,可采取的对策当以制度建设为主。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