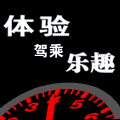名校校长探讨大学与城市关系 合理筹资金成困扰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2日13:41 新民周刊 | |||||||||
|
怎样合理地筹集资金以利于学校的发展而又不影响学术自由,这是永远困扰现代大学的命题,也是每一个大学校长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仅仅认为大学有利可图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大学创造的应该是创新氛围,而不是走从研究到商业的简单线性道路。
撰稿/贺莉丹(记者) 金佳睿 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感叹,现在世界名校校长要见面都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成了一个崭新的探讨现代教育的舞台。 2005年9月23日上午9:30,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谢希德厅,复旦百年校庆之际,包括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在内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30所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会聚复旦,共同探讨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作为特邀嘉宾,上海市市长韩正和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出席论坛。 大学教育与城市发展 “过去十几年来,上海与复旦像在度‘蜜月’,而且日后也将越度越‘蜜’……”,在韩正看来,一个城市的实力强弱,一看硬实力,二看软实力,而大学是这两种力量的发源地。 1980年,上海有49所大学,在校学生不足8万人,每万人中仅有67名大学生;现在,上海有59所大学,在校生50万,每万人中有307名大学生。 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坦率地说,由于中国不少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大学成了城市创新之源,中国高校比国外高校承担更重的历史责任,中国城市发展、现代化进程都离不开大学的服务。 大学兴起能带来国家昌盛,这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在11至12世纪,当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出现时,接踵而至的就是文艺复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校长,63岁的盖文·布朗教授解释,大学不仅对地区经济有贡献,还可以是地区的文化中枢;大学教育提供的一种创新氛围,所孕育的创造力阶层,会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许多创新活动发生在充满文化、充满活力的大城市,城市也能提供宽容的氛围。全球化冲击下,大学不能独善其身。东京大学在10年前组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联盟”,希望通过分析各个学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来建立通用学科,重点研究城市体系。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提出:“高等教育要着力解决环境和城市发展问题,应该重组学术领域和知识结构,建立通用的学科。” 许多大城市面临严峻挑战,包括空间匮乏、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坚持认为必须超越科学技术、超越传统智慧,建立起跨学科的眼光和战略,找到综合性、全面性城市问题解决方案,使城市真正成为生活工作娱乐的场所。 施春风演讲时拿出一份报纸说,《海峡时报》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X和城市》的文章。他说,全球级的城市,是不同社会、社区、文化间相互沟通的重要中枢,城市发展的基础就是叫做“X”的要素,包括社区文化、商业和通信。“大学在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断对城市发展提供贡献,包括创造知识和思想,为今后人们的创新及创业目标提供良好精神基础。” 大学运营的资金难题 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此次论坛发言时,开玩笑地形容市长韩正和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为“两个钱包”,他说,复旦的发展离不开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合力支持。 今年上海市财政总收入除去交给中央部分将达约2100亿,其中21%以上将用来增加教育投入。复旦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大量投入,上海还为复旦扩建提供了1500亩土地,土地成本在30亿元,按国有资产流转计算值50亿元,若拿到市场上拍卖可能价值100亿元。 英国爱丁堡大学校长对此羡慕不已,他风趣地向王生洪校长询问如何与政府间建立了如此良好的关系。 很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都遇到经费难题,悉尼大学校长盖文·布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资本是一柄双刃剑,资本也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怎样合理地筹集资金以利于学校的发展而又不影响学术自由,这是永远困扰现代大学的命题,也是每一个大学校长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世界银行曾指出:目前高等教育的主要情形是经费“处于世界性危机之中”。在经费来源上,各国大学校长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互相取经,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主任Bruce Melville教授向记者抱怨,政府对于他们少得可怜的支持,让他们觉得大学产业化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也承认,“非常遗憾,牛津不像耶鲁一样能够得到政府的很大财政支持。” 他曾担任过4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副校长,也是900年来牛津首次聘任英国以外人士担任的校长,约翰·胡德上任虽才一年,却一直为钱头疼不已。2005年年初,约翰·胡德给牛津下了一剂“猛药”,5年内将本科生的招生名额从1.1万人减少到1万人,这一举措是为了扩大外国留学生的招生力度,因为这些留学生费用完全自理。 道理很简单,一流大学就像皇家马德里队,需要足够多的钱才能招聘最优秀的教授。而如今的牛津,每年光行政开支就有2000万英镑的赤字,这所公立大学很大程度上依靠英国政府的财政拨款,近年来政府不许提高本科生的学费,对牛津来说,多培养一个本科生就等于多赔一份钱,这个大学每年为每个本科生花掉18600英镑,而从每个本科生身上只能得到9500英镑。也是缘于公立大学的性质,牛津收到的私人捐款也相对较少,2002—2003学年,牛津收到了5800万英镑的捐助,而同年,美国的哈佛大学收到了2.62亿英镑的捐助。这样的财政困境,慢慢影响到了牛津的科研、教学等诸多方面。 在国际上,大学争取社会捐助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国大学如哈佛大学等,都有自己的募捐机构,校董会的主要作用也是筹资。纽约大学选择校董会成员的原则是:“捐钱,找钱,否则请便。” 这样一来,美国的大学资金相对充沛。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投资大学的基础学科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投资的不可预见性,私有部门不愿介入。但事实证明,美国从1946年建立的大学基础学科投资机制确保了它在基础学科方面的领先地位。在美国,大学资金的分配,不是由政府或商业部门决定,而是由独立专家委员会和科学家一起评议,资金在各个大学的分配是一个竞争的过程。这一做法鼓励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和挑战性,麻省理工学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目前,麻省理工一共有4000多家学生创办的公司,而且这个数目还在以每年150多家的速度递增。这些公司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占了马萨诸塞州的25%。 58岁的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认为,美国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应该继续加强对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科学投资;投资者要耐心等待结果;要保证投资的集中性;不是由政府而是由专家的评估对同类项目进行挑选和审查;政府投资能大大促进科研者的勇气和冒险性,不能让社会资助取而代之。 大学是创造力中枢 从大学出现至今的1000多年中,全球许多大学都创造了不同的与社会互动发展的模式。 牛津大学同社会的结合历史上并不如美国的大学紧密,但现在知名大学的周围往往会聚了一批高新企业,一项经济学研究表明,对大学科研的投资所能获得的回报是其他投资的7倍,因此,很多企业都转移到了大学的周围。60年代的牛津郡是以农业为主,有一些酿酒业和加工业,而现在,牛津地区80%的高科技企业由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创立,该地区的人均GDP高于全国水平。目前,英国大概80%的高科技公司是由牛津毕业生创建的,技术转让等手段带动了整个牛津及其周边地区的飞速发展。 “我们在牛津以外建立了大量独立实验室,研究高度密集,科研成果广泛应用,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开展跨机构的合作,建立了创意中心。我们拥有全英最大的技术转让中心,技术转让项目平均每6-8周就能创造一个新企业。每年,我们还组织投资洽谈活动,鼓励年轻人创业。”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说。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创新氛围非常浓厚,在生物医药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金,仅纽黑文地区就吸引投资20多亿美元;大学周边林林总总的公司中,有79%是属于“师生类公司”。 美国政府曾经认为投资地方性大学才有利可图,而对于大城市中的大学,则认为它们可以自力更生,不需要政府的投资,悉尼大学校长盖文·布朗直言批评:“仅仅认为大学有利可图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大学创造的应该是创新氛围,而不是走从研究到商业的简单线性道路;大学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组织,是所有创造力的活力中枢。” 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它从来不是创新的反义词。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更智慧的方法是利用现在和过去的知识,创造出新的价值。 一流大学的标准 “一流大学”是中国很多大学提出的办学口号,题中之义,仁者见仁。 大学的魅力在于学术自由和办学独立,大学能给城市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培养未来领袖,培养独立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认为:“衡量一所大学是不是最优秀,标准不是光看它的学术,而应该看它如何帮助所在的社区,应对社会变革带来的诸多挑战,并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校长马克·莱顿则看来,一所优秀大学必须具备高水平的师资和学生。美国很多大学留学生的比例都相当高,比如斯坦福达到了60%以上,极大地促进了思想、创新方面的多元化。 香港中文大学倡导人才的国际化,香港中文大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高薪聘请知名教授,本校博士不直接留校任教,同时增收留学生,以塑造中西合璧的人才。 从大学是跨学科的汇聚之地而言,随着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日渐多样性,学术界和知识结构重新组织,能为现实世界提供更多解决方案。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认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承担这一重任,他认为亚洲大学的面临的挑战是,在增强国际交流的同时保护好本国文化的多样性。 当记者问到中国大学与国外的大学仍旧有哪些差距时,悉尼大学校长盖文·布朗幽默地回答:“中国大学已经在非常正确的路上走了,而且走得非常好,你们做了足够的努力。” 担任耶鲁大学校长12年的理查德·莱温教授认为这种差距来源于师资:“中国大学很多老师都是本校毕业,而在美国大学则更加开放地招收教师,这样显然更有利于建立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优秀的大学并不等于规模的“大”。实际上以规模论,世界上许多一流大学都是“袖珍家庭”:耶鲁只有1.1万名学生,剑桥大学仅有1.5万名学生,但研究生就占1/5。但中国大学近年扩招规模日趋庞大,早已是耶鲁和剑桥的好几倍,与之相伴的是大学氛围日益淡漠。 一个对比是耶鲁,这所大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模仿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模式实行“住宿学院制”,每个“住宿学院”由来自不同院系和不同专业的400—450名学生组成,配有院长和若干住院教授,学生在其中居住、进餐、社交,从事多种多样的学术和课外活动,这是耶鲁之所以成为耶鲁的一个原因。-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